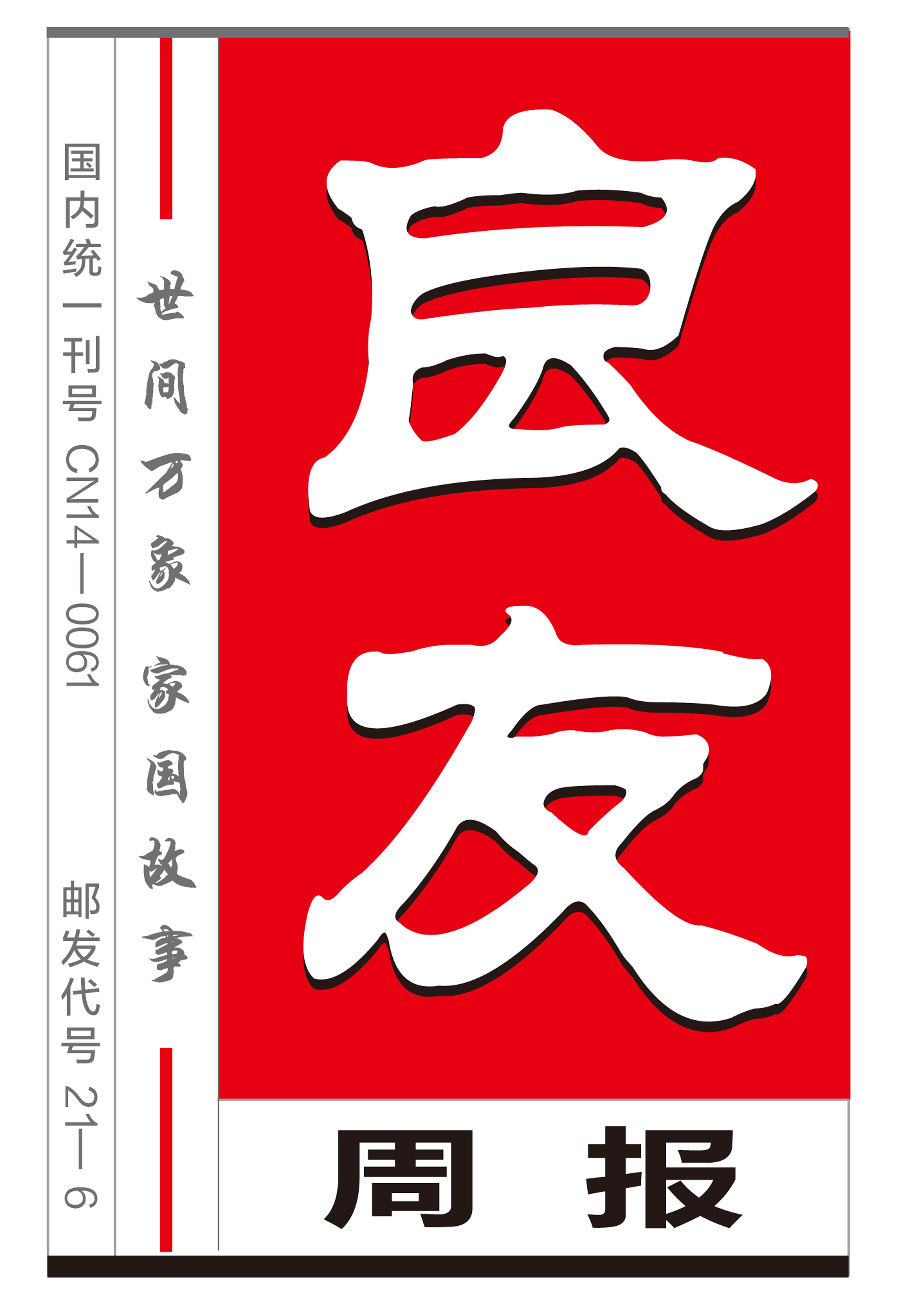【故纸堆里寻安全】叁:太甲桐宫,未道鸣条作网罗
瓶颈之危,宛若魔咒,在每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总能给意气风发的帝王们当头棒喝。
秦朝传到二世,国祚不过14年,便遭到了刘项攻击而灭亡。隋炀帝暴虐,至他隋朝也不过三十七年。五代和元朝亦是如此,即便是强大的唐、汉,均在开国建基后不久便遭遇到了政权危机。
这便和中国传统花瓶般,瓶颈之下便是广阔的空间。但如果不能顺利通过瓶颈,很可能面临朝代终结的危险。
瓶颈之危考验的不是开国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二代、三代继任者的德行与智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监管失位,是瓶颈之危产生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说,开国帝王出生入死,即便深居安逸的皇宫,也还保存着谨慎的作风。而他的后代们,则以天下太平的心态和骄奢淫逸生活断送了江山。
度过瓶颈危机,需要统治阶级内部自我更新和救赎,即除了领导人的政治自觉外,是否有所担当和作为的人中流砥柱般坚持道义和真理,即所谓的“法家拂士”。为此,孟夫子曾有这样的论述: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如果将这样的情形放在当今生产经营单位,从安全的角度讲,国君帝王便是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而“法家拂士”就是专司安全之人。很明显,双方的高度、地位、职权均不匹配,企业的“法家拂士”们很难有所作为,在权力的组织框架内,他们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这是企业盈利与成本的博弈,也是现实与发展的冲突,更是企业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的矛盾。面对巨大的金钱诱惑,就如同人的惰性与享乐之风如帝王般触手可及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完成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和行为纠偏,对朝代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放太甲于桐宫”发生在商朝,在中华民族第一个有确切记载和实物勘验的朝代中,就给出了经典的回答。
大禹之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将公天下改为家天下,传十四代十七王。至十三代帝王孔甲之时,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了,夏桀即位,他更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赋敛无度,万民甚苦”。
瑶台裂帛成为夏桀挥霍享受的标志性事件。桀的王后妹喜天生丽质娇艳无比,所谓“眉目清兮,妆霓彩衣,袅娜飞兮。晶莹雨露,人之怜兮”。一次偶然机会,她发现名贵绸缎撕裂的声音无比悦耳,于是帝桀便命人在他奢华无比的宫殿瑶台中“裂帛”来取悦妹喜。
骄奢淫逸往往需要暴政的实施来维护歌舞升平和天下太平的虚假景象,但也会有正义之士挺身而出直谏君王,关龙逄就是其中一位。
酒林肉池边,关龙逄手捧黄图常立不去。所谓黄图,就是一种地图,关龙逄想借此说明形势危急,进谏夏桀应多关心朝政。可惜夏桀根本不理会关龙逄的意见,甚至对关龙逄的存在表示了极大不满,不仅撕毁黄图,还将关龙逄以“妖言惑众”的名义问罪杀害。
四十年后已经是沧桑巨变,但关龙逄遭遇不测的往事还是让伊尹不寒而栗。
伊尹出身卑微,母亲只是一个地位为奴隶的采桑女,他也只能以伊水为姓。因为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他十分了解民众的疾苦,成年后特别崇尚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当时正好商汤欲图霸天下,于是三次前往他的居住地莘国去聘请他。
如同顽固性和习惯性违章难以杜绝的情况一样,尽管有伊尹等贤人的大力支持,商汤用了二十年时间,与夏桀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才凭借鸣条之战一击而成,驱逐夏桀逃离京师夏都(今山西夏县),取国号为商。
汤之后,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四代君王均拜伊尹为帝师。但在太甲朝,历经三四十年的商王朝时间之窗被打开,瓶颈之危爆发,伊尹遭遇了与关龙逄同样的尴尬与境地。
成汤之后,两任帝王外丙、仲壬的意外早夭,让衣食无忧的太甲,在缺乏历练和系统治国理念培养下,过早地成为一国之君,并在登基后,将所有的帝王惰性和成为帝王之后的享乐心理完全暴露无遗。《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
身受三王重托的伊尹进退两难。进言,或许就和关龙逄下场一样;缄默,并非是为人臣子的本分。历史上明哲保身也是一种态度,但却是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也是怯懦的表现。除此之外,伊尹最大的心结就是从征伐桀纣时期的对立者变为维护政权颜面的维护者。从王权或者皇权的角度讲,对外伊尹最大的工作就是文过饰非、粉饰太平。
伊尹是心怀天下之人,以天下江山社稷和苍生为计,其所要求仅仅止于箪食豆羹一顿饭而已。对于权利,即使是普天之下归其所有,他却觉得十分渺小和不值一提。
于是对于太甲,他做出了史上第一次大胆的行动:在成汤王墓旁,修建了一所茅屋,称之为桐宫,并把太甲幽禁于此。而他则与大臣们共同主持朝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共和执政”。
与贬为庶民无异,在桐宫,龙子狴犴的太甲开始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反思。“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每日里他读着伊尹为他所做的《伊训》《肆命》《殂后》三篇议政文章。其中,《伊训》是伊尹对他的告诫,《肆命》是教他怎样当政,《殂后》是商汤的法律制度。
伊尹是用身死名裂的方式挽救岌岌可危的成汤王朝,或许也只有伊尹拥有这样的胸襟和格局。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同时也是对自身修为的极大提升。他以完美的人格品质,排除得与失在他心中的干扰,荣与辱在他身外的纠缠,不因困窘、得志、利益而丧失初心,用不断提升的道德水平和理想信念作为强大支撑。
太甲被废黜,开“废君”先河,但天下人并没有因此而怪罪伊尹,甚至连被黜的太甲都不以他为僭越和独断专行。
七年之痒,让太甲脱胎换骨。伊尹用帝王之礼把太甲迎回都城,还政于太甲。太甲也没有让天下人失望,二次即位后,太甲勤修德政,以身作则,天下归心,百姓安宁。后世也给了他较高的评价:太宗。
伊尹死后,太甲的继任者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之。后来宋朝的苏轼评价此事时说:“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苏轼大胆批判了倚借惯例而因循守旧的人,以个人荣辱和得失而忘记自身职责不敢担当的人,工作中瞻前顾后、被眼前利益蒙蔽和收买的人。
试想,一个立足长远、心忧百姓,又能为国家或者企业度过最艰难的瓶颈时期的人,又何愁没有美好未来呢?
王清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