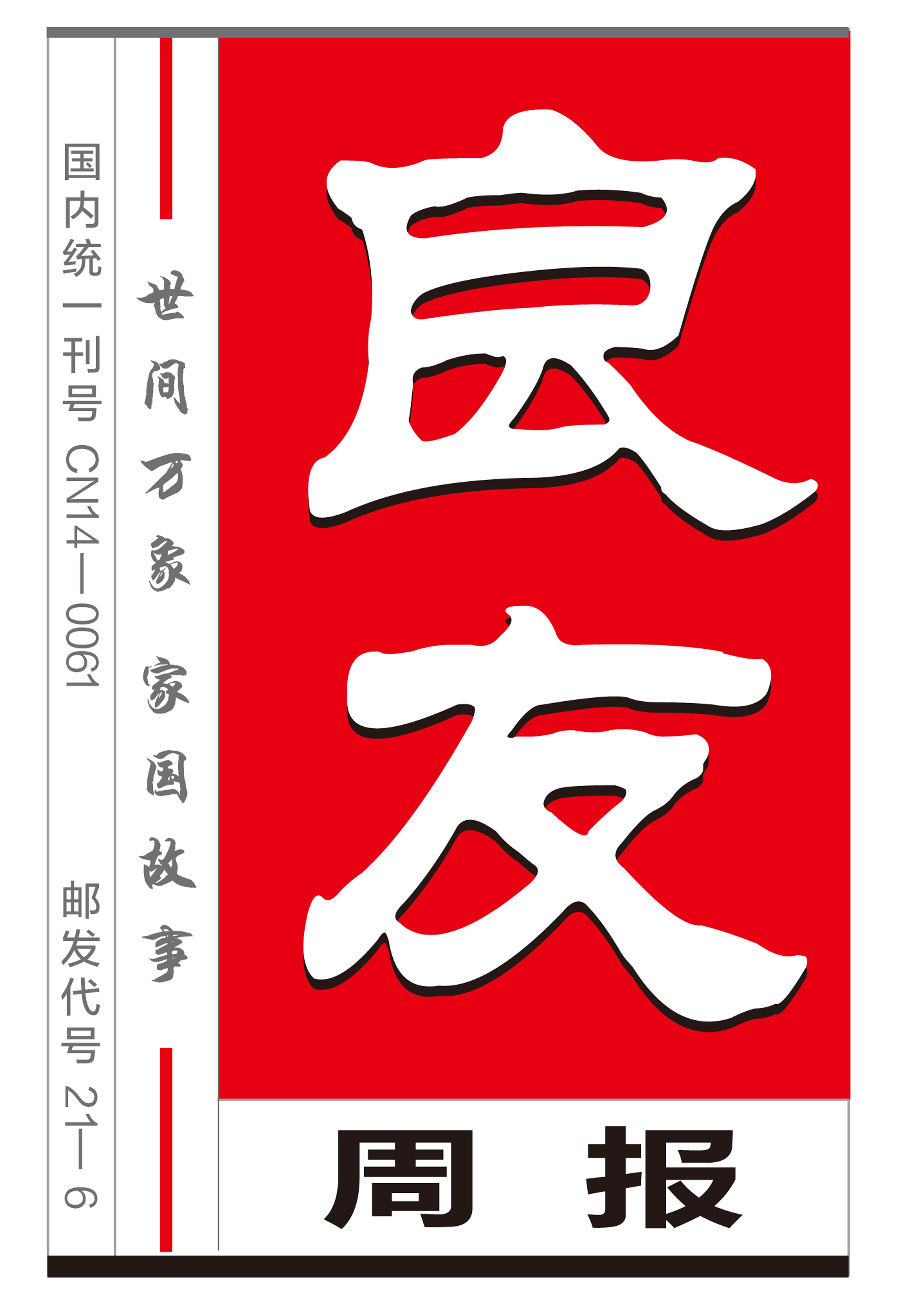【故纸堆里寻安全】柒:郑庄公,中原用计守纲常
春秋初年,郑庄公的故事可以说是现代企业在逆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另类注解,成为双方博弈后来居上实现惊天逆转的经典案例。
郑国原先的封地在陕西棫林(今陕西扶风县),平王东迁时,郑国护卫周室来到中原,并在虢(今河南密县)、郐(今河南荥阳)间定居。很显然,郑国仅仅是西周春秋时期众多诸侯之一,相对于周边诸侯,并没有过高的实力。战事之后的短暂和平以及外部环境的相对宽松,使郑国迅速发展强大起来。郑国的内部也在不断地调整状态,使其从统治阶级内部到庶民都有理性的选择和规范的秩序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对郑庄公来说,有一条重要的强国基础就是保障宗族家事的相对稳定。在经历了“兄终弟及”到“嫡庶子”继承后,至郑庄公时,王位的争夺从统治者家族内部矛盾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全体国民意志的统一。
打破“君权神授”的神话,填补它的便是武力和中央集权的高度统一以及王位争夺的流血现实。这一点对于郑庄公来说,体会或许极为深刻。他的父亲郑武公娶妻武姜,武姜生庄公及叔段。由于难产,武姜并不喜欢庄公,甚至给他起了一个怪异的乳名——寤生,以示厌恶。对于次子叔段反倒宠爱有加,经常在武公面前美言。尽管庄公以嫡长子身份顺利继位,但对于他的弟弟叔段来说,不异于晴天霹雳。昨日同胞,一朝君臣,尽管取得京邑这样的殷实之地,但叔段依然心存野心,与王城里的武姜里应外合准备起兵造反。
叔段极力强化武备,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京邑的城垣已经超过庄公的都邑,并且收编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镇守将领听命于他,实力得到空前发展。他凭借一些恩惠和威望,被人们称为“京城大叔”,俨然一副在野天子的味道。自然,这些情报会迅速送到庄公那里。
天无二日!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郑庄公居然忍受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掩盖了一切事实。忍!郑庄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来等待一战定乾坤的最佳时机,而这一战,必须师出有理、名正言顺。
郑庄公用自我压抑和韬光养晦的办法,等待正义力量汇集成不可逆转的强劲动力。郑庄公祭起的“义”,便是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春秋战国时代战事纷争,但没有一个诸侯国敢于公然对礼制提出挑战,即便周室衰微,诸侯们也得利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来发号施令,超越了这条禁律,天下就会群起而攻之。对于不同层次和不同时代的人来说,“义”所包含的概念不同,包含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但“义”的底线是不分阶层和恒久不变的,任何行为不能触碰这条底线,或者以牺牲“底线”、践踏红线作为发展的基础。从道德层面和现代社会管理方向来看,郑庄公有着故意纵容最终导致叔段身败名裂的战术思维。但从竞争成本的角度看,庄公利用了最小成本,达到发展的终极目的。
现代社会对于企业之间的良性发展和有序竞争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对社会和企业来说,同样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不可触及的底线。企业发展必须遵循安全生产的原则,必须充分尊重安全生产的投入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有效关联,必须在理论上厘清经济手段刺激发展和企业良性可持续发展之间内生动力的根本区别。
与有些企业将经济效益毫无原则地盲目放大,认为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有偶然性一样,叔段将“义”的底线力量爆发看作偶发因素,极端注重“穷兵黩武”般的势力扩张,忽略了违背“正义”被群起而攻之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在践踏底线超越红线作为发展代价的时候,或许繁荣将变得虚假,单凭经济刺激或者精神鼓励难以挽回根基缺失带来的巨大生存危机。
仅以安全生产为例,很多现代企业在放弃安全底线后,确实为企业带来短暂的空前发展,在特定时间内超越了对手。但安全隐患甚至风险的失控,会在竞争最为关键的时刻将企业颠覆。安全作为现代企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仿佛叔段放弃对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起码尊重一般,会使自己不知不觉陷入内外忧患的境界。
终于,叔段膨胀的欲望让他尝到了恶果。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借着修整城垣的机会,大肆补充武器装备,并与母后武姜约定,在其攻打都邑时打开城门。这一切均在庄公的意料和掌握之中,庄公的军队在道德和礼仪武装下的京邑民众支持下,仅仅一战就歼灭了叔段叛军。叔段也逃亡他国,最后客死他乡。
作为我国著名史书和儒家重要经典的《春秋》一书开篇,孔子用“(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字来说明郑国兄弟相争、结局迥异事件的重要意义。在孔子看来,叔段的悲剧在于庄公失于“孝悌”的故意纵容,诱使其走上不归路。但究其根源,便是叔段丧失“底线原则”,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盲目发展、无序竞争造成的。多少有点像现代企业为了挤垮同行,加大生产忽视安全作用一样,最终结果便是企业的灭顶之灾。压垮这个企业的,或许不是同行,而是像庄公所倚靠的京邑民众维护道义的自觉——给再多的经济刺激,也会有人天然地感知生命的可贵。
王清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