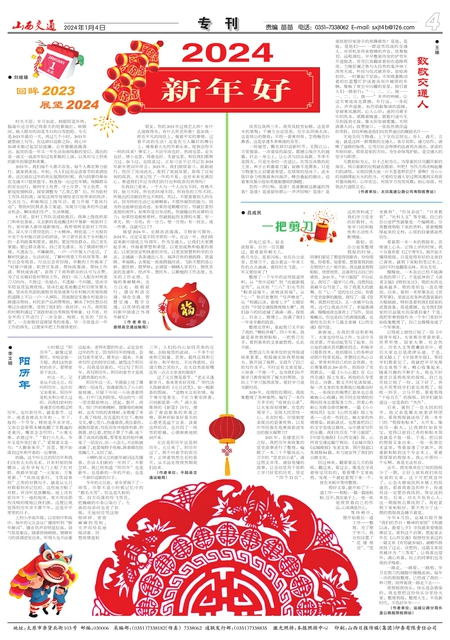阳历年
李文晓
小时候过“阳历年”,就像过星期天,学校会放一天假,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要帮家里干农活。
对这一天,父亲从不说元旦,而叫阳历年。也许在父亲看来,阳历年是机关和公家人过的,而我们农村的普通老百姓都过阴历年,也叫农历年,就是春节、过年、或者直接说大年初一、年下。每到一个节令,特别是年末岁尾,父亲总会看那本被他翻了无数遍的老黄历,嘴里念念叨叨:“小寒大寒,杀猪过年。”“春打六九头。今年又是年里打春了。”紧接着又是一句:“人勤春来早。”说罢,便开始谋划过年和开春的一应事情。
的确,这个叫元旦的阳历年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村前的保健站,还有学校大门上贴了红对联。我最早知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之类的对偶句子,就是从元旦对联看到并记住的。这些地方贴了对联,并没听见放鞭炮,地上没有农历年下一地的炮皮,更不用说那些没响的哑炮让我们拣。这便让我觉得阳历年并不算个年,还是平平常常的日子。
上到小学高年级,以至初中和高中,每年的元旦会从广播里听到“新年献词”。播音员声音明显拉高,语气很是豪迈,随着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语调迸发出来,听得人也不由豪迈起来。老师布置的作业,必定会有过年的作文,因为阳历年的缘故,会比写春节更早,便多出一篇来。不喜欢写作文的同学百锁,就骂这个阳历年,而我是窃喜的,可以写了阳历年,再写阴历年,阴历的春节才是我们最欢喜的大年。
阳历年这一天,早晨窗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花,弥漫着围占了小小的窗玻璃,只留下中间一小块透着明亮。打开门走到院里,哈出的气一团一团在眼前喷出、团起,散开、消失。院门外的刺槐树、猪圈旁的核桃树,还有当院的香椿树,全都瘦了身子,现了枝杈,在瓦蓝的天空下,粗细交叉,横七竖八,你叠着我,我压着你,疏散而紧密,纷乱而有序地排列着、相拥着、挤让着,把院子罩了个满。地下落了淡淡的晨霜,零零星星的枯叶被染了一层浅白。站一小会儿,不由脸就冻麻了,赶紧缩脖子统袖,跺着脚在院里蹦几下,又回了屋。
小喇叭里元旦的新年献词还在播放,告诉人们新的一年到了。不管怎样,我已经知道“阳历年”也是新年,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
今年的元旦前,家乡晋南下了一场雪。尽管不是小时候记忆中的“鹅毛大雪”,但也是久盼的雪。自天而落的纷飞雪花,把巍峨的中条山染白了,九曲的母亲河也老了容颜,天地间任凭这细细碎碎、密密麻麻的雪粒,无声而纷乱地搅动着。回想疫情盘桓三年,人们的内心如同苦焦的庄稼,企盼瑞雪的滋润。一千多个日夜和它较量、苦熬,最终还得和它妥协、和平相处。不由得感叹,自诩万物之灵的人,在大自然面前哪还有一点点主宰者的颜面!
过了元旦便是春节。“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明代诗人陈献章的《元旦试笔》,如一幅新春的图画。“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清人张维屏的《新雷》诗句,增添了喜迎新春的欢喜之情,那种祈盼美好春天的心愿更是溢于言表。读着这样的诗,也许因了一场雪的慰藉,心情渐渐地朗润开来。
无论是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元旦来了,阳历年过了,那个叫春节的农历年,正伴着悄然生长的春天,从不远处欣欣然朝我们走来。
(作者单位:平陆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