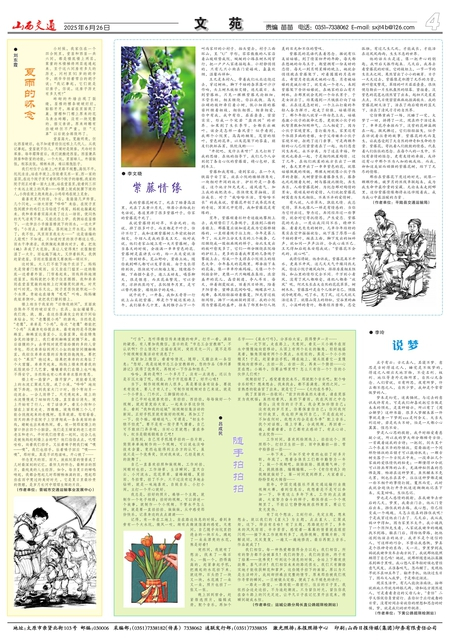夏雨的怀念
刘东霞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堂屋和西屋一共六间,都是楼底楼上两层,笨重的木楼梯将两层连通起来。至于这六间房有多久的历史,问村里91岁的胡爷爷,胡爷爷捋着雪白的胡子说:“我记事起,它们就是旧房子,你说,这房子历史有多久呢?”
砖砌的外墙出现了裂缝,屋檐的檩条破破烂烂,豁豁牙牙,麻雀在里面筑了巢。窗楣和门楣上原来的花鸟鱼虫砖雕,没有一块完整的。据父亲讲,原来砖雕有些破碎但不严重,但“文革”以后就全部毁坏了。
堂屋高大,宽敞明亮,但比西屋破旧,也不知道曾经住过祖上几代人。从我记事起,堂屋就不住人,天暖时是厨房,天冷时当库房。每年霜降前后,我们就搬进西屋,西屋兼具厨房和卧室的功能,一个大炕,里面睡人,外面做饭,粗茶淡饭,稀粥米汤,难以填饱肚子。
我们村位于山坡上,村里路不规整,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站在半坡上,你能看见东一家、西一家的屋顶,在这个院子里可看到那个院子的墙根。我家的院子则正对着一面大土坡,站在堂屋里,能看到三四十米远土坡上的风景——哈腰上坡或挺腰下坡的人,小狗在坡上跑来跑去,公鸡母鸡在坡上觅食。
最喜欢夏天的雨,午后,轰隆隆几声炸雷,几个闪电,一场大雨便“哗哗”来临。在院子里悠闲踱步的鸡们立马钻进了鸡窝,蚂蚁也躲藏起来。我和弟弟着实高兴来了这么一场雨,使闷热的天气凉爽下来,又能迟些上学。我俩站在屋檐下,一边伸出小手接屋檐流下的雨水,一边大声唱:“小雨点,滴滴答,落到地上开水花;雨来了,我不怕,风里雨里我长大……”这是谁编的儿歌呢?不知道,只知道村里的孩子都这么唱。雨水干净清凉,我俩掬起来撩向对方,看,把他(她)弄成了大花脸,真让人觉得爽!衣服胸前湿了一大片,雨也越下越大,又伴着斜风,我俩赶紧进屋,否则衣服湿透又要挨妈一顿训斥。
这时候,大人们不能下地干农活了,妈妈先是倚着门框观雨,后又坐在门槛里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着外面。门帘卷起来,雨线斜斜地潲进屋里,妈妈就把小凳子往里挪挪。我和弟弟则在堂屋宽敞的地板上打闹嬉笑玩游戏,时哭时叫时笑,快乐无比,院子里很快就积起一个个水潭,青蛙也在墙角“呱呱”叫唤,妈妈嫌我姐弟俩吵,就把我们撵到楼上。
楼上相当于我家的“旧物收纳间”,里面放些陈年不用的破旧家什:农具、缸缸罐罐等。我们跑、跳、蹦,在这些落满灰尘的家什间钻来钻去,玩“老鹰提小鸡”的游戏。当然我是“老鹰”,弟弟是“小鸡”,每次“老鹰”都能把“小鸡”从藏身处给提出来。最有趣的是寻找蜘蛛茧。蜘蛛茧比蚕茧小,比蚕茧薄,粘在犄角旮旯的墙壁上。我们看到蜘蛛茧就摘下来,最后谁摘的少;去学校时就罚谁给摘的多的人背书包。那次弟弟钻到两只小缸的缝隙间摘蜘蛛茧,我拉住弟弟衣服的后角使劲拖拽他,要把这个“果实”抢过来,结果把弟弟的衣角扯了个大窟窿。弟弟哭起来,妈妈上楼来照着我的屁股就给了几巴掌,嚷嚷着我们在楼上也叫她不得安宁,当然妈也有心疼弟弟衣服的意思。
楼上有一扇窗户,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坡上的水流汇聚成几股,成了小溪,“哗哗”地向坡下奔跑。快到我家大门口时,拐个弯向另一边流去。一会儿雨停了,天光亮起来,坡上的水流慢慢成了细细的几缕,直至最后消失。坡上开始有了行人,有了话语声,看见小狗和小猫在上面东走走、西瞧瞧,坡角那棵三个人才能合拢抱起来的老槐树,苍翠欲滴,郁郁蓊蓊。雨天的燕子在院子上空滑翔成一条条美丽的曲线,蜻蜓也出来凑热闹,看,坡一侧那家楼上的窗口挤出四个小脑袋,他们是王婶家的老三老四老五和老六,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这会儿也是被他妈赶到楼上去的吧?他们指指点点,叽哩哇啦,向着我们招手,又扯着嗓子朝我们嘁“噢——噢”,我们也招手,扯着嗓子回应“噢——噢”,那时候,真是不识愁滋味,开心极了……
怀念夏天的雨。雨天,放纵玩耍的情景成了儿时最深刻的记忆,最恒久的怀念,最鲜活的图片,最纯美的人生经历。如今,每当夏日的蝉鸣响起,我都会想起儿时那酣畅淋漓的雨,想起那些在雨中度过的美好时光,它是夏日里最珍贵的馈赠,是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片段。
(作者单位:晋城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