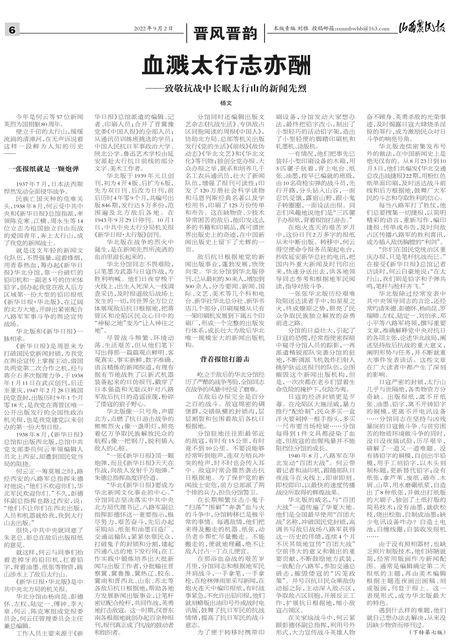血溅太行志亦酬
——致敬抗战中长眠太行山的新闻先烈
今年是何云等57位新闻英烈为国捐躯80周年。
壁立千仞的太行山,缓缓流淌的清漳河,在无声诉说着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张报纸就是一颗炮弹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1938年8月,何云受中共中央和《新华日报》总馆指派,率领陈克寒、江横、周永生等14位立志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爱国青年,奔上太行山,成了我党的新闻战士。
就是这支年轻的新闻文化队伍,不畏强暴,迎着烽烟,用青春热血,筹办起《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靠一台破烂的铅印机和一副老5号的仿宋体铅字,创办起我党在敌人后方区域第一份大型的铅印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辽阔的北方大地,开辟出紧密配合八路军军事斗争的舆论宣传战场。
华北版和《新华日报》一脉相承。
《新华日报》是周恩来为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为我党在舆论宣传上掌握主动,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之机,经与蒋介石多次据理力争,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后迁至重庆,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封,出版历时9年1个月零18天,是我党在蒋管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全国性政治机关报,也是我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
1938年8月,《新华日报》总馆拟出版西北版,总馆中共党支部委员何云率领编辑人员北上西安,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
何云正一筹莫展之时,路经西安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对他说:“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不久,彭德怀副总指挥也路过西安,说:“他们不让你们在西北出版,人员和机器就给我,我到太行山去出版。”
很快,中共中央就同意了朱老总、彭总在敌后出版报纸的意见。
就这样,何云与同事们抬着老掉牙的铅印机,扛着铅字,背着油墨、纸张等物资,跋山涉水上了敌后太行山。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
华北分馆由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傅钟、李大章、何云、陈克寒组成党报委员会,何云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
工作人员主要来源于《新华日报》总馆派遣的编辑、记者、印刷人员;合并了晋冀豫党委《中国人报》的全部人员;从通讯员训练班挑选的学员;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由延安派赴太行抗日前线的部分文字、美术工作者。
华北版于1939年元旦创刊,初为4开4版、后扩为6版,先为双日刊、后改为日刊,前后历时4年零9个月,共编号出版846期,发行达5万多份,范围遍及北方敌后各地。在1943年9月29日停刊。10月1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创刊。
华北版在战争的烈火中诞生,是在新闻先烈所流洒的血泊里滋长起来的。
华北分馆同志不畏艰险,以笔墨为武器与日寇作战,为胜利呐喊。他们日夜穿梭于火线上,出生入死深入一线调查采访,及时报道敌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向世界全方位立体展现敌后抗日根据地,把蒋管区和沦陷区民众心目中的“神秘之地”变为“让人神往之地”。
尽管战斗频繁、环境动荡、生活艰苦,但从他们笔下写出得那一篇篇观点鲜明、客观真实、事实新鲜、数字准确、语言精练的新闻报道,有理有据有节地战胜了以新式机器装备起来的日伪报刊,戳穿了日本强盗和无耻汉奸对八路军敌后抗日的造谣诬蔑,粉碎了倭寇的狼子野心。
华北版像一只号角,声震北方,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像一盏明灯,照亮着亿万争取民族解放民众的航程;像一把钢刀,锐利插入敌人的心脏。
“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千万炮弹。”朱德总指挥高度评价道。
“华北《新华日报》要成为华北新闻文化事业的中心。”分馆同志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这一重要指示,极尽努力,艰苦奋斗,先后办起采购站、纸张和油墨自造厂、交通运输队;紧紧依靠民众,打破鬼子的封锁和分割,建起四通八达的地下发行网;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培养出大批新闻与出版工作者,分批输往晋察冀、冀鲁豫、冀热辽、胶东、冀南和晋西北、山东、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各地方发展新闻出版事业,让笔杆密切配合枪杆,共同作战,英勇地打击敌寇。这一时期,仅晋东南各根据地就创办起百余种报刊,报刊真正成了抗战的鼓动者和组织者。
分馆同时还编辑出版文艺杂志《抗战生活》、专供敌占区同胞阅读的周报《中国人》,协助北方局、总部等机关出版发行《党的生活》《前线》《敌伪动态》《华北文艺》和《华北文化》等刊物;独创全党办报、大众办报之举,联系和培养几千名工农兵通讯员,壮大了新闻队伍,增强了报刊可读性;印发了120万册社会科学读物和马恩列斯经典名著以及学校用书,印刷了125万份传单和布告。这在缺物资、少技术异常困苦的敌后,能印发这么多的书籍和印刷品,真可谓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华北分馆到华北版停刊,已从最初的30来人,增加到500余人,分为要闻、新闻、国际、文艺、美术等几个科和电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书店几个部分,印刷规模从只有一架印刷机发展到下属五个印刷厂,形成一个完整的出版发行体系,成长壮大为敌后华北唯一规模宏大的新闻出版机构。
背着报馆打游击
屹立于敌后的华北分馆经历了严酷的战争考验,全馆同志在战争的风暴中经受了磨难。
在敌后办报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战斗。敌寇绵密的碉堡群,交错纵横的封锁沟,层层割裂和包围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分馆驻地往往距最邻近的敌寇,有时有15公里,有时竟不到10公里。不要说能够经常听到炮声,连双方哨兵冲突的枪声,时不时也会传入耳中。敌寇时常会骤然袭击抗日根据地。为了保护党的新闻战士安危,前方总部派了两个排的兵力,担负分馆警卫。
在长期频繁反击小鬼子“扫荡”“围剿”“奔袭”血与火的斗争中,分馆转移已是极平常的事情。每遇敌情,他们把来得及搬走的机器、纸张,动员老乡帮忙尽量搬走。不能搬走的,便就地埋藏,绝不让敌人讨占一丁点儿便宜。
在那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分馆同志和根据地军民并肩战斗,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枪林弹雨里采写新闻,在炮火连天中编印报纸,有时战事紧急,不允许出铅印报,他们就刻蜡版出油印号外或战时电讯版,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为了便于转移时携带印刷设备,分馆发动大家想办法,最终把铅字改小,制出了小型轻巧的活动铅字架,造出了小型轻便的脚踏印刷机和轧墨机、浇版机。
一有情况,他们把事先已装好小型印刷设备的木箱,用3匹骡子驮着,背上电台、纸张、油墨,按早已编就的班级,由10名荷枪实弹的战斗员,先行开路,分头钻入山谷,一面忍饥受饿,露宿山野,跟小鬼子转圈圈,一面设法出报。同志们风趣地说他们是“三匹骡子办报纸,背着报馆打游击。”
在炮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这份日刊2万多字的报纸从未中断出版。转移中,何云得空便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抄收延安新华总社的电讯,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及时刊印出来,快速分送出去,供各地领导同志参考和根据地军民阅读,指导对敌斗争。
一张张华北版历经艰难险阻送达读者手中,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照亮了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奋勇前进之路。
分馆的日益壮大,引起了日寇的恐慌,经常指使密探暗中窥寻分馆人员的踪影,一再派遣精锐部队突袭分馆的驻地,不断调派飞机轰炸扫射人挑驴驮运送报刊的队伍,企图摧毁这个新闻出版机构,但是,一次次都在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日寇的经济封锁更是歹毒。在沦陷区大施淫威,暴力推行“配给制”:民众多买一盒洋火要剁掉一根手指头,多买一尺布要当场枪毙……分馆每得到1件文具都浸染了血迹,但敌寇的血腥残暴并不能阻挡住分馆的成长。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何云带着记者和油印机,跟随部队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即审即刻、即校即印,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华北版的威名,与“百团大战”一道传遍了华夏大地。他们是全国最早使用“百团大战”名称,冲破国民党封锁,高调书写敌后战场八路军获得这一历史的伟绩,连续4个月不厌其烦地宣传“百团大战”空前伟大的意义和做出的重要贡献,不断鼓励地方武装,一致配合八路军,参加交通总破击,摧毁倭寇的“囚笼政策”。并号召抗日民众乘敌伪动摇之际,主动深入敌占区,争取敌占区同胞,开展反正工作,扩展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寇占领区。
在关家垴战斗中,何云紧跟彭德怀副总指挥,利用号外形式,大力宣传战斗英雄人物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及时揭露日寇大肆烧杀淫掠的罪行,成为激励民众对日斗争的响亮号角。
华北版连续密集发布号外的做法,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8月23日到10月3日,他们共编发《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捷报》22期,用粉红色纸单面印刷,及时送达战斗前线和后方根据地,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
每当八路军打了胜仗,他们总要搜集一切捷报,以简明精彩的语言,重新写作,编印捷报、传单或布告,及时向敌占区传播八路军的胜利喜讯,成为插入敌伪胸膛的“利剑”。
“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在接受《新华日报》总馆记者访谈时,何云自豪地说:“在太行山,我们则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华北版除过经常发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还经常约请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左权、陆定一、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将领,撰写重要文章,准确解释党中央对抗日的各项主张,论述华北战局,阐述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阐明形势与任务,并不断就重大事件发表谈话。这些文章在广大读者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寇严密的封锁,太行山几乎与世隔绝,各类物资万分奇缺。出版报纸,离不开纸张、油墨、铅字,离不开铸铅字的铜模,更离不开电讯设备……分馆同志在坚持与凶残暴戾的日寇做斗争、与贫穷困苦的物质环境做斗争的同时,没日没夜搞试验,历尽艰辛,破解了一道又一道难题。没有铸铅字的铜模,自创出半铅模,用手工刻铅字,以木头刻制标题,更新替代铅字;没有纸张,拿芦苇、废纸、破布、木屑、山草,用水磨碾纸浆,自造出了8种纸张,并做出打纸版的大刷子,独创了土纸打版的简易技术;没有油墨,就砍松枝,烧出松脂,自制成油墨;缺少电讯设备咋办?自造土电池,自缠线圈,自装收发报机……
由于没有照相器材,也缺乏照片制版技术,他们将陋就简,经常用版画作为新闻配图。通常是编辑确定第二天报纸的主题,再由美术编辑根据主题连夜画出画稿、刻成版画,刊登于报上。这一表现形式,成为华北版最大的特色。
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从来没因缺少物资而停刊过。
他们通过艰辛努力,打破了敌寇的封锁,求得了办报所用一切物资的自给自足,牢牢掌握了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朱德总指挥欣闻分馆连克难关,节节胜利,便奖励大洋300块,并写信鼓励道:“继续提高创作热情,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使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进!”
华北分馆和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同根同源,一起走过了峥嵘岁月。
1939年10月19日,北方局决定,华北所有战报和重要新闻,均由分馆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稿。
1941年初,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辽县(今左权县)山庄村成立,由分馆兼管总分社的发稿工作,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
从此,分馆电台除了接收延安总社、重庆总馆和各敌后根据地的电讯,同一些国家的通讯社也建立了联系;从此,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上;从此,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携手作战,牢牢占领着敌后舆论宣传的制高点,成为两座具有无穷杀伤威力的坚强堡垒,被誉为“华北抗战的向导”。
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辽县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129师师部等长期在辽县驻扎。大批干部从这里输送华北各地,大批部队从这里开往别的根据地。
倭寇惊呼这里是“繁殖游击战争的基地”,是倭寇的“眼中钉”。全民抗战期间,日寇“扫荡”、八路军反“扫荡”的激烈战斗,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
分馆1939年9月28日由武乡县转移到辽县,先后在后庄、上麻田、上武、岭南、山庄、熟峪等山村驻扎过,直到1942年10月6日迁往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
一般分馆驻在北方局、前方总部机关的附近。按照常规,日寇每年春秋对这里“扫荡”两次。每到“扫荡”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转往外线寻机作战,分馆跟随总部等机关,在大山深谷里兜兜圈圈,然后就返回了驻地。
法西斯的逻辑跟常人不同,一个中国啃不动,又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偷袭得手,不久即转入逆境。战线太长,顾此失彼,日寇更加意识到唯一生路是迅速“征服中国”,搜刮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大东亚圣战”。而要“征服中国”,就必须首先要消灭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日根据地。
人性泯灭的日寇为根除后方的“心腹之患”,纠集在华的大部分兵力,对敌后战场华北,接连施行“治安肃正”“囚笼战术”“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做法一次比一次野蛮,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1/6、人口减少1/3。
经过几年频繁激烈的反“扫荡”作战,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军民非常疲劳。1941年和1942年又连遭严重旱灾、蝗灾,敌占区、蒋管区灾民大量涌入,根据地军需民用极端困难。
分馆同志穿着破旧的军装,吃粗糠、咽野菜,省下小米、黑豆全都接济给断炊的老乡,和乡亲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鱼水深情。在左权县山庄、岭南、熟峪等山村,至今仍传颂着他们许多动人的故事。
即使再苦再难,分馆照样活跃于抗战最前沿,在敌寇从根据地没完全退走之前,在被毁的房舍余烬未熄之际,报纸继续出版了,居然还创造性地依靠各地方党委出版了南线版、北线版、东线版和西线版的油印报或石印报。
1942年5月19日起,日寇向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篦梳式”的“铁壁合围”,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无所不为。
同历次反“扫荡”作战一样,八路军主力部队果断跳出合击圈,进入“敌后的敌后”,机动寻敌作战,在敌占区断交通、攻据点,消灭鬼子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配合、支援腹心地区反“扫荡”作战。
前方总部等指挥机关,率少数警卫部队坚持战斗在内线。分馆驻在辽县麻田镇以东的山庄村,“扫荡”开始了还没有转移,仍然坚持出版了战时版的第1号和第2号两期铅印报纸。
几天前,分馆接到消息,鬼子又要来“扫荡”。分馆组织大家埋藏机器和各种物资,疏散妇孺病号,进入临战状态。
23日夜,狡诈的敌寇纠集3万多兵力,突袭山西的武乡、黎城、和顺,河南的涉县、偏城(1946年并入涉县),河北的邢台、武安、馆陶,急行军直扑辽县东南部桐峪镇、麻田镇一带,修筑据点,封锁山口,形成直径约25华里的包围圈。
日寇对华北分馆恨之入骨,每次“扫荡”都把摧毁分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24日拂晓,一股强敌猛然奔袭分馆。多亏早一步接到老乡报信,他们快速撤离山庄村,钻入了高山深谷。
鬼子这次“扫荡”作战,用兵之多,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狡猾狠毒,都是前所未有的。
北方局、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党校、华北分馆、朝鲜义勇队、朝鲜独立同盟、日本觉醒联盟等都深陷包围圈。被包围的党军政领导机关、直属单位和后勤部门很多,非武装人员超万人,警卫部队又少,敌我兵力悬殊,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整个白天,6架敌机擦着山头轮番疯狂轰炸扫射,地动山摇,石裂天惊。地面鬼子火力封锁着各大山口,机枪声如骤雨一般。马嘶人涌,万分紧张。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将军率少数警卫部队,以一当百,拼死抗击,逐山争夺,掩护彭德怀副总指挥、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和机关人员奋力突围。左权将军身先士卒,抵前指挥,25日黄昏不幸被敌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白日,日寇每到一地,立即派出多股队伍反复搜索,指挥官站在山头上拿望远镜观察指挥;夜间,小鬼子分头偷袭各村。小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牲口就牵。鬼子步步紧缩包围圈,抉剔清剿,分馆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他们被分围在几座山上,与敌面对面展开白刃战,伤亡惨重。
突围前,分馆已坚壁清野,掩埋隐藏了大型铅印机等物资,改用小型铅印机出报。面对鬼子越来越紧的合围,他们把小型铅印机也藏了起来,只随身携带蜡纸、刻板,出版油印小报。
为应对鬼子发疯似的围剿,分馆同志夜以继日辗转周旋,集合了被冲散,冲散了又集合,与警卫部队也失去了联系。
同志们连续几天没一会儿停歇,连日水米未进,人人口干唇裂,疲惫万分,虚弱无力,已不能再做强烈活动,大多数同志舌头粘在嘴里,连说话都很困难。
他们曾经历过无数次“扫荡”,从这几天日寇极端残暴血腥的情形上,已明显感到这回“扫荡”的不寻常。
的确,这次“扫荡”跟以往不同。为了摧毁八路军指挥中枢等重要机构,日寇早就派出“特别挺进杀人队”,伪装成民兵、八路军,自带干粮,昼伏夜行,绕过村庄,翻山越岭,潜入辽县刺探军情。
迫不得已,27日下午,何云召集大家商议决定:化整为零,分头突围。他带编辑、报务员等10人去寻找大部队坚持出报,副总编陈克寒带10名记者向南突围并随军采访,编委史纪言带60人就地打游击。
最终,陈克寒一路顺利突围出去,而何云这路却无数次突围均告失败。
27日,何云率队转移到辽县大羊角附近,当晚,他将重要文件销毁,不顾个人安危,仍坚持架起电台接收电讯,亲自撰写稿件,准备出版战讯。
28日五更,日寇又开始搜山了。何云和几位同志隐蔽在灌木丛中,不幸被鬼子发现。“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能活着当俘虏受辱!”面对鬼子的疯狂射击,他沉着地对警卫员王保林说。
突然间,一颗子弹射来,何云被击中,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鬼子退后,当医护人员前来抢救时,他已奄奄一息。但他睁开无力的眼睛,小声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救治其他同志。”等医护人员返回来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永远与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吴青分离了。那年,他38岁。
何云是分馆管委会主任、总编辑,同时兼任着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主任,还是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他原名朱士翘,1904年出生,浙江上虞县人,是文坛上声誉卓著的文艺作家。早年就读复旦大学,留学日本,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领导民族解放大同盟,全力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在上海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在狱4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派在南京编辑《金陵日报》,不久又调往武汉筹办《新华日报》。从此,他就一直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
何云牺牲后,129师刘伯承师长悲痛地说:“实在可惜呵!左权、何云两同志,一文一武,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啊!”
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悼何云》一文中写道:“接着左权同志殉国哀讯传来的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扫荡’战争中牺牲的哀讯,一个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何况死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疆场上,这是何等光荣啊。然而何云正在壮年,党所给予的任务尚待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牺牲,这确是一个损失!”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无比悲痛和愤慨,写下了著名的《哭何云》挽诗,纪念疆场浴血的战友。
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
党报事艰来日永,同侪心痛老成休!
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雪大仇!
后死吾曹犹健在,不听胡语乱啾啾!
日寇的“扫荡”还在进行。
6月2日,是分馆管委会总会计兼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30岁的生日。
就在这天下午,日寇包围了辽县庄子岭进行搜索,不幸的是,黄君珏和女译电员王健、女军医韩岩藏身的石洞,被敌寇发现。她当即沉着应战,迫使敌难于接近。
双方对峙到黄昏时,狡猾的鬼子趁着天色朦胧摸索着逼近洞口。君珏发觉后突然跃出,拿手枪连续射击,3个鬼子应声倒地,其余四散奔跑。
鬼子恼羞成怒,从后山爬上山顶,用绳子将柴草吊下,焚烧洞口,浓烟烈火冲入洞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君珏抱定“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勇敢地冲出洞外,打完枪里的子弹,纵身一跃,跳下万丈悬崖,与出生仅3个多月的儿子永别。年仅16岁女译电员王健、女军医韩岩,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熏死在洞里。
黄君珏,原名黄维祐,191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旧官僚家庭,然而优越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影响她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她15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参加苏区红军情报部远东情报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判7年徒刑。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在长沙开展抗日工作。27岁随爱人王默磬到了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战地文化工作。
君珏的儿子出生以后,为了便于工作,她毅然将仅仅3天的孩子,寄养到老乡家,从此孩子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母亲。
日寇在庄子岭一带的山顶上“安营扎寨”十余天,严密包围、反复搜山,分馆的同志陷入难以生存的险境。
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编辑缪乙平、黄中坚,记者乔秋远、陈达、康吾,总务科长韩秩吾,管理股长孙克温,女会计郝青芳,印刷队长董自托,女报务员万兆莲等先后在辽县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肆虐28天后,八路军主力部队转回内线,于6月19日将窜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小鬼子全部击出了根据地。
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大都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他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明天的新中国。但在这次“扫荡”与反“扫荡”中,46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最小的是勤务员魏文天,才13岁;年龄最大的是炊事员牟忠衡,50岁。
另有11位同志失踪。
这一批鲜活的新闻战士倒下了,但是华北版这个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党的舆论宣传阵地并没有垮。正当日寇在北平、东京大吹“华北共产党最大的报纸被彻底粉碎”的时候,7月1日,铅印的华北版又复刊了,发表社论《坚持敌后抗战,反对悲观失望》,再次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敌后广大军民又看到了自己钟爱的报纸,又听到了党的亲切有力的号召,一些人一度产生的消极情绪很快消除,振奋起不畏困难、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迎接黑暗之后的黎明!
太行新闻烈士们用热血和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如同巍然耸立的太行山、滔滔不绝的清漳河,永垂不朽!
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