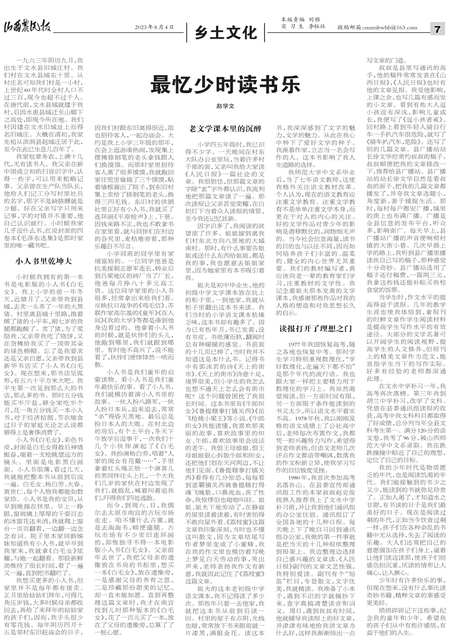最忆少时读书乐
一九六三年阴历九月,我出生于文水县旧城庄村。我们村在文水县城东十里。从村庄名可知我们村是一小村,上世纪60年代时全村人口不过三百,现今也超不过千人。在唐代前,文水县城就建于我村,后因水患县城迁至山脚下之高处,即现今所在地。我们村因建在文水旧城址上而得名旧城庄。大概在清初,我家先祖从洪洞县赵城迁居于此,至今在此已生息几百年了。
我家祖辈务农,上溯十几代,无有读书人。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扫盲识字中,认得一些字,可以用来粗略记事。父亲曾在生产队当队长,他给人们记工分写村里社员的名字,那字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好在父亲写字只用来记事,字的对错并不重要,他自己认识就行。小时候我家几乎没什么书,红皮封面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是那时家里的唯一藏书吧。
小人书里乾坤大
小时候我拥有的第一本书是电影版的小人书《白毛女》。我上小学的前一年冬天,近腊月了,父亲带我到县城,去卖一头养了一年的大黑猪。村里离县城十里路,推着绑了猪的小平车,刚七岁的我腿都跑酸了。卖了猪,为了奖励我,父亲带我吃了烧饼,又在货摊给我买了一顶带耳朵的绿色棉帽。忘了是我要求还是父亲自愿,父亲带我到县新华书店买了小人书《白毛女》。现在想来,那书店呈弧形,有五六十平方米大吧。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书店,那么多的书。那时五分钱能买半斤盐,够全家吃半个月,花一角五分钱买一本小人书,对于经济拮据、节衣缩食过日子的家庭无论怎么说都够得上是奢侈消费了。
小人书《白毛女》,彩色书皮,封面是白毛女得救后神情振奋,端着一支枪眺望远方的镜头。里面是电影黑白画面。小人书很薄,看过几天,我就能把整本书从前到后说一遍。白毛女、杨白劳、大春、黄世仁,每个人物我都能如数家珍。小人书是我的宝贝,从早到晚揣在怀里。早上一睁眼,窗玻璃上厚厚的千姿百态的冰窗花还未消,我就爬上窗台一页页翻看,一边翻一边念念有词。院子里本家同龄姊妹知道我有小人书,就早早到我家来,我就拿《白毛女》炫耀,与她一起翻看。那股新鲜劲维持了很长时间,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书翻烂了。
我想买更多的小人书,但家里并不是每年都有猪卖。正月里给姑姑们拜年,可得几角压岁钱,大多时候母亲都收回去,再给了来拜年的姑姑家的孩子们,因而,我手头很少有零花钱。每年阴历四月十五是邻村东旧赶庙会的日子,因我们村跟东旧离得很近,故也招待客人,一起办庙会。大约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在会上逛游凑热闹,发现集上摆摊修钢笔的老头拿钱跟人们换馍馍。而那时家里招待客人蒸了很多馍馍,我就跑回家往兜里偷揣了三个馍馍,贴着墙根溜出了院子,到东旧村集上卖给了修钢笔的老头,换得三四毛钱。东旧村的供销社里正好有小人书,我就买了连环画《平原枪声》上、下册。因钱来路不正,我也不敢拿书在家里看,就与同伴们在村边的旮旯里、麦秸堆旁看,那种乐趣自不尽言。
小学同班的同学里有家境富裕的。一位同学他爸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连长,转业后到吕梁地区的砖厂当了厂长,他爸每月挣八十多元高工资。这位同学家里的小人书很多,经常拿出来给我们看。反映抗日战争的《鸡毛信》、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都是凑到他身边看过的。他拿着小人书的时候,就是伙伴们的头儿,他跑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有时他不高兴了,说不能看了,伙伴们便悻悻然一哄而散。
小人书是我们童年的启蒙读物。看小人书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事。看了小人书,我们就模仿着演小人书里的故事。一伙人扮八路军,一伙人扮日本兵,追来追去,常常“杀”得昏天黑地。最后总是扮日本人的大败。在村北边的房后,有个土平台,冬天下午放学后没事干,一次我们十几个小伙伴演起了《白毛女》。我扮演杨白劳,唱着“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手里拿着红头绳正给一个演喜儿的男同伴往头上扎,一个大我们几岁的家伙在村边发现了我们,就捣乱,喊着叫着追我们,吓得我们四处逃散。
而今,到周六、日,我偶尔去太原市南宫的古玩市场走走。咱不懂什么古董,就是去淘淘书,顺便遛腿。古玩市场有不少卖旧连环画的,却惟独寻不得一本电影版小人书《白毛女》。父亲前年去世了,我把父母亲的遗像放在书房的书柜里,想买一本《白毛女》,放在遗像旁,一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二是珍藏那份甜美的记忆,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再整理这篇文章时,我才在南宫找到儿时那种版本的《白毛女》,花了一百元买了一本,放在了父母的遗像旁,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老文学课本里的沉醉
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已识得不少字。一天晚间在村东大队办公室里玩,当着许多村干部的面,父亲叫我给大家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文章。我很胆怯,但那篇文章的字除“衷”字外都认识,我流利地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那次读报让父亲甚觉荣耀,在白炽灯下当着众人读报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因字识多了,我阅读的欲望浓了许多。姐姐嫁到离我们村东北方向八里地的大城南村。那时,有什么事要告姐姐或送什么东西给姐姐,都是我的事,我也愿意去姐姐家里,因为她家里有本书吸引着我。
姐夫是初中毕业生,他的初级中学文学课本放在炕上的柜子里,一到他家,我就从柜子里翻出这本书来读。我们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枯燥乏味,这本书却有趣多了。因为已有些年月,书已发黄,没有书皮。书纸薄而软,翻阅时总有种暖暖的感觉。书前面的十几页已掉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记得书中有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天上的街市》诗意十足,境界很美,但小学生的我怎么也想不通天上怎么会有街市呢?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长时间。这本书里有《牛郎织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等小说。《牛郎织女》我能读懂,我喜欢那美丽的故事,喜欢故事里的织女、牛郎,喜欢故事里会说话的老牛。我恨王母娘娘,恨王母娘娘狠心拆散牛郎和织女,还把他们划在天河两边,不让他们见面。《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看得有几分惊恐,每每看到恶霸镇关西被鲁提辖打得魂飞魄散,口鼻流血,丧了性命,我惊悸但也暗暗叫好。姐姐、姐夫下地劳动了,在静寂的屋里读着读着,有时害怕得不敢向屋外看。《荔枝蜜》这篇文章我印象深刻,当时也不懂这叫散文,因为文章结尾写作者梦里变成了小蜜蜂,我在我的作文里也模仿着写晚上梦见白天劳动的事,笑出声来,老师表扬我作文有新意,我就因此记住了《荔枝蜜》这篇文章。
姐夫的这本老初级中学语文课本,我不记得读了多少次。那些年只要一去他家,我就把这本书从前到后读一回。村里的屋子有点阴,光线也暗,常常放下书来眼前就一片漆黑,满眼金花。读这本书,我深深感到了文字的魅力,文学的魅力。从此在我心中种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我羡慕作家,立志当一名会写作的人。这本书影响了我人生道路的选择。
我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七年语文教师,这使我格外关注语文教材改革。个人认为,现在的语文教育应注重文学教育。注重文学教育不是单单注重文学本身,而更在于对人的内心的关注。好的文学作品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当今社会信息海量,读书的目的也与以往不同,因而如何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温柔的、健全的内心世界尤其重要。我们的教材编写者,真应该向老一辈的教育家们学习,注重教材的文学性。我记念着姐夫那本发黄的文学课本,我感谢那些作品对我的人格的塑造和对我思想长久的启示。
读报打开了理想之门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随之各地也恢复中考。那时学生学习特别重视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我也跟大家一样把主要精力用于数理化的学习上。我虽然渴望阅读,但一方面时间有限,另一方面限于条件能读到的书又太少,所以语文水平着实不高。1978年秋,我以刚刚及格的语文成绩上了公社高中后,老师每次布置作文,我都凭一腔兴趣努力写作,希望得到老师表扬,但语文老师几次评点作文都语带嘲讽,数落我的作文标新立异,使我学习写作的自信极度受挫。
1980年,我首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在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的本家叔叔赵克俊找熟人推荐我上了文水中学补习班,并让我到他们通讯组的办公室住宿。通讯组订了全国各地的十几种日报。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通讯组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的十几种报纸整理到报架上。我边整理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读。《人民日报》副刊的文章文艺性强,我特别爱读。副刊有个“短笛”栏目,专登散文,文字优美,我就精读。我准备了小本子,遇到不识的字就摘抄下来,查字典搞清楚读音和词义。周日,遇到叔叔有时间,他就辅导我读报上的好文章,并津津有味地给我讲文章为什么好,这样我渐渐悟出一点写文章的门道。
叔叔是县里写通讯的高手,他的稿件常常发表在《山西日报》,《人民日报》也时有他的文章见报。我受他影响,上课之余,也写几篇有感而发的小文章。看到有些大人逗小孩没有深浅,影响儿童成长,我便写了《逗小孩者戒》。回村路上看到年轻人骑自行车一手扒汽车很危险,就写了《骑车扒汽车,危险》。还写了别的几篇文章。县广播站站长徐文华经常约叔叔的稿子,叔叔顺便把我的文章修改一下,推荐给县广播站。县广播站的站长徐文华自然是看叔叔的面子,把我的几篇文章都播发了,并夸我文章选题小,角度新,善于捕捉生活。那时,每村每户都安广播,城里的街上也布满广播。广播是全县信息的发布平台,听众多,影响面广。每天早上,县广播站广播的声音便响彻村镇的大街小巷。几次早晨上学的路上,我听到县广播里播读我自己写的稿子,那种感觉十分奇妙。县广播站选用了稿子还付稿费,一篇两三元,我拿这些钱还能补贴买些校食堂的饭票。
当学生时,作文水平的提高得益于读报。几年的教学生涯也使我体悟到,拿报刊的时鲜文章作学生阅读材料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大部分的文学名著可以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但报刊上的精美文章作为范文,能直指学生当下的写作实际。好多有经验的老师都深通此理。
在文水中学补习一年,我高考再次落榜。第三年我到胡兰中学补习,改学了文科。凭借在县委通讯组读报的收获,高考中我文科科目都取得了好成绩,总分列当年全县文科考生第一。满分120分的语文卷,我考了96分,被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我在跌跌撞撞中贴近了自己的理想,定位了自己的目标。
我的少年时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阅读饥渴的年代。我们能接触到的书少之又少,能读到的书就弥足珍贵了。正如人渴了,才知道水之甘甜,有书读的日子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现在是阅读过剩的年代,正如当今饮食过剩一样,孩子们在各种杂乱的书籍中无从选择,失去了阅读的乐趣。大人们还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们身上,逼着让他们读这读那,使孩子们倍感负担沉重,厌读的情形让人痛心,让人揪心。
少年时有许多快乐的事,但现在想来,没有什么事比读奇妙书籍、精粹文章的事感受更美好。
琐琐碎碎记下这些事,纪念我的童年和少年。希望我的孩子们从中有些许感悟,有益于他们的人生。
赵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