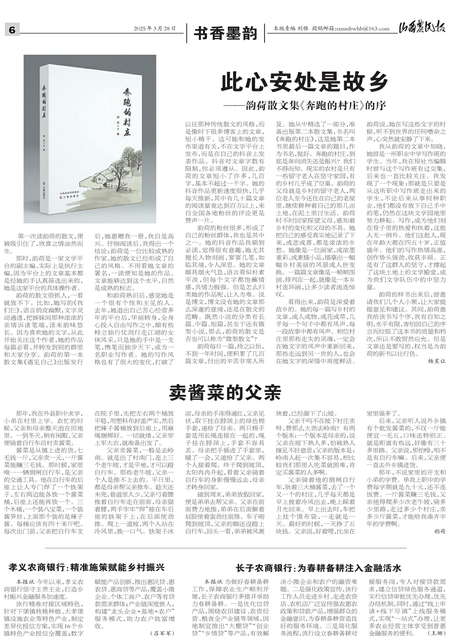卖酱菜的父亲
那年,我在外县职中求学,小弟在村里上学。农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整天泡在田地里。一到冬天,稍有闲暇,父亲便骑着自行车沿村卖酱菜。
酱菜是从镇上进的货,七毛钱一斤,父亲卖一元,一斤酱菜能赚三毛钱。那时候,家里唯一一辆倒闸自行车,是父亲的交通工具。他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让人专门焊了一个铁架子,左右两边能各放一个酱菜桶,后座上还能再放一个。三个木桶,一个装八宝菜,一个装酱笋丝,上面那个装的是辣子酱。每桶应该有四十来斤吧。每次出门前,父亲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先把左右两个桶放平稳,用塑料布封盖严实,然后把辣子酱桶放到后座上,用麻绳捆绑好。一切就绪,父亲穿上军大衣,就准备出发了。
父亲卖酱菜,一般是去岭南。就是出了村南门,连上三个老牛坡,才是平地,才可以蹬自行车。那些老牛坡,父亲一个人是推不上去的。平日里,都是母亲帮父亲推车。趁天还未亮,巷道里人少,父亲弓着腰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母亲猫着腰,两手牢牢“焊”接在车后座的铁架子上,在后面使劲推。爬上一道坡,两个人站在冷风里,换一口气。铁架子冰凉,母亲的手冻得通红,父亲见状,取下挂在脖颈上的绿色棉手套,递给了母亲。两只棉手套是用长绳连接在一起的,绳子挂在脖颈上,手套不容易丢。母亲把手插进了手套里,暖了一会,又递给了父亲。两个人接着爬。终于爬到坡顶,太阳冉冉升起,看着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身影慢慢远去,母亲才转身回家。
碰到周末,弟弟放假回家,便是弟弟去帮父亲。父亲在前面费力地推,弟弟在后面撅着屁股使着蛮劲往前推。车子刚爬到坡顶,父亲的脚还没蹬上自行车,回头一看,弟弟被风裹挟着,已经溜下了山坡。
父亲干吗不在坡下村庄卖呀,费那么大劲去岭南?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母亲的,说父亲在坡下熟人多,怕被熟人撞见不好意思;父亲的版本是:岭南人赶一次集不容易,相比较我们那里人吃菜就困难,肯定买酱菜的人多啊。
父亲骑着他的倒闸自行车,驮着三大桶酱菜,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几乎每天都是早上披着冷风出去,晚上踩着月光回来。早上出去时,车把上挂个馍布袋,一走就是一天。最好的时候,一天挣了五块钱。父亲说,好着哩,比坐在家里强多了。
后来,父亲听人说外乡镇有个批发酱菜的,不仅一斤能便宜一毛五,口味还特别正。就是距离有些远,好像有三十多里路。父亲说,那怕啥,咱不是有自行车嘛。后来,父亲便一直去外乡镇进货。
那年,不说家里的开支和小弟的学费。单我上职中的学费每学期就是九十元,还不连饭费。一斤酱菜赚三毛钱,父亲他得爬多少次老牛坡,骑多少里路,走过多少个村庄,卖多少斤酱菜,才能给我凑齐半年的学费啊。
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