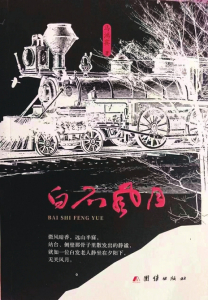为“七壮士”而歌
——长篇小说《白石风月》创作感言
4月26日,山西作家走进基层(汾阳)活动,恰逢由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院主办我的长篇小说《白石风月》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可谓是大家盈门,蓬荜生辉。下面我简要谈谈关于创作的情况,也是创作感言:
约是3年前的一天,小雪后两日。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邻居屋脊上薄薄的残雪。这时,侯荃先生风风火火来到我的院子,迅步进了客厅。我和他同是党政机关出身,与其他政界人不同的是还黏连了一身文气。每次一见面便是谈天说地,漫无边际。闲谈中既有文学认同,难免也流露出力不从心的些许惋惜和无奈。
也就是片刻工夫,他的神态喜悦起来。倏然,他从衣兜里摸出三四页复印件来,说是公安上尘封数十年的蓝色档案解密了,找到了“七壮士”抗战时期救了他们白石全村人性命的专案卷证,如获至宝。这个从衣兜里冒出来的喜讯使他的眼睛里有了神采,额头和嘴角两旁深深的皱纹里似乎也蓄满笑意。接着,他又拿出自己发表在今日头条上的《“七壮士”舍己勇救全村人》给我看。我看过之后,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写作,他想让我带上感性的笔调为迟来的英雄二度梅开,为“七壮士”尽染文学色彩。
侯荃先生是以叙事式写的,类似一则新闻报道,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想,他寄予我的希望就不光是一个故事了,而是要让读者接受更为复杂的生命信息,包括审美的快感、迷人的语言艺术智慧与思想的撞击所引发的阵阵惊讶。侯荃先生眉飞色舞的讲述越来越感染了我,不由自主已经在想是怎样一种力量使得“七壮士”舍生取义的?他们一个个年轻正气盛,在生死攸关时却没有半点彷徨,为挽救近500名乡亲的性命,视死如归?
那时,《丁香花开时》刚定稿,我筋骨气血殆尽,身体尚待恢复,如若连篇累牍再写下去,实感力不从心;然而,一想到“七壮士”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看着侯荃老兄信任和期待的目光,身体马上就像注鸡血一般,我要为“七壮士”而歌。
不能否认,侯荃确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白石风月》书中的不少故事出自他之口。这也是我对“七壮士”题材兴趣渐访渐浓的一个诱因。侯荃、任国祥、李春福、呼永庆、梁继国、冀广大、梁怀勇、冯恩启等讲述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但作品和故事是不同的,作品里肯定有故事,但仅仅有故事还算不上作品。
文体确定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战争题材,自己不熟悉。工、农、商、学、兵中,我从小上学、务农,参加工作首先是在人民公社,后在县农村工作部工作,在县财税局工作期间抽调财贸政治部工作过,可以说农、商、学都从事过,就是没有工与兵的经历。
没有参加过战争,这倒不影响我的小说创作,因为,从文学理论上说,小说作者未必要都是题材的实际经历者,主要依靠想象力来完成。一位小说作者一生写出的东西很多,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不必也不可能亲自经历的,这就要借助于作者的间接经历、经验和感受以及对人性的理解力。
肖家庄镇望春是我的出生地,所在地即那个通常汾阳人所说的“二五区”,生活、上学和工作过的肖家庄与白石毗邻。我的家乡与文湖一衣带水,与禹门河、磁窑河、文峪河有着相承的文脉。原来,今天的肥田沃土正是当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表里山河,每一片土地都留有先辈们的足迹,每一条河流都浸透着他们的鲜血。书中写“三十里铺”饭店,是以演武“二掌柜饼子坊”为背景的;写白石大集,实际上是演武庙会。我在税务局工作时,最初是在演武税务所,那时,天天早餐吃的就是二掌柜饼子;演武寿圣寺北的庙会更是税务所征收交易税的主要场地,庙会印象从那时起就成了记忆。
此外,我听过老山前线参战军人的讲述,看过不少战争题材的小说,观看过战争场面的影视剧。几种感受互补,形成艺术形象,创作既非直观又非常具象的人生阁楼。白石的故事我调动了太多情感和想象。《白石风月》第37章,我在写大汉奸吴远征沿街押送刑场时,路旁有个人说:“没听说他杀过人,好好的怎么……”这个小情节是虚构的,艺术经过挖掘和提炼,塑造的是大敌当前麻木不仁的艺术形象。
小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白石风月》中塑造了很多人物,虽然这其中也会有主要人物胡秉全、任绶勤和次要人物,但仍然有“七壮士”这一“人物群像”。前天,守林跟我谈起小说创作时说:“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如一母多胎,都要赋予生命。”我这里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何赋予?总体上我采取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对胡、任两家同时呈现的结构。《白石风月》主要讲述了胡秉全和他的儿子胡润田、孙子胡新华与任绶勤和他的儿子任国祥、孙子任宏宝两家三代人革命、创业和改革发展的故事。小说是按胡、任两家两条线走的,平行不悖,它的骨干部分,一些故事和情节就是这样形成的。
写作中,我以通俗文学中的故事讲述为主,故事都是线性的,环环相扣,一般不打乱时间顺序,尽量不让读者游离和走神。比如,从开始警长胡秉全深夜出征、村医生任光普进城送情报、日本女间谍夏蝶和汉奸吴远征出场、任绶勤冲破敌人封锁线侦察、老百姓为部队做棉衣、我军偷袭日军抢粮等,都是按时间顺序发展的。同时,借鉴了现代纯文学的写作,在故事的讲述方面就相对地走得远一些。即读者刚开始顺着它的情节往前走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板块就好像是硬生生地插了进来。两个板块有时候也会荡开一点,但不同的线索很快就会合二为一。几个故事板块当然不是简单的镶嵌,是有前后呼应。我努力争取让这些枝蔓和穿插不但不能使全书解体和垮掉,而且尽可能让读者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白石风月》在正常讲述中,时而穿插胡秉全父亲被日军打死,时而倒叙胡秉全的出生。在前面义安三眼门桥被爆炸好长时间、经过了若干章节胡秉全英勇就义、杨庆春接任后,又从三眼门桥被爆炸接写。有时候是冲破小说的边界的,时而作者站在三官庙前大发议论,时而穿插《游铁道》《夸兰嫂》《汾河在我心上流》等诗性写作,深受托尔斯泰小说的影响,当年的海明威读托尔斯泰,常常失望,恨不得站起来堵住老伯爵的嘴,让他少说一点。可是。海明威并不觉得从深处理解了托尔斯泰的伟大。托翁一旦激动起来,哪里还管什么小说的边界。
小说不可能在同一种色彩、同一种气氛、同一种节奏中进行下去,要靠内容、结构和文字去解决明暗的关系、速度的关系、节奏的关系。小说的引子,一下子就把读者吸引在日军司令官毛太君从临汾来白石站视察时,被胡秉全等伏击;紧接着,又是义安三眼桥战斗;继而是任光普、任绶勤等的情报冷战;再就是小的日军抢粮站和大的敖坡保卫战,几乎是波浪式的。我看《红楼梦》时,每一处文字几乎都不愿放弃。写几天的事情,情节不多,但会被它所吸引,这吸引力不是来自曲折的大情节,是细部,是语言,是局部的转换特别频繁。如果没有那么多细节的摆渡大的情节转折就会显得空洞苍白。《白石风月》第十九章写胡秉全抢占碉堡前面对生与死“七壮士”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将笔速调整为“内节奏”,适当穿插回忆,力求展现他们与家人的情爱、不舍以及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怀。在写胡秉全他们被告密、抢占碉堡、碉堡飘出红毛巾、于常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险取情报等情节时,我努力尽可能写的有“戏”,讲述赋予戏剧性。
因《白石风月》作品中,敌我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塑造这些人物?小说应该突出的倾向是“人物”的模糊化和复杂化,作品中的“人物”越复杂越好,比如他的性格,要由许多侧面组成,这才会是一个真实饱满的、说不尽的形象。《白石风月》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形象,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塑造的。如新民中学联欢会,从联欢会前的醉八仙酒馆里的餐战就开始了,不仅夏蝶在演戏,胡秉全更是在演戏,王彩彰、任应枢、任正全、霍四牛等也前来当配角,如同《沙家浜》智斗一场,他们演的都是政治戏。
我还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借鉴民族志,采用深描的写法,触景生情,在战争场面里不断地穿插当地民情、民俗和甚至是在一般人看来是所谓“闲笔”的奇人异事。
在构思的框架里,手里的笔随心所欲,这样的结构,自己觉得疏处不厌其疏,密处不厌其密。在夜深人静,有惺惺相惜、心灵相通的叩访和邀约,有倾诉与默契。有时候会因为某个事件的感叹与唏嘘而沮丧,有时候又禁不住为某个细节笑起来。每到灵感激荡笔不暇书时,或狂歌不休,或泪湿襟袖,悲人自悲,为主人翁的坎坷人生倾吐不平,为诸多文化人的双重人性掷笔徘徊,向苍天发出许多疑问……
千古文章事,得失寸心知。我要特别感谢白石这片土地给予我的力量与灵动,思想与激情,以及在困难时坚持不懈的韧性。所有这一切时世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的契机和历练,使我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化事业。
马鸿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