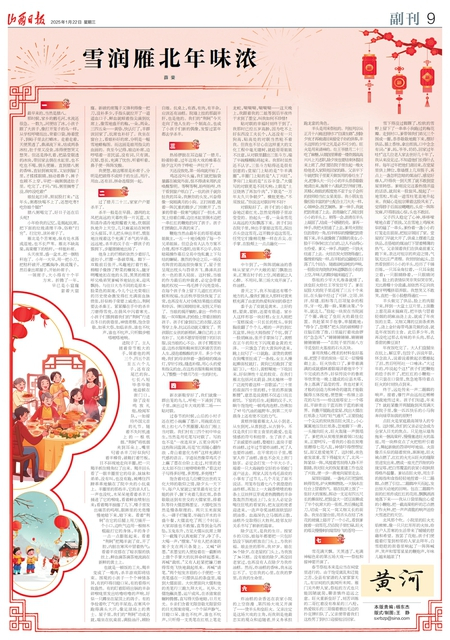雪润雁北年味浓
一
最早来的,当然是腊八。
那时候,家乡的鹅毛河,水流还很急。一数九,河便结了冰,小孩子跟了大孩子,像打开笼子的鸟一样,从学校呼啸而出,背着口袋,挎着筐子,到峪子里去打蜡冰。走着走着,天便黑透了,鼻涕流下来,结成两条冰柱,肚子里又没食,冻得便想哭又想笑。但还是挣扎着,把晶莹剔透的冰块,带回家去倒在水缸里,也不吃也不喝,倒头便睡。直到腊八粥的香味,直钻到被窝里,又钻到脑门里,才揉揉眼睛,抽动着鼻子,裤子也顾不上穿,早把一碗粥倒进肚子里。吃完了,才问:“妈,粥里搁枣了没,我咋没吃着?”
娘扯起扫帚,照屁股打来:“这年头,粥都快喝不上了,还想吃枣!吃你娘个腿!”
腊八粥喝完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小年给我的记忆,是揭起炕席,把下面的垃圾清理干净,俗称“扫穷”。扫完穷,该补席子了。
雁北是个苦寒地,纵有处水荡或湿地,也不长芦苇。雁北不缺高粱,高粱穗下的秸秆,一样能补席。
头天夜里,盛一盆水,把一捆秸秆泡了。小年一大早,用一把小刀,把秸秆破开,把瓤掏净,做成篾子,然后拿出席溜子,开始补席子。
一领席子,大小得有十个平方米。折腾了一年,早已是小窟窿套着大窟窿。新破的席篾子又锋利得像一把刀,没补多少,手指头就拉开了一道道血口子,鲜血就顺着指尖滴到炕席上,像雪地盛开的梅,一朵,两朵,三四五朵……黄昏,快认灯了,羊群该回家了,炕席也补好了。我坐在窗台上,看娘补好的席,分明是一幅雪地蜡梅图。而这画是娘用指尖的血画的。我至今记得,娘边补席,边哼唱着一首民谣,没有词,只有调,沉郁,悠长,充满了忧伤,听着听着,鼻子便一阵阵发酸。
我便想,娘这哪里是补席子,分明是把破得不成样子的生活,用汗,用血,还有泪,拼命连缀到一起。
二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要杀羊了。
杀羊一般是在早晨。凛冽的北风把高远的天幕吹得一片瓦蓝,太阳清冷清冷地照耀着大地,炊烟固执地升上天空,几只麻雀站在树梢交头接耳,羊儿把头伸出羊栏,慌张地注视着这个充满了杀气的早晨。远远地,杀羊的汉子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步履铿锵地出场了。
他身上的烂棉袄依然少着好几道扣子,拦腰一条破草绳。脚下一双鞋前后张开,风趣地打着竹板。棉帽子像掺了野菜的糠窝头,龇牙咧嘴地扣在他的头顶,黑黑的棉絮呼兄唤弟哭爹喊爷地钻出来,迎风飘扬。与往日大为不同的是原本一脸菜色的面庞,今儿个让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激发得红光满面血脉偾张,好似杨子荣要上威虎山,荆轲要去杀秦王。紧紧攥在手中的杀羊刀磨得雪亮,在晨风中闪着寒光。小孩子们簇拥着我们的“荆轲”行进在冬日的街巷里,神情肃穆,饱含崇敬,如承大祭,如临亲丧,谁也不吭声,谁也不吭声,只听脚步啪嗒啪嗒地响。
进院子了。主人搓着骨节粗大的手,领着他的两三个、四五个甚至五六个儿子,还有没尾巴的狗,七长八短毕恭毕敬地迎候在街门口,除了没有鸣 放 礼炮,检阅军队,一如接待外国元首的礼节。随着不失时机递上的一根纸烟。“荆轲”将纸烟夹到耳朵上,嘴里叼着杀羊刀好似狗叼着羊棒骨,破鞋打着竹板,目不斜视地走向羊圈,把一只羯羊抓住犄角拉了出来。羯羊回头看了一眼羊圈里它的母亲、妹妹和弟弟,没有叫,也没有跑,被缚住四蹄乖乖地躺在了院中央的小炕桌上。羊圈里的那些羊,它的亲人们,一声也没吭,木呆呆地看着杀羊刀捅进了它的喉咙,看着鲜血喷射出来;看着羯羊抽搐了几下,嗓子里发出痛苦的呜咽,眼眸里的光亮慢慢地暗下来,暗下来。看着“荆轲”在它的后腿上用刀捅开一个小口,边吹气边用一根细木棍敲打它的身体,羊的身子一点一点膨胀起来。看着“荆轲”把羯羊剥了皮,开了腔,内脏在寒风中冒着热气;看着羊皮搭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鲜血滴答滴答地流淌在新鲜的黄土上。
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羯羊变成了一堆肉,杀羊游戏即将结束。围观的小孩子一个个神情各异,有的吓得目瞪口呆,有的看得兴致盎然。有的盯着即将出锅的羊杂碎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好似一只蹲坐在屋顶上的鸽子。有的争抢着吹了气的羊尿泡,在寒风中跑得满头大汗,像足球场上的勇士。屋子里,我们的“荆轲”功成名就,端坐在炕桌前,满脸油汗,顾盼自雄。炕桌上,有酒,有肉,有羊杂,应该还有油糕。院墙上挂的那副羊肝,也是他的。我们的“荆轲”今天走向了他人生的一个制高点,也成了小孩子们新的偶像,发誓过罢年都去学杀羊。
三
热场锣鼓在耳边敲了一腊月,盼着盼着,过年这场大戏的帷幕在除夕这天终于哗啦一声拉开了。
天还没放亮,第一场戏就开始了。
鸡还没叫头遍,我们就把脑袋暴露在被窝外面,恨不得请来周扒皮唤醒黎明。等啊等啊,盼呀盼呀,终于看到窗户纸白了,一炕的孩子就你扯我的耳朵,我揪你的头发,兴奋得像一窝刚满月的小狗。正打闹着,随着一阵沉重的脚步,门帘掀开了,当爹的带着一股寒气挑回了一担水,须发上结着白霜,边往水缸里倒水边把一串红红的鞭炮扔向了孩子。孩子们便确信,年真的来了。
鞭炮当然由最年长的哥哥或姐姐做主,一五一十地分配给了每一个兄弟姐妹。但总会有人认为方案不合理,程序不透明,结果不公平,存在暗箱操作幕后交易中饱私囊上下勾结的嫌疑。激烈的争论之后,一场没有阵营的混战很快爆发了,屋子里呈现出枕头与笤帚齐飞、鼻涕共泪水一色的喜人局面。这时候,当娘的作为最后的仲裁者,必定会带着她的权杖——鸡毛掸子闪亮登场,在每个孩子身上留下几道红红的问候和祝福,生活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也再没有人对分配结果提出质疑和申诉。弹压刚刚结束,安抚又开始了。当娘的揭开躺柜,拿出一件件衣服,一双双鞋袜,扔给脸上带着泪痕的孩子。孩子们拿到自己的衣服,还没等穿上身,抗议活动就又爆发了。男孩眼红女孩的新棉袄,嫌自己的上衣有补丁。兄弟不愿穿哥哥替下的旧衣服,说当娘的心不公。孩子们哪里知道,这些衣服和鞋袜里沉积着苦苦的人生,浸泡着酸酸的岁月。多少个夜晚,我们的母亲伴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穿针引线,缝连补缀,用心头的爱和指尖的血,在这些衣服和鞋袜里缝入了整整一个腊月乃至一生的时光。
四
新衣新鞋穿好了,我们就像一群出笼的鸟儿,呼啦一下涌到了院子里,演出过年大戏的第二场——贴对联。
过春节的时候,山后的小村子还在把小碗蘸了墨汁,用碗底在红纸上扣七八个黑圈圈,贴在门框上当对联。我们村有三四个初中毕业生,当然是用毛笔写对联了。写的也不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这些陈词滥调,而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样充满时代感的语言。字迹虽然像草鸡爪子上蘸了墨在台阶上走过,村里的老太太却不住口地啧啧称赞:“看这对子写得多好哩,多黑哩,多亮哩!”
饱含着对这几位横空出世的文化大师的敬仰之情,除夕头一天下午,每户人家就让家里最有社交才能的孩子,腋下夹着几张红纸,恭恭敬敬送到有世交的大儒家里,排着队等待大儒恩赐墨宝。大儒吃饭当然是慢条斯理的。两只玉米面窝头、一碟子烂腌菜、半碗白开水的丰盛午餐,大儒直吃了两三个时辰。大家却谁也不敢催,直等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方见大儒从炕席上掰下一截篾子认真地剔了牙,净了手,大喝一声:“摆案。”早有人把杀猪的案子支在两只条凳上。又喊“研墨。”求墨宝的人便抢着在一截断砖上凿个手掌大的坑拼命研起墨来。再喊“裁纸。”又有人赶紧把镰刀磨得雪亮飞快地裁起纸来。再喊“请笔。”两个短发齐眉的小子便把一支秃笔盛在一只摆供品的条盘里,端到大儒面前。大伙便面向大儒和他的秃笔行三跪九拜大礼。礼毕,大儒饱蘸淡墨,运斤成风,在杀猪案前辗转腾挪,直写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乡亲们含着无限崇敬无限景仰的目光围案旁观,一个个屏声静气,目瞪口呆,谁也不吭声,谁也不吭声,只听得一支秃笔在红纸上笔走龙蛇,唰唰唰,唰唰唰……这天晚上,我跟着我的二姐等到后半夜终于求到了墨宝,叫我如何不珍惜!
贴对联的幸福时刻终于到了。我那时已经五岁高龄,因为吃不上好东西没工夫长个,人还没有一只狗高,贴高处的对联当然轮不着我。但我也不甘心在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中毫无建树,就趁哥哥姐姐不注意,从对联里翻出三张斗方,端了半碗糨糊贴将起来。我那时虽然还不认字,三张斗方贴得还是很有创意的:堂屋门上贴的是“牛羊满圈”,羊圈门上贴的是“人丁兴旺”,茅房门上贴的是“五谷丰登。”大儒写的对联更是不同凡响:上联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下联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横批更绝:“不须放屁。”你说这对联好呀不好?
对联贴好了。孩子们的小脸兴奋地泛着红光,忽然觉得脖子里凉莹莹的。抬起头一看,一朵朵雪花从高远的天际飘落下来。孩子们站在院子里,伸出手掌接这雪花,探出舌头尝这雪花,迈开脚步追这雪花,任凭它们像棉花糖一样在舌尖、在手掌、在脸颊上一点点融化……
五
中午到了,一阵阵胡麻油的香味从家家户户大敞的屋门飘散出来,汇聚在村子的上空,闻着就让人心醉。不用问,第三场大戏开演了:炸油糕。
普天之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的人,像我们雁北人那样对黄米糕充满了由衷的热爱和深刻的眷恋!
黍子去了皮就是黄米。上好的糕,要黄,要软,还要有筋道。家乡人这样形容一块好糕:女主人刚把一笼糕採成一只长长的枕头,举到胸前翻了个个儿,啪的一声扔到红瓦盆里,伸出大拇指按了个坑,倒了一股胡麻油,张开手掌抺匀了,黄糕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现着金黄的光泽。一只饿急了的大黄狗冲进来,跳上炕叼了一口就跑。滚烫的黄糕在狗嘴里扯成了一条线,女主人操起擀面杖就打。黄狗已经跑到了堂屋门口,一松口,黄糕唰地一下收回来,好似弹性十足的胶皮。在我们雁北包括河北蔚县、陕北榆林一带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意思是说黄糕不仅适口而且耐饥。下窑的后生,赶脚的汉子,大晌午饱饱吃一顿鸡肉泡糕,仿佛加了97号汽油的越野车,到第二天早晨身上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黄糕伴随着雁北人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从喜到悲,从古到今。不仅是我们日常主食里的最爱,也是情感的符号和纽带。生了孩子、来了亲戚要炸油糕,娶媳妇、盖房子要炸油糕,过年过节要炸油糕,死了人也要炸油糕。在平常的日子里,哪家人炸了油糕,谁也不会关上街门独享。必定会打发一个半大小子,端着一只大海碗给交好的乡邻挨门逐户送去。两家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了过节儿,几个月见了面不说话。用笼布包着七八个黄澄澄的油炸糕,再加上一大碗香喷喷的粉条土豆丝拌豆芽或者热腾腾的羊杂轰轰烈烈地送上门,女主人必定会喝住狂吼的看家狗,把友谊的使者迎进来,一迭声夸奖油糕面软馅好胡油香。血海深仇立马烟消云散,油糕外交取得巨大胜利,睦邻友好关系书写了崭新的篇章。
除夕这天,是我的生日。按家乡的习俗,娘每年都要把一只包好馅没下锅的糕放在门头上,为我祈福。娘去世的那年,我37岁。娘在36个除夕,在老屋的门头上,为我放了36只糕。没有娘的除夕,再没回老家过,也再没有人在除夕为我炸油糕。然而,炸油糕的香味,我永远忘不了。它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梦里,在我的生命里。
六
炸油糕的余香还在农家小院的上空弥漫 ,第四场大戏又开演了——烫羊头和垒旺火。父亲注定是这场大戏的主角,而我则是他最忠实的观众和追随者,并义务承担跑龙套的角色。
羊头是用来祭祖的。列祖列宗从正月十六被送到村口“自谋生路”,到除夕夜才再被请回来接受子孙的供奉,羊头这样的少牢之礼是必不可少的。旺火是用来请神的。灶王爷腊月二十三吃了麻糖,从烟囱里乘着一缕炊烟高高兴兴上天述职,除夕夜也要结束休假回来上班了,我们要在院子里生起一堆火给他老人家照亮回家的路。父亲半下午就把院子里夏天做饭用的春灶生了火,把拳头大一只小小的羊头恭恭敬敬地请出来,施展十八般武艺仔细打理,其精心细致的程度绝不亚于女子会所的技师给当红女星美容。我小朋友也像经验丰富的护士配合主刀大夫一样,心领神会,技艺娴熟。爹一伸手,我就把沥青递了上去。沥青融化了,倾注到小小的羊头上。稍等一会,沥青在羊头上凝固了,结成一个硬硬的壳。爹再一伸手,我把火钳递了上去,爹用火钳扯住沥青的一角,怕羊疼似的慢慢把沥青揭下来,羊头就像做了面膜的美女,小脸干干净净红红白白的,让人不由得心生怜爱。爹又一伸手,我就把一只铁火炷递了上去。火炷在炭火里烧得通红,像搜索残敌一样,在羊脸的边疆地区扫荡了几个回合。随着滋啦滋啦的声响,一股股皮肉烧焦的味道飘散在小院的上空,年味儿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祭祖的少牢大礼准备就绪了,该垒旺火给灶王爷发信号了。爹在屁股大的院子里巡视了三五十个来回,在头脑中经过了可研、立项、环评、报建、招标等几百项复杂的程序,牙一咬,脚一跺,果断决策:“今年,就这儿。”捡起一块炭在当院画了个圈,确定了垒旺火的最佳位置。我赶紧双手抱拳,单腿跪地:“得令了,您哪!”把头顶的破棉帽子往脑后推了推,口里敲打着戏曲锣经“急急风”:“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在院子里四面八方寻觅垒旺火基座的石头瓦块。
爹用我精心搜求的材料垒好基座,把筐子里的炭块一层又一层慢慢砌上去。旺火快收口了,爹带着满满的成就感眯着眼端详着他半个下午完成的杰作,好似传说中的鲁班爷欣赏他一晚上建成的应县木塔,身上落满了晶莹的雪。我也对爹天才般的创造力和神奇的建筑才能敬佩得五体投地,便想做一些锦上添花的勾当——给这座塔安上一个塔刹,开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境界。我撒开腿跑进堂屋,找出大儒在红纸条上写的“旺气通天”,正要捡起一个尖尖的炭块放在旺火顶上,小心翼翼地压住红纸条,忽地脚下一滑,一头撞向旺火,旺火轰隆一声倒塌了。爹把我从炭堆里揪着领口拉起来,正要呵斥,一看我的小脸在炭堆里蹭得七花八乱,神情吓得愣愣怔怔,却又慈爱地笑了。这时候,夜色愈发浓重,雪下得越发大了,北风一阵紧似一阵,风搅着雪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对旺火的恢复重建工作也没了兴致,便一步一滑地向屋里走去。
屋里好温暖。一盏电石灯把窗纸映得雪亮,炉火熊熊燃烧,一大锅水在灶台上冒着热气。娘在炕席上放了一张好大的案板,挥动一支足有四五尺长的擀面杖,把脸盆大一团豆面擀成了半个炕席大的一张纸,然后操起菜刀,切成一窝又一窝又细又长的面条。我坐在窗台前,用舌头在结了冰花的玻璃上舔开了一个小孔,看到爹披着一肩雪花,仍在院子里忙碌,旺火的塔尖慢慢刺向瑞雪纷飞的苍穹……
七
雪花满天飘。天黑透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第五场大戏——祭祖和接神要开演了。
春节祭祖本来是应当在祠堂里进行的。由于饱受离乱和迁徙之苦,全县有家谱的人家寥寥无几,有宗祠的氏族闻所未闻。雁门关外野人家,祭祖的方式也只能因陋就简,聊表慎终追远之意。旺火重新垒好了,刻苦训练的二哥扛着没有准星的三八枪,热爱娱乐的三哥揣着磨出毛边的扑克牌归队了,父亲便带着我们这些男丁到村口迎接祖宗回家。
雪下得没过脚踝了,松软的雪野上留下了一串串小狗跑过的梅花瓣。走到村口,爹带领我们弟兄三个围成一圈,恭恭敬敬地跪下来,摆好供品,插上香烛,拿出纸钱,口中念念有词:“爹,妈,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哇!”这几位老人家去世好几十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每年过年把他们请回来,在堂屋里供上牌位,靠墙摆上几双筷子,再点上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感觉好瘆人,吓得我一到天黑了就不敢到堂屋里转悠。爹刚说完这番热情洋溢的话语,就刮来一股旋风,搅起了一地雪粒,形成一道雪柱笔直地升起来。我疑心是祖宗乘着这股风来了,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吓得胆战心惊,头也不敢回。
父子四人稳定了心神,哆哆嗦嗦地点着了纸钱,又在雪地上鸡啄米似的磕了一串头,爹拎着一盏小小的灯笼走在前面,把祖宗领回了家。堂屋的门早就大开了,供桌上摆着几盘供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冒着稀薄的热气。父亲领着我们在供桌前重又跪下来,表达对祖宗的欢迎之情,气氛无比庄严肃穆。我悄悄抬起头,忽然看到那只小小的羊头,经历了千锤百炼,一只耳朵耷拉着,一只耳朵挺立着;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无比滑稽十分诡谲,却依然不忘向我龇牙咧嘴挤眉弄眼。我想笑又不敢笑,直把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羊头做完了供品,脸上的肉剔下来,拌到一大盆土豆片里,上面撒上葱花蒜末摘麻花,把半铁勺冒着轻烟的胡麻油浇上去,就成了年夜饭的主菜。又细又薄的豆面条煮熟了,浇上金针海带鸡蛋花做的卤,就是年夜饭的主食。此后多少年,我再没吃过那么有味的羊头肉,那么香甜的擀豆面!
年夜饭吃完了。大人们盘腿坐在炕上,解豆芽,包饺子,诉说年景,怀念故人,说着说着掀起衣襟擦起了泪,然后呸呸吐一口唾沫:“大过年的,咋说起个这!”孩子们把鞭炮的捻子拆开了,把红红的小鞭炮一只只装在口袋里,焦急地等待着点旺火的时刻快点到来。
终于,远处传来一声二踢脚的响声。接着,爆竹声由远而近稀稀疏疏地传过来。孩子们知道,年来了!就赶紧撒开两腿跑到风雪满天的院子里,像一匹匹快乐的小马驹奔向绿草如茵的原野!
点旺火是家庭最高领导人的专利。这时候,我们的父亲必定会成为全家人目光的焦点。只见他从墙角拖来一捆高粱秆,慢慢塞进旺火的基座,用一块桦皮点了火把秸秆引着了,舞起新做的笤帚呼呼地扇。火苗像舌头似的舔着炭块,渐渐地,旺火被点燃了,红红的火光从旺火的缝隙里迸发出来,燃成一座光芒四射的玲珑宝塔,把白雪覆盖的农家小院映照得格外温馨。爹站在旺火旁,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一只二踢脚,点燃了引信,二踢脚冲天而起,发出惊天动地的回响。包在二踢脚外面的红纸炸成红红的花雨,飘飘洒洒地落下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心爱的小鞭炮,把一截高粱秸秆的芯点燃了作火种,把一声声清脆的响声送给大雪迷茫的天空。
北风那个吹。小院里的旺火光焰熊熊,像一只只红彤彤的火烛,给庄户人苦寒的生活带来了暖暖的慰藉和希望。放罢了花炮,孩子们便提着灯笼到相邻的人家去拜年,白雪皑皑的街巷里响起了一阵阵喊声、笑声和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