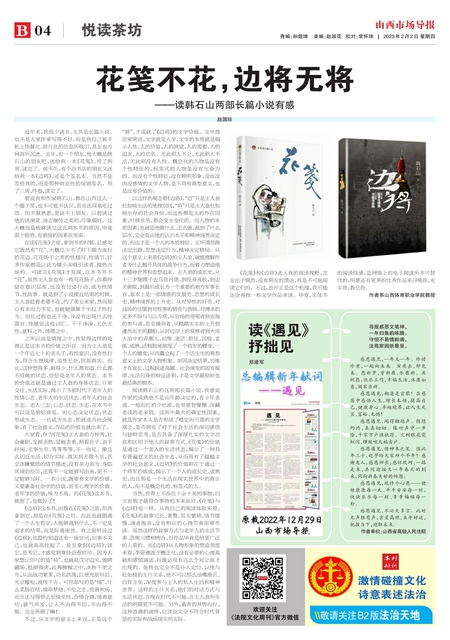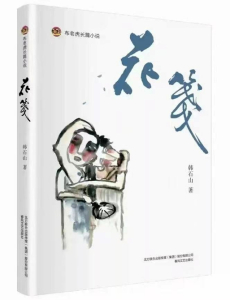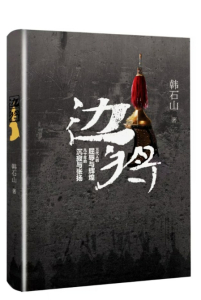花笺不花,边将无将
——读韩石山两部长篇小说有感
近年来,我很少读书,尤其是长篇小说。也不是人家作家写得不好,而是我自己被手机上快餐化、碎片化的信息所吸引,甚至也为网游所沉迷。去年,有一个朋友,他大概是韩石山的朋友吧,送给我一本《花笺》,用了两周,读完了。前不久,有个办书店的朋友又送给我一本《边将》,还是个签名本。当然不是签给我的,而是那种商业性的促销签名。用了三周,终卷,读完了。
要说我和作家韩石山,都在山西这么一个圈子里,也不可能不认识,甚至还同桌吃过饭。但不算熟悉,更谈不上朋友。以前读过他的讲演录、徐志摩传之类的,印象颇好。这大概也是能够读完这么两本书的原因,毕竟混个脸熟,有感情的因素在里面。
在读《花笺》之前,拿到书的时候,总感觉它既然有“花”,大概总少不了时下颇为流行的花边、花花肠子之类的性描写、性情节,好多作家都是以此为噱头来吸引读者、搅热市场的。可读完《花笺》才发现,这本书并不“花”,虽然主人翁也有一些花花肠子,但都停留在意识层面,远没有付诸行动,成为性情节、性故事。就是到了小说接近结束的时候,主人翁趁着老婆不在,约了美女来家,然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勉强算个半拉子性行为。而且过程也还干净,并没有出现什么性器官、性感觉这些词汇。干干净净,无色无性,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之所以说是情理之中,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正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因为主人翁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有性意识,没有性行为,符合生理规律,虽然无奈,但却真实。而且,这种想得多、做得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待做的状态,恰恰是老年人的常态。本书的价值还就是通过主人翁的身体状态、日常交往、生活实际,揭示了当前时代下老年人的性情心态、老年人的生活状态、老年人的社会生态。老人三态:心态、状态、生态,在本书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而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形成生态。一旦成为生态,那就成为社会现象,有了社会意义,作品的价值也就出来了。
大家看,作为《花笺》主人翁的方仲秀,社会兼职,发挥余热,显能卖乖,照看孙子,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像这么切近生活、切合实际、真实到无微不至,甚至涉嫌繁琐的情节描述,没有亲力亲为、身临其境的经历,还真不一定能够写出来,更不一定能够写好。一本小说,既要有文学的价值,又要兼备社会学的价值,甚至心理学的价值、老年学的价值,殊为不易。而《花笺》这本书,做到了,也做好了!
《边将》这本书,出版在《花笺》之前,但我拿到它,却是在《花笺》之后。在此也就偶遇了一个人生哲学:人能够遇到什么,不一定是追求的结果,而是际遇使然。我之前听说过《边将》,也隐约知道还有一场官司,但事不关己,也就高高挂起了。及至拿到《边将》,读它,思考它,才感觉到难怪会惹官司。因为人家想让你写的是“将”,也就是戊守边关,驰骋疆场,抵御强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而战功累累,功名浩荡,以便光前裕后,光宗耀祖,流传千古。可你却写的是“情”,什么柔肠百结,情牵梦绕,不伦之恋,荒唐欢场,而且还写得那么至情至性,合情合理,情真意切,意气风发,让人不由得不信,不由得不服。完全弄掰了嘛!
不过,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个“掰”,才成就了《边将》的文学价值。文学理论家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本质就是揭示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望,人的需要,人的追求,人的功名。无此则人不立,无此则人不活,无此则没有人性。概念化的人物是没有个性特征的,标签式的人物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没有个性特征,没有鲜明形象,没血没肉没感情的文学人物,是不具有典型意义,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这样的观念看《边将》,“边”只是主人翁杜如桢生活的地理空间,“将”只是主人翁杜如桢生存的社会身份,而这些都是人的外在因素,时移世易,都会发生变化的。而人物的本质因素,也就是他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了什么层次,完全是由他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决定的,而这才是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决定行为,精神决定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边将》的主人翁,就能理解作者为什么抛开具体的战争行为,而着力塑造他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追求。主人翁的成长史,从十三岁随嫂子去马营河堡,到投身戎机,到边关御敌,到最后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地方军事长官,基本上是一部情感的发展史,思想的成长史,精神境界的上升史。从对异性的好奇、对战场的怯懦到对性事的猎奇与放纵、对搏杀的见多不惊与习以为常,从官场的旁观者到宦海的参与者,甚至操弄者,从踏踏实实的上升到遽然而至的翻船,从河边岸上的观察者到大风大浪中的弄潮儿,幼稚、迷茫、胆怯,沉稳、老练、成熟,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将军的蝶变,一个人的嬗变,从而矗立起了一个活生生的典型意义上的文学人物形象。原因决定结果,历练才有成长,过程跃进高潮。社会演变的固有规律,生活自身的辩证法则,才是文学最原始也最经典的脚本。
阅读韩石山的这两部长篇小说,我感觉作家的成熟绝不是由年龄决定的,有少年老成、一炮而红的少壮派,也有睿智爆棚、深藏老成的老来俏。这其中最大的确定性因素,就是作家本人是否形成了稳定而可靠的文学观念,是否拥有了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切感悟与独特思考,是否具备了深厚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区别于他人的叙事方式。《花笺》的价值是通过一个老人的生活状态,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态,从而具有了超越文学的社会意义。《边将》的价值则在于通过一个将军的炼成,揭示了一个人的成长史、成熟史,而且那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真正的人,而不是概念化的、标签式的人。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物,白玉有瑕才最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花笺》与《边将》也一样。从我自己的阅读体验来看,《花笺》的叙事冗长、累赘,甚至繁琐,情节缓慢,演进拖沓,没有相应的心理节奏很难卒读。虽然这样的叙事方式与老年人的生活节奏、思维习惯相吻合,但作品毕竟是给更广泛的人看的。而《边将》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角度来看,李景德流于概念化,没有必要的心理基础和感情演进,好像必须有这么个对立面才出现的。张胜也完全不是仆人定位,以他与杜如桢的主仆关系,他不可以那么油嘴滑舌、自作主张,深度参与主人的私人生活和精神世界。这样的主仆关系,他们的对话方式与生活状态,在现在时代不可能,在主人翁所生活的明朝更不可能。另外,慕青的并辔而行,这种浪漫的演绎,应该说完全不符合时代背景的实际和战场现实的实际。
《花笺》和《边将》进入我的阅读视野,完全出于偶然,没有朋友的馈送,我是不可能阅读它们的。不过,也许正是这个机缘,我可能还会再找一些文学作品来读。毕竟,实体书的阅读快感,是网络上的电子阅读所不可替代的,但愿还有更多的优秀作品来召唤我,充实我,教化我。
作者:山西体育职业学院教授 赵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