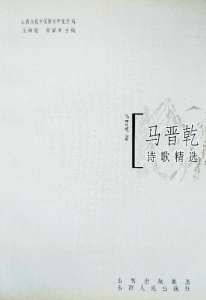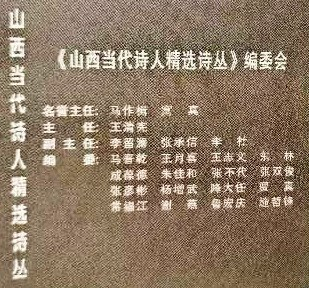提灯的人已远去(节选)
——深切怀念马晋乾先生
2020年8月12日晚上,我敬重的老诗人马晋乾先生驾鹤西去。13日下午3时,东林电话里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差不多同一时间,马老师孩子也给我发来了微信,证实了这一不幸消息。一年来他与很多诗友失联,别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期间我去山医一院和家里看过他两次。第二次见他时,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每天还坚持散步,精神也不错,我为他的健康而暗自高兴。后来,听他孩子说他已经不认识人了,粱志宏老师转来东林看望他的照片,没想到一个铁骨铮铮的人竟被病魔折磨得那样憔悴不堪,我除了伤感就是担忧。现在他离开了我们,心里还是感到突然和无法接受。
在我心中,他不应该离开我们,因为在庸碌的世俗生活中,我需要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甚至亦敌的精神导师和知音。作为他来往较多的弟子,从拜访他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我们一生的友谊。可以说他是我最理想的对话者,因为一个诗学观点,我们常常会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他给我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到人生的温暖,更重要的是他做人的风骨对我深入骨髓的影响,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不媚俗,有操守,敢于直言,宁折不弯,堪称山西诗界的良心。前几年我在他家斜对面办公时,常去找他聊天,世道人心,诗坛怪事,无所不谈。与他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想到这,悲从心来,眼前一片惘然。
我和先生合作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共同编辑《当代著名汉语诗人诗书画档案》一书。他早有此念,但又举棋不定,因为之前他应别人之邀筹办《诗中国》杂志,付出很大努力很多心血,最后不了了之。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我一起完成这项难度不小的工作。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正遭受严重挫折,又不想虚度年华,期望在文学上能有所作为,于是一拍即合。由于马老师早有考虑,他很快就起草了邀请函,随后带我赴京拜访了牛汉、雷抒雁与屠岸等诗界大家。牛汉老师第一次见面就直言直语:“这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他在八十八岁高龄时,不顾多年的腰椎劳损,不顾亲人和我们的劝阻,执意拿起放下多年的毛笔,坐在轮椅上,在膝盖上支起一块薄木板,认真地写下两幅珍贵的墨宝,让我们喜出望外。其中一幅内容为:诗是人格的影子。另一幅内容为:诗和人是我一生写的最多的字,这两个字是最为难写的,我写了一生诗,就是企望写好这两个神圣的字。我们恳请牛老师帮忙向邵燕祥先生约稿,牛老师满口答应。之前马老师给邵燕祥先生发过函,邵先生回信作了解释。牛老师后来改变了主意,提出让我们自己约。我们还是不死心,准备登门拜访邵先生。其时邵先生听力出现问题,我打通他家电话后说明来意,她爱人接的电话,说由于身体原因,只认旧朋友,不结新朋友,我们只好作罢。第二次见面时,牛老师提出一个让我们很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档案中有雷抒雁,他就不参加。实事求是地讲,雷老师对档案的贡献无人可及。我们在他家里,他从手机里一个一个地翻找诗人中的书画家,提供联系方式,没有这些珍贵的信息,工作不会迅速推进。我常想,没有雷老师,就没有《档案》。由于诗学观念上的分歧,牛老师不愿意与雷老师在一本书里见面。我感到,他们二人无法取舍,没有谁都不完整,都是遗憾。从平时和马老师的交谈中,牛老师在他心中的分量要重一些,马老师不想失去这样一位有风骨的大诗人,当时面对面谈这个问题时,也无法征求我的意见,就答应了牛老师的要求。我心里想,这可怎么办呀。《档案》出版时,两位大家都已仙逝,我都写了简短的怀念文章。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征稿接近尾声时,雷老师还未寄来书法作品,我直接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住入中日友好医院,还是爽快地答应:“我的作品随时都可以寄去”,最后还是没来得及。我们只好把他给我们个人写的字收入书中。屠岸老师是第一个寄来作品的诗人,从他这里拉开了在海内外华人中征稿的序幕。我和马老师拜访他时,他的低调和谦虚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又倒水,又签名送书,告别时站在家门口目送好长时间,当代一位真正的大儒。后来我写了《我眼中的屠岸》发表于《太原日报》,给先生寄去一张报纸。先生回复:“立世,我没有你写得那么好,就算是对我的鼓励吧。”我把这封亲笔信捐献给黑龙江一家诗歌展览馆,让更多的诗人了解学习。我们还去石家庄拜访了原河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书协副主席旭宇先生,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约请原中国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为《档案》题写了书名,使《档案》熠熠生辉。经马老师介绍,前几年就认识了山东大学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吴开晋先生。在《档案》编撰过程中,他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有成就的诗人。向吴老师求助时,往往是事不过夜,让我感激涕零,终生难忘。在马老师的引荐下,我得以与这些大家相识,有幸当面聆听他们的高见。牛汉、屠岸老师还分别为我的诗集题词。旭宇先生为我的诗集题写了书名,并赠我一幅珍贵的书法。吴开晋老师给我赠诗一首并写成书法。这些都是我此生意想不到的收获,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舞。
马老师是《档案》编委会主任,把握方向。我为主编,具体落实。除孟伟哉、韦其麟、周涛、聂鑫森、郭曰方等少数名家由他约稿外,大多数都是我通过各种办法取得联系。我约中国传媒大学陆健教授的稿子时,陆健教授又推荐了广东诗人张况,张况先生又提供了欧阳江河的电话。联系上欧阳江河后,知道他的书法已经与经销商签了合同,每年只能免费赠送朋友五幅。当年的已送完,他说自己买两幅参加吧,我觉得这不合适。后来马老师给他打了电话,果然寄来了两幅。在定稿时,我和马老师也有一些分歧。经我努力,一些诗人寄来了电子版,比如于坚,他不愿意寄书法原迹,理由是他的字只送朋友,和我们还不熟悉……每位诗人的个人简历和作品都由我选定,好多诗人的简历太长,我进行了大幅压缩。木斧先生寄来了十多首诗,我从中选了四首,在电话上与先生进行沟通时,先生当即表扬我的审美能力。马作楫教授准备了十多页诗,让我从中选择。《档案》的序由马晋乾先生撰写,我读后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序中提到的个别诗不能代表《档案》的水平,建议更换。马老师说明了他的考虑,就没动。第二条,序中提到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等一个个耀眼的明星,我建议把我和孟繁信删除。我觉得与这些大家不在一个层次,放在一块不伦不类,感到很别扭。我理解马老师的用心,他一直认为我的《夹缝》在新诗中有代表性,在我的坚持下只把我删除了。这篇序尽管有瑕疵,依然是新时期一篇重要的诗学理论文章,凝聚着先生一生对新诗的理解和探索,得到诗界如潮的好评。我在《后记》中对《档案》的编撰过程做了交代,特别提到包括马老师在内的6位诗人的历史性贡献。马老师做为《档案》一书的总策划,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最初他觉得作为编委会主任收入自己的作品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我力主举贤不避亲,没有必要错失这次难得的机遇,但最终送审时他还是把自己的作品撤了下来。马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但我们在诗歌认识上也有很多不同观点,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常常是求同存异,保留各自的意见,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知音,反而比那些可怜的应声虫更友好!
经过马老师、我及众多同仁的共同努力,《档案》如期出版,共收入174位当代著名汉语诗人的诗书画作品。这是国内首部诗书画结合的典籍,填补了中国诗歌史的空白。孟伟哉先生生前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必将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作为马先生的得意门生,我尽最大努力帮先生完成了一桩心愿,也算是对先生谆谆教诲的倾情回报。
我与马老师从相识,到深交,一点一滴,受益无穷。从写诗到做人,他都像一个提灯的人,引领着我不断前进。而今,斯人远去,音容犹在。他与我谈诗谈人生的慷慨激昂,与我共同编辑《当代著名汉语诗人诗书画档案》的点点滴滴,仍然历历在目。这美好的一切,都将成为我永远的怀念。因为公务在身,遗憾的没有能送他最后一程。我含泪写下“人走正气留,似梅兰竹菊。诗美灵魂在,比日月星辰”的悼词,和《你就这样走了》一诗:你就这样走了/在我不知道的一个夜晚/我也不知道/那晚的天上有没有星星/你就这样走了/放下了尘世的一切/包括窗台的花朵和地上的蚂蚁/还有无穷的热爱、误解和伤害/你就这样走了/带着高贵的骨头和卑微的诗歌/带着春风、秋雨和寒冷/只剩下我们对你无尽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敬重。
王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