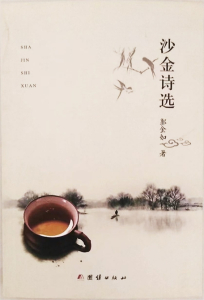淘尽狂沙见真淳
——诗人沙金素描
沙金,顾名思义,沙里淘金。出处在《关尹子》六七:“我之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矿沙之金。破矿得金,淘沙得金,扬灰终身,无得金也。”
——题记
一
初见你,是在秋天的七岭山。此时,草木葳蕤、云淡风轻,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爬山途中听得有人喊“沙金老师”,我抬头一看,正对着一双扭头回望着的深邃的眼睛,极有神韵。我一下子定格了这双眼睛,也记住了这个名字。
你剑眉深目、肤色黝黑,沉默如崖边的岩石,在一众嬉笑欢闹的人群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我怎么也无法和几年前“欢迎诗人——沙金先生”畅谈会上的那位侃侃而谈、风趣诙谐的男子看成一人。你说,你本来是不善言辞的,是大家的热情和厚爱让你成为那天的主角,实属惭愧。虽然我无缘参加那次盛会,却知道你的那首《沙金·爱》的诗一经刊出,便大放异彩,成为众人模仿套写的版本,为此你哭笑不得。你说,这首诗套写的几率太大了,换几个字又是一番风情。有诗为证——《沙金·爱》:
爱我的时候
请你把诗也爱上
就像爱树的时候
同样把果实爱上
爱诗的时候
请你把我也爱上
就像爱鱼的时候
请你一并把水也爱上
爱我也爱诗的时候
请你务必把人间爱上
就像爱云的时候
你同时要把天空爱上
没有刻意雕琢,没有华丽辞藻,敞亮的情怀跃然纸上。这样的好诗谁会不爱呢?这就是“沙金”,一个会写诗的农民。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在你的空间浏览觅足,看你的文字,看你和家人的照片。有时你会给我讲文字里的故事或者照片里的家人。你的率真、你的质朴、你的经历、你的欲言又止的隐忍,都让人产生一探究竟才可释怀的心愿。你在打工。问你干嘛呢?你不吭声,发一张戴着头盔干活的照片。你说,只有下雨,工地才休息;而雨天又阻止了我的脚步。这样一次次错过,慢慢地就过了一个季节,直到夏日的一个清晨,那天没有下雨,你又恰好休息,此时不见更待何时!我和张姐开着导航驾车一路向你的村庄驶去。
刚进了村子,远远地站着一个人,看见我们的车子,便远远地招手走了过来。是你。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握住双手,脸上都是笑意。在你简朴的小院里,几枝粉红的月季和一畦嫩嫩的韭菜正在美美地晒着太阳;六间砖瓦房亮亮堂堂,光窗户玻璃就分上中下三层,显得格外通透。正屋旁边东西两侧,各是厨房、厕所和一个储物间。我和张姐东屋进西屋出四下打量着这个离我们四十公里以外悠然自得的农家小院,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欣喜,说,你这小院不错啊!你笑了,说,还凑合吧。我喜欢干净,也爱整理拾掇。
屋里陈设极其简单,床、沙发、茶几、衣柜,各居其位。一只缩在屋角的小火炉。烟筒弯曲着伸向窗外。沏上茶,你招呼着我们喝水,随手就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茶几旁,两盆君子兰油绿绿的,煞是喜人。你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打开了话匣子。
二
谈话间,我知道,你出生在盂县西潘乡侯庄村,兄妹五个,你居中。那时候家里穷,但父母还是供你们读到高中毕业。从小就爱看闲书,爱写字,看见有意思的事情,就会记到本子上。19岁那年,你应聘到某个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同年,在《盂县文艺》刊登了你的第一组处女诗作,一共三首,其中有一首好像还有底稿,你喃喃着。说着,起身把搁在柜子上的皮箱拿下来放在茶几上。一页一页翻看着这些旧迹斑斑的文稿,像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因年代久远,纸张有的发脆,有的软塌塌的没有质感,破损严重。有些文字已经洇湿,模糊不清。诗词不多,散文小说多些。每一篇文字最后都写着日期,几乎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
在《翠翠的婚事》一文里,开头便写道“翠翠已满27了,却还没嫁,并非姑娘长得丑,也不是做了甚没脸的事,为甚老大不小还守着爹妈?芝麻庄的人都说,是换换连累了人家姑娘……”小说不长,不到三千字。一开始就似田野的馨香扑面而来,让人不由得往下读,直到读完,眼睛里还是满满的喜悦。处女作找见了,你兴奋地拿给我看,是一首小小的诗,钢笔写的,笔迹有些模糊。题目是——《羞》:
姑娘眼里
早荡起一湖秋水
却不往外流
她呀是等着情人
投一粒石子
好让溅起的水花
洗去那
满脸的羞
我读完最后一句笑着看向你。你挠挠后脑勺,不好意思也笑了。说这些都是你25岁以前写的。那时意气风发,总想好好地大干一番;后来因生活出现了变故,极大地挫败了信心,从此停笔二十几年再没写一个字。你停顿了一下说,当然,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更加重了与文字的隔阂。你似乎在平复自己的心情,又仿佛不吐不快似地滔滔不绝开来。1987年,你25岁,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一部近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书名叫《醒来的山村》。写好后,你专程去了省城太原,经一位姓李的老师引荐,把小说交给当时的《山西文学》编辑张小苏老师手里。回来后,一直等不到消息。你写信询问,张老师说,稿子整体不错,好好修改,至少可以在市级文学刊物发表,并且说,稿子已经给我寄回来了。你赶紧去问邮局。工作人员也是含含糊糊,说不出个长短。去了几次,都没能给个明确的答复,慢慢的,你也灰心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25岁,一个多么热血沸腾的年纪!刚刚褪去了青涩而还没有真正走进世俗的杂乱,生命是充盈丰盛的,眼睛是明净的。你满怀憧憬带着你的“山村”,带着你的希冀,向理想奔去,向朝阳奔去。然,仿佛是造化弄人,这篇文稿最终“折戟沉沙”,不知去向。你说,那滋味,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些年你都怎么过的?你说,很简单!种地、卖炭、打工。为了养家糊口,碰见什么干什么,没有挑选的余地。闲暇之余,麻将消遣。你自嘲,这一蹉跎就是二十来年。有人说你是“硬汉诗人”,但你说,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刚强的,在苦难面前,除了刚强,别无选择。
三
可你又开始写了。写你的村庄、你的邻舍,写你那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和你的亡妻。你的诗里有青涩时的迷茫、困顿时的倔强,是生命的沉淀,也是生命的礼赞。是啊,47岁那年,我又拿起了笔。你说,离开得太久了,终不能释怀,一拿起笔来,眼眶都湿润了。诗人刘年这样说你:
“南沟村的郭金如(沙金),应该是一个农民吧。希望他家有十来亩地和五六亩水田。若不是太远,我会帮他锄地、挑水、倒粪……”
我想,读你诗的人都懂你。懂你忙碌的身影卸掉沉重一天后的疲惫,在笔下生出的诗意;懂你的坚韧和向死而生的张力。古人有“诗言志词言情”之说。然而现代诗词,用真情写就的诗歌更有生命力和穿透力,直抒胸臆。用听得懂的话抒发心中的激情,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毫无牵强迎合之意。我手写我心,是你一直不变的初衷。比如,组诗《村里那摊子事儿》之《死对头》:
老孙头和老赵头
一辈子是死对头
两人同庚都活了大岁数
谁也没向对方低过头
前几天老孙头走了
临咽气喃喃着说
这辈子我最佩服老赵头
老赵头很少出门了
昨天我看见他攥着一沓纸
独自去了老孙的坟头
读这样的诗,会不由自主地与之产生共情,有一种未加修饰的素朴的美,泛着淡淡的泥土的馨香。你是农民,你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你熟悉村里那些一想起就永远也写不完的琐碎。你歌颂爱情、盛赞友情,对朋友肝胆相照,对农民以及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有着感同身受的悲悯情怀。你的诗歌形式多样,不流媚俗,有直入人心对社会现象的声讨和追问,有自我剖析后的觉醒和奋进。厌倦了太多乏善可陈、空洞苍白的高言大志,你的诗言简意赅、温婉灵动,有时像春风拂面草青青,有时如急雨劲风雷电鸣。
你赠我的《沙金诗集》一直摆在我的案头,闲暇时总要翻几页读读。一共三百三十首,分青涩岁月、困惑的日子、生命的沉淀、人间真情、古韵悠悠等五个辑子。我想,这一定是囊括了你前半生心血和生命的凝练谱写的人生华章。很精彩、很动人。很喜欢《也读指尖》这样曼妙的诗句:
读你我不想用眼
眼太笨拙了读不出你的深浅
读你我要把眼闭上
把眼闭上才看得更清更远
读你我用心抚摸你的文字
那山那水那轻吟浅唱
读你我必须抛开缠绕的尘世
如僧如道如佛如仙
你的温河你的山岚
你的阿婆你的牛羊
你的窑洞你的老树
你的雾你的雨
你灵动的小蛇多嘴的麻雀
你的碾碎晨雾的石碾
还有你乡下的姐妹
以及回不去的童年
读你我必须读你的标点
你芳草一样的发丝
你淡淡朦胧的眼光
你唐宋借来的衣着
你从明清复制的坠扇
你雾一样迷蒙的山水
你月亮般空灵的九曲回肠
以及你特有的手势
和站在孤独里的倔强
读你我忘了自己的孤独
我平添自然的温暖
此后再无需刻意去读你
空旷的野外到处是你的篇章
这样的诗,怎一个美字了得!像荡着涟漪的清泉汩汩地跳跃着、流动着;微风轻荡,云朵笑着飘向远方。吟诵间,定有笑意溢在心上、脸上。不信你看,在春天的诗会上,在你简陋的屋舍,还有那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他们都在大声地朗读着你的诗句。
指尖,一个行走在文字里的奇女子。去你的村子,得先经过她的村庄。你们同属一个镇,两个村子相距不过二里。虽然她已离开这个村子,但还是在《沙金诗集》的序言里这样娓娓道来:“乡下人,除去村亲,最熟悉的便是上下邻村的人,他的村子叫南沟,后来,我出走,他入住。我们曾经和正在拥有同一条干涸的河床、一条凹凸不平的道路,连绵的田地,还有星空。我一直停留在过去,他一直坚守在如今。我们在交错的时空中擦肩而过,却成为意念里无比熟悉却从未见过的故乡人。”
网名“含烟春天”在你的诗评里写道:“荷锄待旦、种瓜点豆,沙金忙碌地耕种着两块土地。一块是乡下的几亩薄田,一块是梦里的诗歌大田。”
沙金,一个会写诗的农民。平头短发,根根直立,硬朗的外形如你的诗一样透着真诚和不服输的个性。生活没有磨损你的棱角,只会愈发柔韧有光,即使有再多的沙子,也挡不住它熠熠生辉闪烁的时刻。记得有一位作家曾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还能热爱生活。”
还在打工,还在为生活奔波。你说,如果我有充足的时间,你一定专心搞创作好好搞创作,好好写诗,甚至好好写一篇小说了。你1963年生,今年应该60了。
冷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