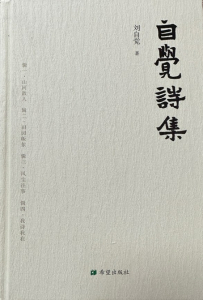生命的航标(序言)
我对文学,一直是爱好。少年没读多少书,荒了一份童子功。大学学的是政史,只在外围瞎晃悠。工作后,更是忙忙碌碌,没有在文学上有所奢望。
2016年夏天,我不慎脚踝骨折,在家待了近百天。闲来无事,看手机短信,有许多美图,就配上一两句话,发到朋友圈。大家反应热烈,这对我是个大鼓舞,于是就每天坚持写这个《看图说话》。先是一图一句,慢慢成了几句小诗。几年下来了,在朋友的鼓励下,就有了今天的诗集。
出版时因涉及版权问题,只能忍痛割了图片。没有诗画相配,减色不少。也因版幅限制,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没有办法,只能如此。
关于我的诗,还想多说几句。就当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
第一、因画而话、话里有画。
我写看图说话,既要说画的形式美感,又想说画的思想内涵,更有自己的随意想象和自由发挥。因为大多不是现场感受,也就缺少了身临其境的感染力。相对而言,我出游采风写的东西就显得血肉丰满些。
从写作状态看,多是随感而发。既是看图说话,看中的图就有话想说。更多时候,是看着图说话,所以有些诗多是即兴之作,未经反复推敲和琢磨。难怪有人说,艺术追求完美,但最终都是遗憾。
看图说话贵在诗画相配,如今虽然没有了图片,但从我的诗中,还能感受到比较强的画面感,这大概是看图说话的“胎记”吧。
第二、有韵无格、通透流畅。
诗有韵却没有严格遵守传统的格律,主要是缺少古典诗词专业训练,不过我似乎也不想让格律束缚了创作的灵性与自由。好在诗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大众也不怎么讲究格律规则,念起来朗朗上口、好听就行。当然,如果能给人回味和启迪那就更好了。
我的诗写的比较直白,这可不是刻意追求深入浅出,而是自己文学修养不足,没有足够的语词储备来修饰和表达。有多少词就说多少话,有什么样的词就说什么样的话。理屈词穷时,也可以手舞足蹈、哼哼呀呀。我后期的一些看图说话,试图打通不同的艺术形式,让它们互相弥补和印证。如看字说话、听音乐说话,看舞蹈说话等等。有时还可以用音乐来诠释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但无论如何,都是在表达一个大写的、活生生的人的感受!有一种表达是诗歌,它是我们心灵的歌!
第三、民歌元素、田园背景。
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在农村长大。童年生活和传统文化,使我的作品打上了浓郁的田园色彩。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夹着离井背乡,这个生命的底色变得越来越清晰。大山、大提琴、咖啡、窗户、西园等元素,渐渐成了我诗歌的符号和密码,嵌入我生命的河流中。
影响我诗歌写作的还有另一个元素,那就是山西民歌。
大约2004年前后,我应山西电视台《一方水土》栏目邀请,担任九集专题片《山西民歌》的专家点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对民歌也有了特别的兴趣和爱好。先后接触和研究了一些民间艺人和乡村艺术,高亢的音调、激越的唢呐,红红的棉袄、黄黄的肌肤,蒲剧眉户、华阴老腔等等,这些来自黄土高原的山、陕民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使我的诗歌更接地气、更有人间烟火味,那是农民身上质朴厚重的黄土的味道。
另外,我在大学讲授和研究西方哲学和生命美学,诗里自然就贯穿着对生命的敬畏、人性的拷问,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假丑恶现象的批判。柏拉图、尼采、海德格尔等诗性哲人告诉我,哲思是可以用诗来表达的,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
西方文化的专业背景、山西民歌的爱好以及童年农村生活经历,使我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
我自诩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虽然几经生活的磨难与打击,但依然不改初衷,并在生命之爱的乌托邦里经营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生命的活力、生存的压力与理想的张力,在我的成长中演绎着各种版本的“三国战乱”。这种内在的焦虑与冲突,使我有一种强烈表达的渴望。诗歌,或许就是唱给自己的歌,以此来安抚我那无处安放的灵魂。
人终究是孤独的过客,诗歌是我灵魂的航标。人类已进化到刷脸的时代,亲爱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在诗歌中刷出彼此的心灵来?
风也有根、心也留痕。让生活诗情画意,让你我心心相印!
刘自觉,男,1960年生于山西临猗陈家卓。农民儿子、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专著《笛卡尔》《尼采》《解析死亡》,主编青少年心理自助丛书一套(六册)。主要研究方向:生命美学。
刘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