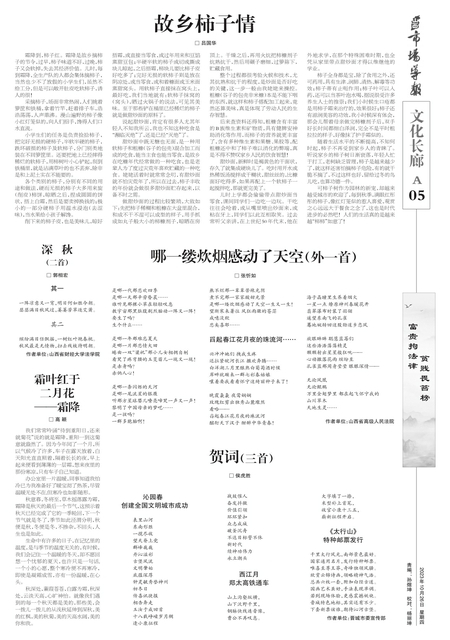故乡柿子情
霜降到,柿子红。霜降是故乡摘柿子的节令,过早,柿子味道不好,过晚,柿子又会软掉,失去其经济价值。儿时,每到霜降,全生产队的人都会集体摘柿子,当然也少不了放假的小学生们,虽然不给工分,但是可以敞开肚皮吃软柿子,诱人的很!
采摘柿子,场面非常热闹,人们挑着箩筐和铁桶,拿着竹竿,赶着排子车,浩浩荡荡,人声鼎沸。漫山遍野的柿子像小红灯笼似的,向人们招手,馋得人们口水直流。
小学生们的任务是负责捡拾柿子,把完好无损的硬柿子,半软半硬的柿子,跌坏破损的柿子及软柿子,分门别类地装在不同箩筐里。还要把地上已经摔得稀烂的软柿子,用柿树叶小心铲起,刮到铁桶里,就是沾满草叶的也不丢弃,除非是和上泥土实在不能要的。
各个类别的柿子,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做法,硬而无损的柿子大多用来旋(削皮)柿饼,晾晒之后,捏成圆圆的饼状,捂上白霜,然后是要卖掉换钱的;极小的一部分硬柿子用温水浸泡(去涩味),当水果给小孩子解馋。
削下来的柿子皮,也是美味儿,晾好捂霜,或直接当零食,或过年用来和豆馅蒸甜豆包;半硬半软的柿子或切或撕成块儿晾起,之后捂霜,柿块儿要比柿子皮好吃多了;完好无损的软柿子则是放在阴凉处,或当零食,或和着糠面或玉米面蒸甜窝头。用软柿子直接抹在窝头上,最好吃,我们当地就有:软柿子抹窝的(窝头),晒过火锅子的说法,可见其美味。至于那些铲在桶里已经稀烂的柿子就是做甜炒面的原料了。
说起甜炒面,肯定有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知我所云,我也不知这种吃食是“濒临灭绝”了,还是已经“灭绝”了。
甜炒面中既无糖也无面,是一种用软柿子和粗糠(谷子的包壳)混合加工而成的吃食,能当主食也能当零食,是故乡在吃糠年代经常做的一种吃食,也是老辈人为了度过灾荒年喜欢贮藏的一种吃食。姥姥活着时就常常念叨,有甜炒面就不怕灾荒年了,所以在过去,柿子丰收的年份就会做很多甜炒面贮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做甜炒面的过程比较繁琐,大致如下:先把柿子稀糊和粗糠在大盆里混合,和成不干不湿可以成型的样子,用手抓成如丸子般大小的柿糠剂子,晾晒在房顶上。干燥之后,再用火炕把柿糠剂子炕熟炕干,然后用碾子磨细,过箩筛下,贮藏食用。
整个过程都很考验火候和技术,尤其炕熟和炕干的程度,是炒面是否好吃的关键,这一步一般由我姥姥来操控。粗糠(谷子的包壳非米糠)本是不能下咽的东西,就这样和柿子搭配加工起来,竟然还算美味,真是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
后来查资料还得知,粗糠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健脾安神助消化等作用,而柿子的营养就更丰富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糖、果胶等,配粗糠还中和了柿子难以消化的弊端,真是不得不赞叹家乡人民的饮食智慧!
甜炒面,新鲜时是褐黄色的干面状,存久了就集成硬块儿了。吃时用开水或热稀饭汤搅拌成干糊状,甜丝丝的,比糠面好吃得多,如果再配上一个软柿子一起搅拌吃,那就更完美了。
儿时上学都会偷偷带点甜炒面当零食,课间同学们一边吃一边玩。干吃往往会呛着,或从嘴里喷出炒面来,或粘在牙上,同学们以此互相取笑。过去常听父亲讲,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他在外地求学,在那个特殊困难时期,也全凭从家里带点甜炒面才得以维继他的学业。
柿子全身都是宝,除了食用之外,还可药用,具有生津、润肺、清热、解毒等功效;柿子蒂有止呃作用;柿子叶可以入药,还可以当茶叶泡水喝,据说很受许多养生人士的推崇;我们小时候生口疮都是用柿子霜来治疗的,效果很好;柿子还有滋润美容的功效,我小时候深有体会,那会儿帮着母亲做完柿糠剂子后,双手好长时间都细白泽润,完全不是平时粗拉拉的样子,好像抹了护手霜似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知何时起,柿子不再受到家乡人的青睐了。听说家乡的柿子树日渐衰落,年轻人忙于打工,老树缺乏管理,柿子是越来越少了,就这样还害怕摘柿子危险,有的就干脆不摘了,不过这样也好,留给过冬的鸟儿吃,也算功德一件。
可柿子树作为园林的新宠,却越来越受城市的欢迎了,每到秋季,满眼红彤彤的柿子,像红灯笼似的惹人喜爱,观赏之心远远大于餐食之念了,这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吧!人们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柿柿”如意了!
吕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