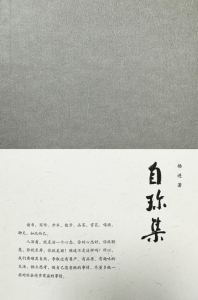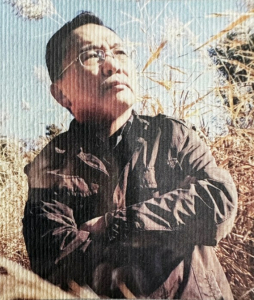敝帚千金
《自珍集》收集了我30多年来所写的部分文章。我是记者出身,然而,对出书、编书却情有独钟。这些年,我和同事出版了《明日黄花》《李双良的故事》及《寻访傅山的足迹》等新闻集子,还编辑了“启航文丛”“记者文丛”“小记者作品集”等三套丛书,共计20余册。如今,欲将这些类似于文学的东西汇集成册,我是颇为纠结的,心情也有些复杂。因为,我见证过许多书籍甫一出版就进了废品收购站的悲惨命运。
1995年,我和一位同事结集出版的新闻通讯集《明日黄花》其书名取意于苏东坡的诗句“明日黄花蝶也愁”。我担心的是,蝴蝶见了《自珍集》,是不是也会愁上眉头呢?
去年七月,我们大学同学在忻州北合索温泉度假村聚会后,在系列“美篇”的基础上,我和毛力丁、王世瑾等同学开始策划太原师专文七班毕业40周年纪念文集《岁月》。两个多月后,《岁月》问世,赞誉不断,好评如潮,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同时,一种自信与一种自豪油然而生。于是,有了编辑出版《自珍集》的想法。我想,鸡肋也好,敝帚也罢,《自珍集》里所收的六十余篇文章,毕竟是自家的心血凝成的东西。2017年,我准备出书,和陶厚敏总编说了我的想法。没有几天功夫,陶总编为我撰写的《不打不相识》就出现在我的案头。遗憾的是,陶总编已无法看到《自珍集》了。2018年立春那天,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许,他为我写的序言《不打不相识》是他最后的遗墨。
来报社前,陶总编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曾为胡耀邦写过讲话稿。1984年初,为了《太原日报》小报改大报,他受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王建功的邀请,来到太原日报社工作。第二年,我考进报社。刚见到他,我毕恭毕敬喊他“陶总”。他不让,坚决地说,“喊职务干什么?以后喊我老陶就行了”。从此,我当他的面就喊他“老陶”,而在背后始终称其为“陶总”或“陶老师”。我和老陶是忘年交,他比我大三十岁。他帮我修改论文,经常在电话中谈想法、提建议。两次撰文,为小记者队伍鼓与呼,并多次给我分管的太原晚报阳光天小记者举办讲座。他对我帮助很多,影响很大。2017年,陶总为我撰写的序言《不打不相识》在网上发表后,反响强烈,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网友折服于陶总的文笔和见识。我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忘年交而骄傲。这些年,我一直往前走着,总怕辜负了陶厚敏等前辈的殷切期望。
《写在前面的话》的作者是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他的《旧人旧事》《教授当年》和《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著作。早年,谢泳在山西作协工作时很刻苦。1997年10月4日,送我《学人今昔》时,他对我说:“你们记者比我们强,没有生活压力。我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多块,不写稿就没有饭吃。”多少年过去了,谢泳的话让我记忆犹新。那天,看了谢泳为《自珍集》撰写的序言,我很高兴。当即在微信中对谢泳说:“谢谢你的谬赞。回太原后一起喝酒。”他回答:“一定!”
敝帚千金。敝帚自珍。看了这两个成语,大家也就明白了我把书取名《自珍集》的涵义了。但愿读者见了,能够喜欢,还不至于愁上眉头吧。
本书的出版叨扰了我的一些大学同学。他们赶来捧场,给足了我面子。他们的锦绣文字,给本书增了光添了彩,我怎能不欣欣然呢?老同学郭天保挥笔为《自珍集》的封面题了字。老同学王学兰、王湄先后点评了我的诗歌。那些天,老同学牟琳琪正陪着老母亲和姨姨在海南游玩。她一边看大海、看椰子树,一边看《自珍集》的校样。本书共有五篇后记,除我的一篇外,其它四篇的作者分别是我的老同学毛力丁、王世瑾、王学兰和王瑞玺。毛力丁和王学兰既是后记的撰写者,也是《自珍集》的把关人。他们自掏腰包,将《自珍集》的电子版打印成纸质版,进行校正。毛力丁多次和我一道去18公里以外的设计公司,确定装帧设计方案,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珍集》又校对了一遍。《自珍集》付梓在即,我首先想到的是老同学和朋友们在出书过程中的种种鼓励和帮助。多少次,我坐在书房,静静地想:退休了,去哪里能寻得这么多的温暖、这么多的温馨呢?
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