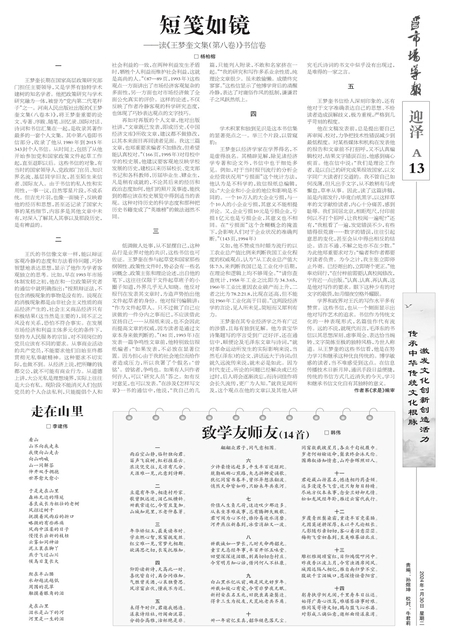短笺如镜
——读《王梦奎文集(第八卷)》书信卷
一
王梦奎长期在国家高层政策研究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又是学界有独特学术建树的知名学者。他把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被誉为“党内第二代笔杆子”之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梦奎文集(八卷本)》,将王梦奎重要的论文、专著、序跋、随笔、回忆录、国际对话、诗词和书信汇集在一起,是收录其著作最多的一套个人文集。其中第八卷即书信部分,收录了他从1980年到2015年343封个人书信。从时间上,包括了从他开始参加党和国家政策文件起草工作起,直至退职以后。这些书信的对象,有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党政部门官员、知识界名流、基层同学旧友,甚至陌生来信者、国际友人。由于书信的私人性和实用性,一事一议,自然零星片段,不成系统。但吉光片羽,也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他的经历和思想,甚至还记录了国家大事的某些细节,内容多是其他文章中未有,对深入了解其人其事以及那段历史,是有裨益的。
二
王氏的书信像文章一样,能以辩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方法看待问题、巧妙智慧地表达思想,显示了他作为学者客观独立的思考。比如,早在1993年市场体制发轫之初,他在和一位政策研究者的通信中就明确指出:“按照辩证法,不包含消极现象的事物是没有的。说现在的消极现象都是由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产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有积极结果(这当然是主要的),同不正之风没有关系,恐怕不符合事实。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不同岗位的党员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从事商业活动的共产党员,不能要求他们自始至终都贯彻无私奉献精神。这种要求不切实际,也做不到。从经济上说,把所赚的钱都交公,就不可能有商业行为。从道德上讲,大公无私是理想境界,实际上往往是大公有私。现阶段不能消灭人们包括党员的个人合法私利,只能提倡个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在两种利益发生矛盾时,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社会利益,这就是高尚的人。”(87—89页,1993年)这些观点一方面讲出了市场经济客观复杂的多面性,另一方面也对市场经济做了全面公允真实的评价。这样的论述,不仅反映了作者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也体现了巧妙表达观点的文字技巧。
再如对再版的个人文章,他对出版社讲,“文章既已发表,即成历史。《中国经济文库》所收文章,建议都不做修改,以其本来面目再同读者见面。我这三篇文章,也郑重要求编者不加修改,但希望能认真校对。”(166页,1995年)对母校中学的校史展,他建议要客观地反映学校发展的历史,建校以来历届校长、党支部书记和各科教师,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凡是稍有成就的,不论其后来的经历和政治态度如何,他们的照片及事迹,能找到的都应该在校史展览中得到适当的表现。这种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和那种把历史书籍变成了“英雄榜”的做法迥然不同。
三
低调做人处事,从不显摆自己,这种品行是业界对他的共识,这些书信也可佐证。王梦奎在参与起草党和国家那些纲领性、政策性文件时,势必会有一些名词概念、政策主张和理论论述,出自他的笔下,这往往仅限于文件起草班子的小圈子知道,外界几乎无人知晓。他反对报刊在发表其文章时,为造声势抬出他文件起草者的身份。他对报刊编辑讲:“作为文件起草人。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件分内之事而已,不应该借此宣扬自己……从报纸来说,也不会因此而提高文章的权威,因为读者是通过文章本身来做判断的。”(81页,1993年)在发表一篇争鸣性文章前,他特别致信报纸编者:“如果发表,不必放在显著位置。因为担心由于我的社会地位而给作者造成压力,所以我署了个假名:‘曾铭’。曾铭者,争鸣也。如果有人问作者何许人,可以‘研究人员’答之。如有反对意见,也可以发表。”在涉及《怎样写文章》一书的通信中,他说,“我自己的几篇,只能列入附录,不敢和名家挤在一起。”“我的研究和写作多系业余性质,纯理论文章很少。虽未敢偷懒。成绩终究寥寥。”这些信显示了他博学背后的清醒冷静,表达了对庸俗作风的抵制,谦谦君子之风跃然纸上。
四
学术积累和独到见识是这本书信集的显著亮点之一。举三个片段,以管窥豹:
王梦奎以经济学家在学界得名,不是虚得浪名。其精辟见解,除见诸经济学专著和论文外,书信中也于细处多见。例如,对于当时报刊流行的分析企业经营状况用“亏损面”这个统计方法,他认为是不科学的,致信报纸总编辑,说:“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同的。一个10万人的大企业亏损,与一个10人的小企业亏损,其意义不能相提并论。又,企业亏损10元是亏损企业,亏损1亿元也是亏损企业,其意义也不相同。在“亏损面”这个含糊概念的掩盖下,会影响人们对于企业状况的准确判断。”(143页,1994年)
又如,他不赞成当时颇为流行的以工农业总产值比例来判断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权威观点,认为“从工农业总产值大体7:3,来判断我国已是工业化中后期,在理论和逻辑上均不够周全。”“请你查查统计,1958年工业之比即为34.3:65,1960年工业比重因农业破产而上升,二者之比为78.2:21.8,比现在还高,但不能说1960年工业化高于目前。”这两段经济学的言论,见人所未见,简短而又犀利有力。
王梦奎在其专业经济学之外有广泛的涉猎,且每有独到见解。他为袁宝华诗集题写的序言受到广泛好评,还在通信中,顺便论及毛泽东文章与诗词,“就对革命运动所发生的实际影响来说,当然毛(泽东)的论文、讲话远大于诗词;但就久远流传来说,就未必是如此。因为时代变迁,所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已经过时,后人将会逐渐淡忘,而诗词佳作将会长久流传,更广为人知。”就我见闻所及,这个观点在他的文章以及其他人研究毛氏诗词的书文中似乎没有出现过,是难得的一家之言。
五
王梦奎书信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于文字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给读者造成误解歧义,极为重视,严格到几乎苛刻的程度。
他在文稿发表前,总是提出要自己再审阅、校对,力争把技术性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对某些媒体和机构在发表他的报告和文章前不打招呼,又不认真编辑校对,结果文字错误百出,他感到痛心疾首。他在信中说:“我们是理论工作者,是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国家,以文字同广大读者打交道的。我不管自己如何浅薄,但凡出手文字,从不敢稍有马虎懈怠,草率从事。因此,读了这篇讲稿,虽是内部发行,毕竟白纸黑字,以这样草率的文字献给读者,内心十分痛苦,感到耻辱。我们同居北京,相距咫尺,付印前何以不打个招呼,让我校阅一遍呢?”还有,“我粗看了一遍,发觉错误不少,有些错得很荒唐……数字的错误,往往引起意思的变化,甚至会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语言不通、不解之处亦不在少数。”为此他郑重要求对方:“编者和作者都要对读者负责。为今之计,我主张立即停止外寄。已经寄出的,立即寄个更正。”他奉劝同行,“在付梓前需要认真校阅修改,宁肯迟一点出版。”认真、认真、再认真,这是他对写作的要求。眼下这种少有的对文字的敬畏,如月缀夜空格外耀眼。
学界和政界对王氏的写作水平多有赞赏。这些书信,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他对写作艺术的追求。书信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名篇佳作代有流传。远的不说,就现代而言,毛泽东的书信以其思想深刻、虑事周全、表达恰当婉转、文字简练至极的独特风格,为世人称道。从王梦奎的这些书信看,他是在努力学习和继承这种优良传统的。博学敏感的读者,当不难感受到这点。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通讯手段日益便捷,传统的书信方式几近消失的今天,学习和继承书信文化自有其独特的意义。
作者《求是》编审 杨柏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