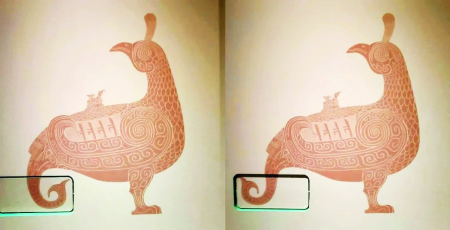晋侯鸟尊的前世今生
晋侯鸟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的杰出代表。这件器型精美的文物寄托着晋侯燮父镇守疆土、拱卫周室的政治情怀,也激励着晋国君臣励精图治,谋求百年霸业。深埋厚土之下3000余年的晋侯鸟尊在世纪之交盗墓之风盛行的岁月里重见天日,后经文物工作者修复得以展出,与公众见面。而关于鸟尊尾部的形状,争议持续颇久,表现了考古学者的求真探实之心。
唐风晋韵:鸟尊背后的晋国史
当我们走进山西博物院的“晋国霸业”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文物正是晋侯鸟尊。走近细观,会发现其器型似一只回眸凤鸟,头部微昂,高冠直立,鸟中之王的高贵身份一目了然。鸟身多以羽片纹为饰,两翼及双腿则为云纹。通观,鸟尊禽体丰满,线条流畅,两翼上扬,轻轻卷起,似欲迎风飞翔,却又恋恋不舍。以鸟为原型的先秦文物甚多,这与先民们多认为好些鸟是神圣的生灵有关。对此,先秦典籍多有记载。《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国语·周语》则载“周之兴也,鸣于岐山”,这便是著名的凤鸣岐山之典故,因而周人形成了凤鸟信仰——作为周初重要封国的晋国,也深受凤鸟信仰的影响。
晋侯鸟尊的器型还融合了象的元素,体现出晋国工匠的巧妙设计。从后方观察鸟尊,以凤尾为象首,可见象鼻自然垂下,又以凤翼为耳,鸟尊便好似变成一只大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据学者考证,商周时期大象曾经分布于黄河流域。《吕氏春秋》曾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后来由于人类过度捕猎及气候转凉等因素,大象分布范围逐渐南退。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曾以“大象的退却”为题出版了一本中国环境史专著,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大象栖息地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南退。考古研究也证明包括今日晋南在内的华北地区曾经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大象等动物的生存,且当时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的交往逐渐频繁,晋国工匠见到大象并将其形象设计于青铜器之中,不足为奇。然而,在同一件文物中巧妙融合鸟和象两种动物的形象,还是令人叹为观止。
晋侯鸟尊的盖钮为一小鸟,它与回首之凤鸟四目相对,静静相依。西周行分封制,晋国也是周初封国之一,二鸟相望仿佛象征着周王室与晋国的密切关系。晋国是周初重要封国,第一代晋侯为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据《史记·晋世家》载: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这便是“桐叶封弟”的故事,其本为年幼的成王与幼弟叔虞的孩童之戏,却被史官记录而“成真”,并以之告诫天子“君无戏言”。或许司马迁也是要借此宣扬春秋大义与史官秉笔直书的操守,另《吕氏春秋·览部》等古籍亦有相关记载。唐国本是位于今天山西西南部的一个古老方国,周初三监之乱时它也曾参与,后被周公平定。周王室遂把这片土地封给叔虞以立邦建国,叔虞也因此被称为唐叔虞。另因此地有一晋水,故唐国也称晋国。
鸟尊的盖内与腹底皆铸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其中“向”通“享”,有“贡献”之意,“太室”为宗庙,因此可以判定鸟尊为西周诸侯国礼器。因该文物出土于晋侯夫妇合葬墓,难以判断其属于晋侯还是其夫人。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根据“晋侯”称谓、出土墓葬规制及乐器、金属兵器等随葬品判断,此器属于晋侯燮父,即晋国的第二代君主。
唐叔虞与鸟尊的主人燮父父子二人不负天子所托,励精图治,镇守河汾之地的一方沃土,使之成为周王朝重要的诸侯国。直至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终无道而失其位,西周的都城镐京也被焚毁,晋国是护送新即位的平王东迁洛邑的三个诸侯国之一,为周天子立下汗马功劳。不久后,晋国逐渐崛起,直至献公、文公时开疆拓土,匡正天下,终于开创霸业。
重见天日:晋侯鸟尊的出土与修复
晋侯鸟尊及其相关文物的显赫前世在20世纪80年代引来盗墓分子的注意,因而它的今生非常坎坷,发掘和修复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
晋侯鸟尊出土的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位于山西省曲沃县境内。该墓地最早发现于1963年,起初被学术界认定为以西周晚期遗存为主的重要墓葬。1979年,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率领山西考古工作者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对曲村-天马遗址及附近墓葬进行深入调查与尝试性发掘,确认其为周代与晋文化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
从1980年至1992年,北京大学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通力合作,邹衡教授等学者先后6次在曲村进行发掘工作,并组织考古专业学生在现场实习,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1986年后,北大考古专业师生和山西省考古工作者不仅要从事风餐露宿、条件艰苦的现场工作,还要与盗墓分子“斗智斗勇”。有时候全副武装的盗墓分子甚至在考古队的驻地旁边安营扎寨,向考古工作者打探消息。1992年4月4日,在徐天进教授陪同下,邹衡教授去勘察该墓地的一个盗掘现场,没多久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盗洞。据现场窑工介绍,4月3日晚有两伙盗墓分子潜入墓地,甚至还发生了枪战,大批文物遭到破坏和盗卖。同年8月,包括晋侯编钟在内的部分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流落香港古玩市场,可见当时盗掘活动已十分猖獗。邹衡教授等考古工作者为抢救文物四处奔走,一方面呼吁有关部门加大重视力度,并与盗墓分子周旋;另一方面组织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和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对晋侯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从而保护了大量珍贵文物。
然而,由于当地较为偏远,保护性措施难以深入持续,猖獗的盗墓活动无法彻底遏制,许多墓葬未能躲过一劫。2000年9月,曲沃县公安部门在审理一起盗墓案件时,意外地了解到1998年曾有盗墓团伙在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范围内盗掘一座大型墓葬,盗走大量玉戈与铜器。公安民警当即将此情况上报,并通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考古工作者和公安民警带犯罪分子指认现场时,只看到一片狼藉,令人痛心。通过现场调查和分析,得知这伙犯罪分子采用爆破方式盗墓,破坏了墓葬结构,也使众多珍贵文物粉身碎骨。不幸的是,晋侯鸟尊就在盗洞附近,因此几乎被炸成碎片,特别是鸟尾部与尖喙部破坏严重,还有另一件同墓鸟尊甚至直接被炸成了粉末状。也因此,盗墓分子放弃了盗走这些“青铜渣”。
然而,考古工作者没有放弃鸟尊。他们将墓室北端残余的两堆“青铜渣”整体打包到实验室进一步清理,经辨认,发现一些纹饰特殊的残片,推测应该是同一件器物的碎片。又经过仔细收集,总共获得了100多块碎片。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经过无数考古工作者反复拼对、修补、去锈,这件惊世之器才呈现出基本器型。然而晋侯鸟尊的修复远未完成,“浴火重生”的凤鸟尾部尚残缺。
旷世难题:鸟尊的尾部该如何安放
初步修复后的晋侯鸟尊在山西博物院展出时,其尾部即象鼻处有一小段没有任何纹饰,系由文物修复工作者用其他材料暂时填充。庆幸的是,2018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整理晋侯鸟尊出土的114号墓时,从铜堆中意外发现疑似鸟尊尾部的残片。经文物专家组与鸟尊原物进行比对,确认该残片正是鸟尊尾部的缺失部分。同年4月,晋侯鸟尊赴北大参加120周年校庆特展,经现场比对,发现该残片确系鸟尊尾部象鼻处的缺失残片。深埋数千年的晋侯鸟尊终于有机会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将残片与鸟尊主体部分合二为一,考古工作者首先进行了超声清洗和热风枪烘烤,并且由专人手工进行表面硬结物和层状堆积锈蚀的清洗工作,随后在鸟尊主体上进行尾部断裂面覆土加固、打孔与内置铜芯工作,最后将尾部残块粘接好后进行了封护和做旧工作。修复工作的每一步都由专人按照流程完成,体现了文物工作者一丝不苟、认真仔细的职业操守。于是,在出土19年后,晋侯鸟尊主体与尾部残片终于完美合璧。
在修复过程中,关于鸟尊尾部残片怎么放,即“鸟尾”或曰“象鼻”,是向内卷还是向外翻,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持“向内卷”观点的学者们主要有如下理由:第一,生物学家观察,自然界中的大象其象鼻多自然下垂,并稍微内向;第二,内敛之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且象鼻内卷符合鸟尊形制以鸟为主、象为次的基本理念;第三,按照物理学和文物学的解释,“头昂尾收”更符合力学平衡原理,可使该器物更为协调稳定。而持“向外翻”观点的学者们也有着有理有据的论点:一方面,象鼻属鸟尾的一部分,尾巴外翻更符合自然状态下鸟儿的生活习性与形态;另一方面,按照生物学的解释,鸟类只有在寒冷、受惊等特殊状态下才会收尾,而在捕食、进攻时,其尾部则多外翻以示张扬——鸟尊属于第二代晋侯燮父,此时的晋国正处立国之初,正需要开疆扩土,因此鸟尊也应以积极昂扬的神态表示晋侯的雄心壮志,故而应为外翻。最后,鸟尊尾部还是向内卷,并得到验证。
晋侯鸟尊见证了河汾之地、唐晋故国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也目睹了文物工作者为守护这份历史与文明而筚路蓝缕,考古寻根。近年来,山西博物院和社会各界文物爱好者以晋候鸟尊为原型的文创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深受民众特别是广大年轻人的喜爱,这些文创产品在助力山西文旅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三晋文化的传承。
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