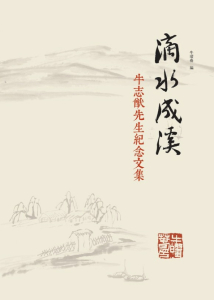慈父·良师·挚友
一本书
先父进山中学的师弟、年届八十的太原市教育界名师张奠石听到我准备为先父筹备出版诗文作品集时,很高兴,连连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是尽孝道最好的方式。办大事,前三十年看父亲,后三十年看儿子。你还是很有想法的,也很有出息,我一定帮忙。”他和先父均师从现已96岁高龄的太原进山中学名师何文。便主动邀请何老为先父说几句。并几次三番给何老的子女打电话约见。
我们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见到的何老,初见老人,极像是电视台的正规采访,老人半倚半卧,一直没有进入状态。因为怕他累着,本想着聊几句,道谢后欲离去。突然,老人却放声大哭起来:“志猷,好人呐!”
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停也停不下来,“你爸爸政治觉悟高,业务水平强,待人真诚,在进山中学和山西大学都是高材生。你父亲在当时外部环境不好,我自身状况也很难的情况下,居然勇敢地担负起给我整理书的重任。每天在我家待十几个小时,连续20多天。每个字认真地写,仔细地改。每个章节的编排、推敲,又在书成之后撰写了序言。把我饱含着辛酸的一身阅历呈现给了世人。他的付出不计一分报酬,好人呐!”
两元钱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山西大学客座教授、傅山书画院院长薛俊明先生是先父在古交授学时的学生。听到我欲为先父出书的事,他慨然提笔,撰写了一副对联:“想见音容云万里,思听教诲梦三更”。由此,可见二人的情谊。去他府上取对联时,他谈及了与先父的交往:“曜春,上个世纪60年代,我身上没有钱,吃不起饭。当时你的父亲牛志猷先生是我的班主任,给了我两元钱。曜春,你知道吗?两元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他的爱人也附和道:“您的父亲,人品好,性格沉稳,内秀,好人呐!”
薛先生出生于古交一个小山村一户贫寒人家。一直靠着自身的韧性和刻苦,才进入古交区中学。与先父相识时,他才14岁。当时,父亲也是刚刚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位于太原西山脚下的古交区中学教书,是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的结果。两元钱在如今算不得什么,可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拿出两元钱给学生,实在不少了。
“两元钱”的故事于先父其实也不只此一例。如退休前是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其时为先父学生的姚二团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及:“曾经有两年是牛老师、薛老师共同负担我的伙食费。老师听说我家的情况后,便和同住一室的薛老师商量(那时候两个老师才能分到一间宿舍),资助我读书。我们读书的年代,伙食费每个月五六块,付不起伙食费从家带干粮上学的同学比比皆是,我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完成三年的学业何其幸。五六块钱,在今天的人看来微不足道,但是那是当年老师工资的十分之一。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里孩子,付出如此爱心,老师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教授、作家刘媛媛也曾提及:“孩子两岁的时候,我先生被派去修京九铁路,偏巧赶上我们住的房子要商品化,交一笔在当时看来数目不小的钱,父母公婆不在身边,无处借贷,钱又要得急,无奈我骑车到报社找到牛老师,牛老师二话不说拿给我,那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正是经商热,大家都在集资投资,借钱给别人是有风险的,亲戚朋友之间这类事也时有耳闻。我拿着钱,嗫嚅着要写一个借条,牛老师笑着摆摆手说,等你有了就还,没有就算了。”
三头牛
先父最喜上进。小时候,先父经常教导我:“让你打算盘,你就练好一身好本领;让你去学习,你把书本倒背如流。”我之所以能以优异成绩就读大学本科,少不得先父的谆谆教诲。无独有偶,我的叔叔牛志平1962年参加高考时曾落榜,其时,先父怕他情绪低落,很耐心地劝他重振旗鼓,明年再考。叔叔自此发奋努力,于次年,一举考入山大历史系。后入陕西师大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史念海、黄永年教授,最终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于别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他小时候就学,几乎每回考试都是全班第一,有一次考了第二,便自责不已。对学习的精益求精,使他自己不论是在教书育人上,还是当编辑为他人做嫁衣上都夯实了基础。太原日报资深编辑张厚余曾提及:“我与志猷同事多年,仅在报社副刊部供职,就有十几个春秋。那时他是《知识库》版主笔,每周一期八版。他兢兢业业,日夜劳作,约稿组稿,精批细改。每期内容非常丰富,而期期都有新意,绝不互相重复。”
举凡文史,科技,天文,地理,民俗,典故……都组织安排得恰到好处。不仅读者喜闻乐见,增加了知识,而且提高了品味。他经营了十几年的这个版,月月评好稿好版面最多,年年都得到上级的嘉奖和外界的赞誉,成为太原日报副刊优秀品牌之一。
有的老先生因年迈眼花,写字不清,他得一页页照稿重抄。譬如姚青苗先生的字迹比较潦草,而且字数又多,每次志猷都是不厌其烦,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抄好,送交排印,然后再细致入微地在清样上校对改正。志猷的敬业精神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期发了几篇文章,作者姓名,文章题目,他都要清清楚楚记在编辑本上。谁得了多少稿费,也记得一清二楚,以备查问。作者文章见报,他都要寄报给本人。老先生家远难来,他都要替他们领上稿费带上报纸,送到家中。
“志猷是一位守信义,重承诺之人。在职时,所托他办的事,说到做到,从无差错。然后还要向你告知,以免挂记。记得前几年,我有几本拙作托他送给山大尊师马作楫老。他那时脚后跟疼,走路不便,我再三嘱咐他不必着急,抽空顺便去即可。谁知他不但很快就去了,而且是碰巧马老外出不在家,他一直在家门口等到马老回来,交了拙书才离开。忠诚老实的老弟,默默耕耘的老友志猷永别了,你真是一头名副其实的老黄牛呀!你‘只去耕耘不问收获’(闻一多句),但你收获多而又多,这收获就是众多读者对你的怀念和赞誉,就是无数亲友对你的惦记和纪念。你永远活在真善人的心中,即将杀青的君之作品,就是一座永在的丰碑。”
无论在教学中认真批改学生作业,还是积极对待学生的提问,在报纸的编辑中对每个标点符号的推敲,无人能挑出毛病,以及退休后被聘请到《山西大典》当编辑,用兢兢业业来形容,恰如其分!我理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事情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精神。在他刚参加工作,在古交区,当人民教师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他和校友自己动手。没有乐队,他自制乐器。没有教案,他自己油印,创造性地开展教师工作。80年代初到了报社后,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寻找新知识的领域,他对自己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开办了《知识库》《科技苑》《双塔》等许多新专栏,给一群如饥似渴的读者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尤其《双塔》专版,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创刊,历经四十多年,如今成为《太原日报》的一个品牌和业内认可的品质专刊,省城资深编辑介子平先生曾评价:“我认为《双塔》当年是省内最好的几家副刊之一。‘双塔’整体水准之高,国内可数,而牛先生在此起到过不小的作用。”这可为先父身上的拓荒牛精神作一个完美的注解。
除此,还有许多为先父点赞的作者,他们有德高望重桃李遍天下的名师;有同窗共读彼此相扶相助的同学;有共事多年彼此肝胆相照的同事;有同气相求舞文弄墨的同道;有血缘相通骨头连筋的同胞;有传道授业功成名就的学生。他们的作品无不饱含着深情;无不扼腕叹息,但所有的内容就是三个字“牛精神”,这也道出了我出版此文集的初衷——不忘祖先;不失善良;不负韶华。
亲爱的父亲,您虽然走了,但您留给我们的这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我将传承下去!
父亲,愿有来世,再做您的儿子。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牛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