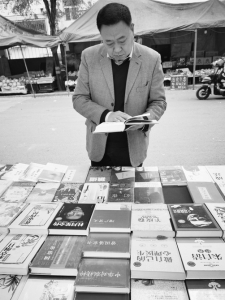母亲的“口信”
我写母亲,写的是亲情、是心灵的独白,是母亲过往的真实,也是无尽的思念。
母亲生在战火弥漫的年代,别说读书,就连吃饱饭也很困难。因此,母亲的少年就无书可读,无学可上,只会勉强写自己的名字。但是母亲行事干练,说话有理有据,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求人不如求己”,从这些日常用语,就可看出母亲的为人,而她的这些话也深深影响着我们。
1972年12月,大哥应征入伍,到了新疆边防九团,和家人交流只能书信往来。刚到部队,远离故土,大哥思念父母,不间断写信汇报在部队的情况,以免母亲惦念。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思念不已,收到大哥信后,找本家的全文兄代读代写。生产队不能缺勤,帮忙写信只能靠雨雪天或晚上,母亲说一句写一句,写完后,全文兄从头到尾念几遍让母亲听。年复一年,母亲的“口信”一写就是十五年。
信寄走后,母亲扳着指头数日子,盼着邮递员来村投递,经常站在大门口遥望。看到邮递员范世明从石坡道缓缓走来,母亲就快步走去询问有没有大哥的信。有的话母亲兴奋不已,没有的话就茫然空荡。那时,邮递员是最受母亲欢迎的人。一封封跨越天山的来信,成为母亲时时刻刻牵挂的欣喜,山村的小王庄石坡道,也谱写了军民的故事与邮递的传奇。
儿子当兵,母亲会牵肠挂肚,有一段时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大哥所在边防九团担负着边境的防卫作战任务。大哥一段时间未给家写信,家人十分惦念,放心不下。过了一段,大哥回了信:“亲爱的母亲,您和父亲不用对儿太牵挂,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当兵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
当时,母亲因想念大哥,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里偷偷抹泪,曾经和大哥一起当兵的战友回乡探亲,来家看望父母,母亲见到这位大哥的战友,抱着放声大哭。此间,大哥的战友只好转移话题,看着挂在墙上的照片说,“阿姨,你儿子兴荣很优秀,刚刚成为党员,已任代理排长……”临别时,母亲一直恋恋不舍,送了很久很久。
1980年12月,我也如愿参军。到部队后第一封家信的内容是:亲爱的父母,离开家当兵,是我读高中时的追求,更是我对解放军的崇敬和信仰,既然选择了,就安心服役。
母亲收到信后,还是找全文兄代写。母亲在回信中说,儿子你离开家快两个月了,你是十二月二日离开家的,你走时,父母亲没有送你到公社,也未参加公社欢送的新兵座谈会,父母亲心里也有愧疚,主要是不想耽误集体劳作。不过,你走后,爸和妈时常也想念,现在好了,武装部的干事来家说我们家是“双军属”了,一时总有说不完的激动和高兴。在家时,你懂事听话,从不让妈操心,你寄回的照片我们收到了,全家人都看了,看你站在雪地中穿着军装大衣那英姿飒爽的样子,都说你变得更成熟了。儿子啊:万事开头难,说心里话,很感谢部队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加油吧,为你鼓掌。
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思想总是受到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部队这座大熔炉,给了我兄弟展现自我的机会,我虽没大哥军龄长,但我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积极上进,不怕吃苦受累,无论连队大小工作抢着做,勤奋学习等。大哥先后入党提干,我进修学转业技术。这些进步出于自身的努力外,归根是部队的培养,父母亲的教育,每当取得荣誉时,我们兄弟俩即刻写信告诉父母亲。
母亲一生省吃俭用,不乱花钱,家养鸡下蛋后,积攒够一斤就卖,卖了的钱为儿子买信纸,邮票和信封,剩余用于购盐油酱醋。家里有啥困难,绝对不能让服役的儿子们知道。她曾因患结核病住院,但每次的信中,老是说家里一切很好,不要惦记,再三叮嘱好好干,要给家争光。
母亲一封又一封的“口信”,十几年如一日。虽看不见妈的表情,但炽热的爱,却在字里行间涌动。
我1984年退伍,刚返家时帮母亲整理旧物,发现小柜内存放多年的“宝贝”信件。轻轻翻着泛黄的旧信,读着大哥和那些似曾相识的文字,依然亲切,恍如隔世,我不禁怀念起写信、读信的岁月,瞬间,母亲珍藏着的这些旧信,忽然戳中了我的泪点……
母亲在世时告诉我,时代在变迁,儿子你要把旧信整理归类,这些全是你们在部队的人生阅历。妈未给你们留下物质财富,这一大堆“宝贝”旧信,作为母亲的一笔精神财富传下来吧。
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社会进入网络时代,通讯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互联网把天南地北的距离都拉得那么近,仿佛隔着屏幕就可以触摸到对方,电子媒介也让人们远离了那个书信传情的年代。母亲的“口信”时代,将成为永远的历史,但那段母亲口信的岁月,将永远留在我们兄弟心灵深处。(作者:原晋中市环境监察支队 张仁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