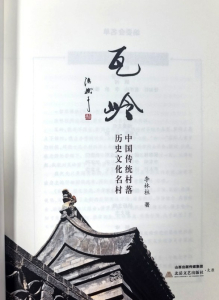《瓦岭》: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倒影
城市柏油马路上的穿行,让月华在脚底匆匆忙忙、毫不留情、冷冰冰地一滑而过。一路忙忙碌碌的行旅,倦怠之隙,一脸慵懒,十分疲惫,百无聊赖,静静地蛰伏在所谓的“宅”里,眼眸里倒映出的常常是老村文化长河里过往的点点滴滴,覆盖着的常常是眷恋悠远故乡的一往深情,望见的常常是思绪演绎出的淳朴的家的风景,体味的是“家”的那份难以名状的宁静,荡涤的是渐渐清澈的心灵。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出门在外,常常被人问及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自不必说;第二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最不好回答。不着边际的回答或者回答欠妥是会招人讨厌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做如下处理:上下邻村的人问,我回答是瓦岭的;离开了乡里,我回答是东回的;离开了县域我回答是平定的;走出山西我回答是山西的……惭愧、没有出过国,就遑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了。
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不经意间总会捕捉到一些触动灵魂的问题,难免会一直追寻下去。特别是年岁一日长乎一日、天命之年又先后两次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挫折之后,不用别人问,自己就常常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同时又增加了一个“我最终会到哪里去?”的问题。对这几个问题的追寻有时还颇感紧迫。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生,用什么也买不来;死,用什么也买不走。既然生和死对谁都一样公道,那就不如积极面对人生的意义和死的价值。
尽管有如此的觉悟,但每当思绪不由自主、触及到这个问题时,还总是剪不断、理还乱,雾水一头,懵懵懂懂,继续周而复始地、努力地剪、努力地理。
想到先前的时候,乡民外出谋生或者吃粮当兵,离开家乡时,总会用红布抱一撮黄土揣在怀里,意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掏出来闻一闻,就能适应哪里的水土;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掏出来闻一闻,就有家在身边,就不会想家;有它在身边,无论走到哪里,就和在家里一样。这里面虽然有一定的物理学抑或其它学科的原理,但最多的还是一种家、以及家乡的情节在作祟,用现在时髦的话讲,是一种乡愁。
思考得多了,笨拙的人有时候也会生发出灵感的。
戍鼓断行人,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且未休兵。(《唐·杜甫·月夜忆舍弟》)在安史之乱中,杜甫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既怀家愁,又忧国难,常常感慨万端。稍一触动,千头万绪便一齐从笔底流出,所以把常见的怀乡思亲的题材写得如此凄楚哀感,沉郁顿挫。明明是普天之下共一轮明月,本无差别,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明明是作者自己的心理幻觉,偏要说得那么肯定,不容置疑。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宋·陆游·示儿》)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老子!
肖邦,在19世纪初,因波兰落到了俄国的手里,不得不离开波兰来到巴黎。18年后,肖邦的肺结核病突然复发,弥留之际,他希望在死后,他的姐姐能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他要长眠在祖国的地下。
那曾经惊天地、泣鬼神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也有同样的遗愿:“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很难想象,这些如雷贯耳的政界和艺术界名流到最后,无比留恋的还是他们的家乡,还是他们的父亲、母亲。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常念叨的这几句话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灵魂。
富有时不忘家乡,贫穷时故土难舍。看来,古今中外的、提刀耍枪的、舞文弄墨的、算数唱曲的,概莫能外。财富有多种多样,我在物质上虽然失去了许多许多……更谈不上富有,但所幸还没有泯灭灵魂、失去思想、丢掉理想。
心存仁德之念,不在利禄功名。我就像一棵树,无论高大、还是渺小,树干移走了,根却永远留在——瓦岭——这方土地上;其枝、其叶也最终会永远落在——瓦岭——这方土地上;最终将永远静静地眠在父亲和母亲的脚下。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我虽然无法“高千尺”,但也一定不能“忘根”,不能忘自己的故乡,不能忘自己的乡亲,更不能忘自己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在生育了我的同时又给予了我太多太多……我没有理由不尽己所能,用自己的思想迸发出的智慧火花,用自己的心智闪现出的明慧灵光,把附着在瓦岭这方水土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门一户、一砖一瓦、以及附着在这些山、水、草、木、门、户、砖、瓦之上的遗迹、遗物、风情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实实在在展示出来,昭示于世人,让人们从中发现他的美,说出他的美,进而热爱他的美,弘扬他的美,权作对家乡的一种“反哺”吧。
文人报家报国,别无长物,唯有一支笔了。虽然我算不得文人,但窃以为,相较于捐钱捐物、或者兴建实体,这种“反哺”未必能给家乡外貌的“面子”带来多么立竿见影的改变,但肯定会增加家乡“里子”的质感和厚度,让子孙后代的心里积累起更深厚的人文土壤,引起共鸣,进而生发出更多的人文关怀,热爱家乡,回报家乡,建设家乡。唯其如此,才无愧于我的这个根,我的这个家,我的父母亲大人,我的父老乡亲。
用画者的眼光看,瓦岭,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具有超凡脱俗、含蓄空灵的意境之美;用诗者的眼光看,瓦岭,是一首山水田园诗,具有恬淡自然、醇厚隽永、平和散淡的心境之美;用书者的眼光看,瓦岭,是一方楷书作品,具有结密而无间、宽绰而有余的结构之美;用乐者的眼光看,瓦岭,是一支舒缓的思乡曲,具有如丝如缕、如梦如幻、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音乐之美;对于歌者来说,悠远苍凉的歌声,些许凝重、些许悲怆,浅吟低唱间,诉说思念之幽情,凝结了对父亲和母亲无尽的眷念与牵挂,从此让心灵不再孤寂。
人世间,一切事物生命力的显现,大至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寒来暑往,风雨晦明;小至花卉的枝分叶布,春华秋实,禽鸟的飞鸣栖止,戏斗饮啄,无不符合于自然的节律。行走在这一节律之弦上的——瓦岭,正是华夏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一个节点,一个音符。
无可否认,在日新月异的城镇化面前,很多建构我们乡土记忆的文化标签正在消亡。故乡的沧桑历史正在不知不觉中消逝。每一个关于故乡的记忆即将变成一场夜话、一个笑话,甚至幻化于无形无影。我们的祖祖辈辈,传宗接代,都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有辛勤的汗水,有无奈的悲怆,也有丰收的喜悦。杨柳拂面,抚今追昔,难忘祖先、先民,不为怀旧,只在于了解历史,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对未来,我们又应该担负起什么责任?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龚自珍·己亥杂诗》)小心翼翼奉上蘸着深情和泪水著成的这本《中国传统村落——瓦岭》,权算作绿叶对根的情谊吧!
李林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