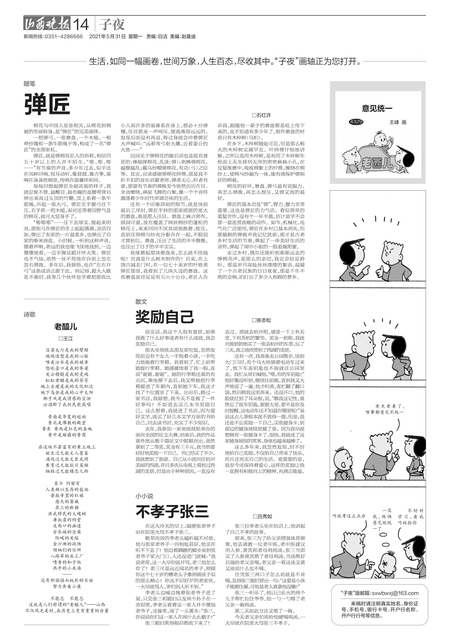弹匠
□石红许
棉花与中国人息息相关,从棉花到棉被的华丽转身,是“弹匠”的完美演绎。
一把弹弓、一张磨盘、一个木槌、一根牵纱篾和一条牛筋绳子等,构成了一名“弹匠”的全部家私。
弹匠,就是弹棉花匠人的俗称,相信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并不陌生。“嘭、嘭、嘭……”有节奏的声音,多少年过去,似乎还在耳畔回响,悦耳动听,像琵琶、像古筝,奏响在袅袅炊烟里,传唱在温馨祥和间。
每每回想起弹匠全副武装的样子,我就忍俊不禁,最醒目、最有趣的是腰带背后伸出来高过头顶的竹鞭,顶上系着一条牛筋绳,吊起一张大弓。弹匠左手握弓往下压,右手抓一把木槌,面对还带着田野气息的棉花,就可大显身手了。
“嘭嘭嘭”……压下去厚实,提起来明亮,那张弓在弹匠的手上起起落落,灵活自如,弹出了东家的一片温柔乡,也弹出了自家的柴米油盐。小时候,一听到这种声音,循着声响,老远的我也能飞快地找到,一边傻傻地看,一边手舞足蹈开怀大笑。弹匠也不气恼,依然一丝不苟地在台面上忽左忽右弹拨。多年后,我顿悟,也许“左右开弓”这条成语正源于此。尚记得,趁大人歇息不备时,我等几个伙伴也学着把那些比小人高许多的装备系在身上,想必十分滑稽,往往惹来一声呵斥,便逃离得远远的。发现后面没有再追,转过身就会冲着弹匠大声喊叫:“远看弯弓射大雕,近看姜公钓大鱼……”
民间关于弹棉花的歇后语也是挺有意思的:棒槌弹棉花,乱谈(弹);刺棒弹棉花,越整越乱;戴乌纱帽弹棉花,有功(弓)之臣等。其实,应该感谢弹棉花师傅,那是我不折不扣的音乐启蒙老师,弹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富有节奏的弹拨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余音缭绕,满屋飞舞的白絮,像一个个音符激荡着少年时代单调乏味的生活。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快到最后工序时,弹匠手持的那面圆圆的宽大的磨盘,真是惹人注目。磨盘上麻点密布,圆润可爱,放在覆盖了网状棉纱的蓬松的棉花上,来来回回不厌其烦地推磨、按压,直到压得棉与纱充分黏合在一起,不脱层才算到位。磨盘,压出了生活的平平整整,也压出了日子的平平实实。
我琢磨起那块磨盘来,怎么就不挂线呢?究竟是什么树木制作的?后来,在上饶古城北门村,在一位七十来岁的叶姓老弹匠那里,我看到了几块久违的磨盘。这些磨盘直径足足有五六十公分,老匠人告诉我,跟随他一辈子的磨盘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制作磨盘的材质只有木梓树(乌桕)。
在乡下,木梓树随处可见,但是那么粗大的木梓树实属罕见。叶师傅仔细地讲解,之所以选用木梓树,是利用了木梓树年轮面上天生排列无序的密密麻麻小孔,在反复推磨中,吸收棉絮上的纤维,缠绕在棉纱上,使棉与纱融为一体,能有效保护弹制好的棉被。
棉花的好坏,磨盘、弹弓最有说服力,再怎么弹拨,再怎么按压,又弹又泡的最好。
弹匠的基本功是“弹”,臂力、腰力非常重要,这也是弹匠的力气活。看似简单的重复劳作,没有个一年半载,估计是学不会那一套连贯流畅的动作。如今,机械化、电气化广泛使用,弹匠在乡村已基本消失,但那催眠的弹拨声我记忆犹新,那才是古老乡村生活的节奏,弹起了一串美好生活的音符,弹起了闺中小姐的一脸羞赧甜蜜。
走过乡村,偶尔还能听到渐渐远去的弹棉花声,是那么的亲切,我定会驻足聆听。那是岁月深处丝丝缕缕的絮语,温暖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日日夜夜,那是千年不绝的交响,拍打出了多少人相拥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