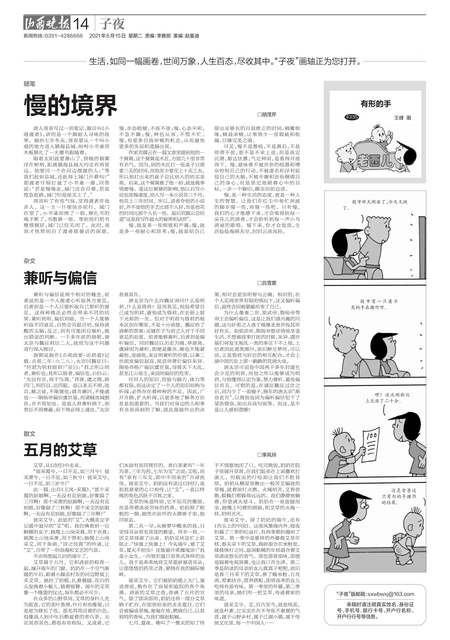五月的艾草
□李风玲
艾草,从《诗经》中走来。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此一篇,出自《王风·采葛》。“那个采葛的姑娘啊,一天没有见到她,好像隔了三月啊!那个采萧的姑娘啊,一天没有见到她,好像隔了三秋啊!那个采艾的姑娘啊,一天没有见到她,好像隔了三年啊!”
彼采艾兮。此处的“艾”,大概是文学记载中最早的“艾”吧。我仿佛看到一位婀娜的女子,她爬上山岗采葛,用于衣食;她爬上山岗采萧,用于祭祀;她爬上山岗采艾,用于灸病。“诗之经典”的吟诵,让“艾”,自带了一份浪漫和文艺的气息。
不由得想起儿时的端午了。
艾草属于五月。它和清新的粽香一起,撞开端午的门窗。奶奶在一个空气渐暖的午后,踮着小脚去村东的河边野坡上采艾草。她拄了拐棍,扎着裹腿,花白的头发挽着小鬏儿,插着银簪。端午的艾草像一个隆重的仪式,每年都必不可少。
在众多的山野草间,艾草的身杆儿尤为挺直,它的茎叶条理,叶片有些像菊,只是更为修长了些。那毛茸茸泛着的白色,很像我人到中年后酷爱着的老白茶。无论其形其色,都很有些相似。又或者,它们本就有其同理在的。老白茶素有“一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宝”之说;艾呢,则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古谚流传。彼采艾兮。奶奶没有读过《诗经》,是祖祖辈辈的心口相传,让“艾”,一直以特殊的角色活跃于百姓之家。
艾草的味道特别,它不似花的馥郁,而是带着淡淡苦味的药香。奶奶割了粗粗的一捆,她兜在前怀的大襟褂子里,抱回家去。
第二天一早,从睡梦中醒来的我,只觉得耳朵里毛茸茸的难受。用手一抠,一团艾草球滚了出来。奶奶见状急忙上前阻止:“快塞上快塞上!今天端午,塞了艾草,夏天不招虫!还能避开邪魔鬼祟!”我是小女生,一向惧怕夏日里各式各样的虫儿。我于是乖乖地将艾草重新塞进耳朵,让那悠悠的药草之香,萦绕在我的脑际额畔。
彼采艾兮。它们被奶奶插上大门,塞进席底,散布在了房屋和庭院的各个角落。清新的艾草之香,弥满了五月的空气。除了即采即用,奶奶还将一部分艾草晒干贮存,在即将到来的炎炎夏日,它们会被编成草绳,匍匐在地,燃烧自己,以其独特的香味,为我们驱赶蚊蝇。
七月,夏夜。嘶叫了一整天的知了终于不情愿地闭了口。吃完晚饭,奶奶在院子里铺开草席,任我们姐弟在上面撒欢打滚儿。但蚊虫的叮咬却让我们不胜其烦。奶奶从棚屋里揪出一根苦艾编就的草绳,就着油灯点燃。火绳明灭,艾香弥散,蚊蝇们都躲得远远的。我们静静地躺着,仰望满天星斗。奶奶在一旁盘腿而坐,她嘴上叼着的烟锅,和艾草的火绳一样,明明灭灭。
彼采艾兮。除了奶奶的端午,还有《舌尖上的中国》。这部风靡海内外、接连拍摄了三季的纪录片,有两季都拍摄到了艾草。第一季中是慈祥的外婆做艾草年糕,春天采下的艾草,捣碎混合在米粉里,揉捣捶打之间,温润黏糯的年糕混合着艾草清淡悠长的香气。那色那香那味,即便是隔着电视屏幕,也让我口舌生津。第二季是陪读的母亲给女儿做蒿子粑粑,依旧是春三月采下的艾草,掺了糯米粉、五花肉,荤素结合,营养搭配,即将高考的女儿吃得有滋有味。第一季里的外婆,第二季里的母亲,她们用一把艾草,传递着家的味道。
彼采艾兮。艾,自古至今,就是纯美,就是朴素,它实实在在不夸张不奢靡的气质,属于山野乡村,属于江湖小镇,属于传统文化里,每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