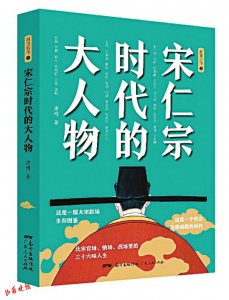精选海量文献,精准还原历史人物原貌,《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节选——
我和我的时代
《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唐博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宋仁宗时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大人物,他们正是群星闪耀时。本书用风趣、接地气的笔触讲述了宋仁宗身边和周边的男男女女——皇后妃嫔、文官武将、公主宦官、科技巨匠、文人墨客、敌国首领等,既有宫廷的逸闻趣事,又有朝堂的勾心斗角;同时蕴含了作者对他们人生际遇的感同身受,以及从中总结的人生经验和思考。36个大人物的人生轨迹,共同绘就了宋仁宗时代与众不同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画卷,呈现出一幅立体丰满的“清明上河图”。
我是赵祯,若干年后,他们尊我为“宋仁宗”。整个宋朝,就数我在位最久。四十二年皇帝时光,足够写好几本书,称得上是一个“时代”了。
我是个好人
我十三岁当皇帝,却不得不先做十二年傀儡。刘太后垂帘听政,大权在握。我要做的事,就是她点头的事,我也点头。下班以后,她继续召见大臣们,而我还要跟着师傅读书习字。
刘太后号称是我的生母,她的话我必须信,也必须服从。她是个女政治家,把我爹宋真宗的“天书”闹剧体面地画了句号,把心怀鬼胎的大臣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朝廷的稳定。
一个寡居女人,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佩服。
让我不爽的是,直到她死后,我才听说,自己真正的亲娘是李顺容。我们见过面,却从来没有相认。每次想到她,我都想哭。我好想见到她,当面叫她一声娘,哪怕是在梦里。
这是宫闱秘闻,却搞得人尽皆知,被坊间编成了“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我不想辩解什么,也不想报复太后。因为,她冒充我亲娘,把我从娘手里抱走,是一笔交易。她让李顺容衣食无忧,李顺容帮她母以子贵,当上皇后。后人在《宋史》给我点了赞,说“为君者,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作为皇帝,“仁”是最难得的品质。我做到了。
太后让我母子分离,我却没有降低她的尊号,破坏她的声誉。大臣们在朝堂上很嚣张,动不动就大吵大嚷,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范仲淹甚至领着一帮谏官砸宫门。我宽容他们,毕竟,理不辩不明嘛。吵着吵着,善恶忠奸都能分辨出来了。
包拯是急性子,给我提意见,情绪激动,唾沫星子乱飞,甚至口水喷我一脸。我没有动怒,而是静静地擦了擦,继续洗耳恭听,保持笑容。
王拱辰为了劝我收回成命,揪着我的袖子不放。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不撒手。这号人我实在拗不过,只好照办。要知道,他是个状元。敢情状元也这么粗鲁啊!
每次上朝,都闹哄哄的,我还都能泰然处之,很少发脾气。回到宫里,虽说这儿才是我的家,但我依然先人后己。
吃饭被石头子硌了牙,我不发火,也不让身边人声张,为的是不让做饭的人受到惩罚。
在园子里散步,走得口干舌燥,也要忍着口渴,回宫以后再抱着茶壶狂饮,为的是不让奉茶的宫女宦官受到责骂。
出席宴会,听说一只蛤蜊要一千个铜钱,顿时觉得太贵,没胃口不吃了。
晚上肚子饿了,想吃烧羊肉,想得流哈喇子,但我忍了,没说。我不想让御厨为了一顿夜宵,宰杀那么多活泼可爱的羊羔。
京城闹瘟疫,我按照御医给的方子,亲自给老百姓煎汤药。
不管哪里有水旱灾害,我要么在宫里偷偷祈祷,要么大冬天光着脚丫子在殿外祈祷,也要祈求上苍宽恕百姓,有什么事冲我来。
大臣们建议扩建我的园子,我没同意。先帝给我留下来的园子,足够大了,干吗还要花这个冤枉钱?
我坚信一点,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全国各地存疑的死刑案子,我都要过目,大笔一挥,每年少杀上千人。我专门交代吏部,如果有哪个官员,把不该定死罪的人定了死罪,制造了冤假错案,这样的官员终身不得提拔。
晚上,远处传来歌舞声,我问宫女:何处作乐?宫女答说:是宫外的酒楼。她很是感慨:民间这么快活,哪像宫里这么冷清。我没有失落,反而得意:正是宫里冷落,民间才能快活;如果宫里快活,民间就冷落了。
从本质上看,我应该算是个好人。
我是个官家
景祐二年(1035年),我刚亲政不久,宰相王曾、吕夷简都要求退休。
我搞不懂,这两个老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就把参知政事盛度找来,问个究竟。
盛度很滑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宋史·盛度传》)于是,我就去分别询问这两个老头。结果,王曾推荐蔡齐接替他,吕夷简推荐宋绶接替他。我终于搞明白了,原来他俩是在培植提线木偶,自己躲在幕后继续遥控。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让他们都想不到的决定: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就地免职。只有盛度,职位不变。
我是官家,我的小心思和大谋略,决不能让大臣们猜透。
童年的特殊经历,让我很受伤;尔虞我诈的宫斗、欺上瞒下的内讧,又让我警醒,甚至到了猜疑、敏感、揣度的地步。反映在用人问题上,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让亲信大臣也发蒙。
狄青是我一手栽培的名将,又是我一手猜忌而死的。范仲淹是我一手栽培的名臣,又被我贬出了京城,只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们的生与死,升与贬,全在我一念之间。
小心思琢磨太多,大事就考虑不周了。换句话说,“仁”可以御人,却不足以成事。我没有勇气了却前朝遗留的边患问题,也没有魄力改变日益严重的政策困境。
庆历年间,西夏的元昊要称帝,我派兵去打,连吃败仗,而且都是全军覆没的败仗。最后,只能花钱买了西夏名义上的臣服。
北方的契丹(辽国)一看这都可以,也叫嚣发兵南下。我派富弼出使,据理力争,谈下来的,也只是破财免灾。
我坚信,能用钱办成的事,就不要动刀兵。我也咬定,我的地盘我做主,不能割出去。
也许有人说我懦弱,但我是花小钱办大事,还顺便控制了契丹和西夏的经济命脉,连他们市场上流通的钱,都是我大宋的。试问,到底谁厉害?
在我的时代,大宋军队打仗不行,兵却很多;大宋官员办事繁琐,官却很多;买和平花的都是小钱,给官员和将士开工资,养活宫里宫外一大家子人的花销,却是天文数字。
冗兵、冗官、冗费,已经成了社会问题,就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蔓延。直到跟西夏打仗吃了大亏,我才真正下决心,搞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