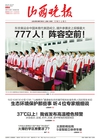走出苦难,走向救赎
——《罪与罚》读书笔记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提到,“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在这一点上,他是十足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忍受痛苦的能力大于西方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讲述了一个有关苦难和救赎的故事。
《罪与罚》中的苦难是多重的,首先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拉斯科尔尼科夫作为小说的核心主人公,遭受了不少物质上的苦难,出场时往往衣衫褴褛。他生活拮据,被迫辍学,当家教还多次碰壁,靠着母亲和妹妹获得一定的生活来源。他在书的开头就因交不上房租充满恐慌,不敢见女房东。贫穷带给他无尽的苦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书中的另一位主要女性角色索尼娅,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不得不出卖肉体,备受侮辱,挣的钱却少得可怜。书中的大多数角色境况都是如此,处于社会底层,贫穷、拮据,物质上的匮乏折磨着人的灵魂,带来无尽的苦难。
《罪与罚》中的苦难,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拉斯科尔尼科夫毕竟接受过教育,本质上是一个自尊自爱的人,他因为贫穷受人冷眼,在底层挣扎苟活,又因为母亲和妹妹的牺牲而感到羞愧无力。在杀人之后,他又掉入了无尽的自我矛盾和自我折磨之中,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断地呓语、做噩梦、脾气暴躁,刻意疏远昔日的伙伴和深爱的家人。他在书中逼问自己:“难道我杀掉的是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真的是一下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杀死了自己。”对于他内心活动的种种描写,都令人感到繁乱、充满痛苦与无助,甚至有点反复无常,像是一个意识混乱的疯子。索尼娅迫不得已走向出卖身体以获取钱财的道路,忍受着他人的冷眼与嘲笑。她早早失去了母亲,又因为一场事故失去了酒鬼父亲。这样的不幸对她的精神也是一种折磨。
透过《罪与罚》的文字,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俄国彼得堡底层社会的种种苦难。如果把这本书中的社会画成画作,那底色一定是令人窒息的灰暗,让人仿佛看不到希望。不得不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的描写水平。
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来希望通过成为“拿破仑式”的英雄人物摆脱苦难。他对酒馆里军官和大学生的对话表示赞同,杀死社会上那些毫无价值的“虱子”,就能拯救千百万受苦受难的灵魂,以一人的死换千百万人的生,通过犯罪、夺人性命表达对于不公平社会和苦难的抗争。他想要成为敢作敢为、能够主宰他人命运的人。但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自我救赎”的思想最终失败了,原本渴望摆脱苦难的他却因为这第一次尝试走向了更大的苦难。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呢?《罪与罚》给出的答案是爱与信仰。
同样在人间遭受苦难的索尼娅并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走向杀人放火的极端行为,依靠心中的信仰坚持了下来,并以此感染了渴望得到救赎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曾明确提到拉斯科尔尼科夫自首的原因:“因为杀人者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的良心不断地遭受各种情感的折磨,最后上帝的启示和人类的规则征服了他,促使他去自首……他决定承受痛苦以赎罪。”
若要真正理解这救赎之路的内核,就不得不谈及俄罗斯的主流宗教——东正教。
东正教与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新教、天主教存在一定区别。“西欧的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意识发生了很大改变,无论是新教教徒还是天主教教徒都不再专注于探究上帝和人的关系,而是更多地把信仰看做是对道德的追求。但是作为以正教自居的俄罗斯,对这些东西则是完全反感和抗斥的,并且俄罗斯东正教精神中的罪感与西欧天主教源于外在认知和道德约束的原罪意识有所区别。
俄罗斯人有很强烈的罪感,但他强调的却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源自人类始祖的‘原罪’,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启示,从内心深处视苦难为神圣,认为没有经历苦难历练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贫穷和苦难才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原初所具有的神性。”因此俄罗斯民族所信仰的宗教本身对于苦难有一种尊敬和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体现为一种普遍的同情心。例如,俄罗斯民间会用“不幸的人”来称呼罪犯,因为犯罪是与人的神性相悖的,实施犯罪的人是在对自己的神性和善良进行践踏,这样的行为将使他被上帝拒绝,是“不幸的”。这也就解释了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坦白自己杀人的事实之后,索尼娅扑进了他的怀里对他说:“不,现在你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啦!”这句话的宗教内核了。
在我看来,这种思想本身确实拥有一定的合理性。宗教引人向善,虔诚的信徒会为了获取灵魂的不朽与纯洁积极行善积德。面对人生苦难,也更有信念坚持下去,不知自暴自弃。这份信仰能够给予苦难中的人希望,让人“有盼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写苦难,他也关注苦难、深切地体会过苦难,这条救赎之路或许正是他在经历人生种种之后总结出的。或许忍受苦难并不如积极反抗的成效显著、进展迅猛,作为旁人,我们也无需因为这些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进行指责和批判。
承受过苦难,也就愈加明白生命的力量。
□王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