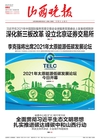崔庆轩:不拿枪的战士也是英雄
1932年3月14日,崔庆轩出生于河北省沧州交河县西关乡岳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父亲和兄长们在外奔劳,做饭和料理家务的担子早早地落在了尚属童年的崔庆轩肩头。一转眼,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可家里哪有余钱供他上学。小小年纪的崔庆轩便把家里种的瓜果梨桃等应时水果,以及小食品等挑到县城去,将卖得的钱积攒下来,充当学杂费。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攒,直到11岁那年,崔庆轩才得以在县城读上小学。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时光,天性聪颖的他加上勤奋努力,崔庆轩创造了连续跳级的纪录,用两年半的时间读了小学五年的课程。抗战胜利后,崔庆轩又在边区政府开办的学校学文化、学技能,从那个时候起,红色的种子便在少年崔庆轩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194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破裂。为响应党中央扩编军队以保卫解放区胜利果实的号召,当年10月,14岁的崔庆轩毅然报名参军,是当年沧州地区2000多名应征入伍新兵中最年轻的一个,并作为新兵代表作了表态发言。三个月后,根据部队工作需要,他调到了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二十团卫生队,从事伤员看护工作。两年后,由团部卫生队调入三营七连当卫生员,从事战场救治与伤员护理工作,正式开启了他30多年的医疗卫生生涯。
1949年4月,三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华北战场最顽固的堡垒——太原战役即将打响。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这一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6个多月,伤亡4.5万人。
崔庆轩所在七连的主要目标是攻打双塔寺周围的“顶天碉”。“顶天碉”其实是一组碉堡群,由梅花碉、卧虎碉、暗碉、“无奈何”碉等各式碉堡组成,号称“铜墙铁壁”的严密工事,散布在双塔寺的四周,因其地势较高,守方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故称“顶天碉”。
4月20日深夜,三颗绿色的信号弹划破夜幕,猛烈的攻城战打响了。随着我军引爆预先埋在敌方阵地前沿的炸药,上百门各种口径的炮筒几乎同时发出吼声,喷发出的炮弹如冰雹一般密集地倾泻在敌方的城墙和碉堡上,炮火将暗夜彻底撕开,映红了大半个天空,炮声、机关枪声和喊杀声疾风暴雨般地裹挟着太原城。
面对敌方纵横交错的密集火力网,我军指战员毫无畏惧,爆破组队员一批倒下去,又一批跟上来,与敌方展开殊死的争夺战。
崔庆轩接到火线救护的命令,要迅速将战斗一线伤员运送至后方,他背上急救包开始冲锋。眼前是冲天的火光,耳边是地动山摇的爆炸声和炒豆子一般的机关枪声,脚下是被炮弹炸焦的土地,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和飞扬的尘土。他时而奔跑,时而匍匐,在黑暗与炮火交织的战地上穿插前行,巧妙地突破敌军火力网的封锁,下到六七米深的壕沟底去抢救伤员。由于壕沟太深,又是黑夜,攀爬所用的木梯长度有限,爬上爬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沟底随处都有埋伏的地雷,头顶上还不时有从梅花碉堡里丢出的手雷,稍不小心就有中弹的危险。他顾不得这些,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及时抢救伤员,就是与时间赛跑,就是与死神争夺生命,就是抢救和保存我军的有生战斗力量。在搜寻伤员和施救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着两条原则,一条是绝不落下一个伤员,战场环境复杂,伤员并不一定只在开阔地,他仔细地在草丛里、壕沟中搜寻,不放过任何可能有伤员之处,只要发现有生命体征的伤员都要想方设法施救;另一条是绝不让伤员二次受伤,遇到附近有炮弹爆炸、石块飞溅时,他就用自己的身体压住伤员,让碎石弹片砸在自己身上,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伤员。
现场搜救过程中,他发现两侧壕沟的立面上有好多被炮弹炸出的类似窑洞的大洞,把它当作临时掩体相对安全。于是他机智地把伤员先挪到洞内进行紧急包扎处置,等到后面的爆破手第二次炸开封锁打开通道后,再将伤员背上壕沟进行转运护送。就这样在枪林弹雨中爬上爬下,来来回回也不知跑了多少趟,身上伤了多少地方,身上的军装与其叫衣服,不如叫裹了一身布条更合适。脸上身上流淌下来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是泥土还是烟尘。激烈的战斗打了整整一夜,次日清晨,第63军全歼守军,攻克双塔寺,七连全连参加攻打双塔寺的108人仅剩下了12人。这场战斗中,崔庆轩因其英勇机智的表现受到了团部的表彰,为他记了两个小功。两天后的4月24日,太原全城解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3月,崔庆轩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第187师560团赴朝参战。并在次月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即著名的“临津江战役”,痛击侵略者。
1951年4月22日,星期天。黄昏时分,在三八线附近的数百里地段上,志愿军万炮齐轰敌阵,打响了第五次战役。当天夜里,崔庆轩所在63军187师560团接到了渡江命令,由车辆、骡马及数以千计的士兵组成的渡江大军,涉入百尺宽、齐腰深的江水,冒着铺天盖地的炮火,似决堤的洪水般向前涌动,向对岸的守敌发起冲锋。
四月的朝鲜尚处在春寒料峭之时,临津江水冰冷刺骨,河床里到处都是光滑的鹅卵石,河岸堤坝陡峭处还结了冰,举步维艰。行进的困难还不算什么,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对岸敌人的炮击以及天空上敌机的俯冲扫射和轰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㞎㞎”,朝鲜战场与国内战场最大的区别就是来自天上的袭击。美国人自诩的“空中优势”确实对擅长打地面战的我军构成极大的威胁。因而,在渡江过程中我军伤亡严重。
崔庆轩及卫生队全体人员负责将渡江受伤人员护送和转移至后方,在北岸与南岸之间冰冷的河水里穿梭。他刚刚将一名伤员背到北岸,接着再跨进齐腰深的河水里向南岸接收新的伤员。湍急的水流冲击腰部和两条腿,走到河中间时,江水已经漫到他的腋下。他的右腿不知被什么重重地撞了一下,钻心地疼,为了及时护送伤员,他强忍着剧痛坚持走到了河对岸,从急救包中抽出一包绷带简单地给自己做了个小包扎,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到了宿营地后整个小腿已是血肉模糊,经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是小腿肌腱损伤。虽经过治疗得以痊愈,可仍然留下了后遗症,至今,他走路时仍有些跛。
4月22日23时,我军终于撕破“联合国军”在临津江沿线设立的防线,强行突破了天险临津江,向雪马里地区挺进。至4月25日,560团在雪马里地区全歼英军王牌精锐部队——英29旅皇家格劳斯特群团1营三个步兵连、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重坦克连,俘虏敌军500余人。
1953年3月,崔庆轩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被任命为187师560团后勤处助理军医,开始了他和平环境的军旅生活。他潜心钻研业务,在中西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多次获得师、军级的功勋和嘉奖,他参与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伤自救互救手册》,曾作为教材下发至全军各部队的基层连队。
董增红
(此栏目内容节选自三晋出版社新书《战火中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