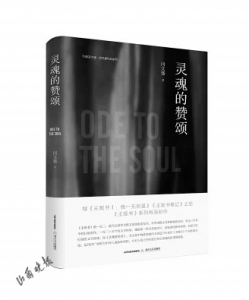闫文盛:《主观书》的写作是在与思考对话
去年年末,我省作家闫文盛获得第四届“茅盾新人奖”,成为全国10位获奖者中的一位。“茅盾新人奖,相当于一个针对青年作家的成就奖。能够获得这个奖,也意味着在一定层面上,我迄今二十多年的写作获得了基本的认可。”获奖时,闫文盛曾这样说。
“茅盾新人奖”的奖励对象为中国大陆近年来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成绩特别优异,并具备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潜质,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青年作家、评论家。
闫文盛,1978年生,山西介休人,现为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散文集《失踪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小说集《在危崖上》、长篇人物传记《罗贯中传》、人文专著《天脊上的祖先》等10余部。曾先后获得赵树理文学奖、《诗歌月刊》特等奖、安徽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山西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等。
在闫文盛二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迄今分量最重的作品是《主观书》,这部长篇散文他已经写了10卷120多万字,现在推出了前三卷《我一无所是》《主观书笔记》《灵魂的赞颂》。在申报“茅盾新人奖”时,闫文盛寄的便是这几部书。所以,闫文盛说,茅盾新人奖虽然是针对作家整体创作进行奖励,但对他来说,却又似乎是奖给《主观书》的。他特别感谢评委会的认可,因为《主观书》的写作漫漫无尽,他不会止顿于这已成的120万字,而是会将它一直写下去。
闫文盛是一位有着很高辨识度,或者说有着高度个人风格的作家,其奥义大概在于他以殊异的视角和身份在观望、感受和思考自身与世界。闫文盛的文字难以被某种确定性的文体所涵盖,或许由于其复杂的维度和丰富的阐释空间,又或许由于作者自觉地突破文体界限的意识,《主观书》系列被定义为“闫文盛作为散文家的重要发明,对中国散文有着独特的贡献”。
在《灵魂的赞颂》新书研讨会即将举办之际,山西晚报对闫文盛进行了独家专访。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闫文盛讲他的《主观书》以及这种“接近散文神髓的文字”的创作过程。
《主观书》与我的生命之途休戚与共
山西晚报:咱们还是先从获“茅盾新人奖”开始吧,说说当时的感受。
闫文盛:获奖,印证着一段时期的结束。因为我最近的十年主要在写散文——《主观书》,我希望以这种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世界,但是《主观书》不同于当下绝大多数的中国散文,所以之前我一直感觉,要想获得认同,时间或许是很漫长的。现在,有了这个奖的认定,或许可以使我对自己的写作保持一种基本的镇定和自信?尽管不能维系太久,因为新的思考、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但也至少让我感觉到了一丝安慰。总之,到此为止,与这部巨型作品相关的第一个十年也就差不多过去了。
山西晚报:所以说这个奖似乎也是给《主观书》的。
闫文盛:因为申报奖项时,需要提交的就是近几年的作品。我提供的便是迄今已经出版的《主观书》系列三书。《主观书》的写作漫漫无尽,并不会止顿于这已成的120万字。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写作旅程中,能得到一些鼓励,对我自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些慰藉和理解,会照亮我继续跋涉的道路。
山西晚报:《主观书》的内容完完全全是你个人的所思所想,既激情满怀又满腔愁绪,感觉你想和所有人诉说,又想要背向这个世界远行,是这样吗?
闫文盛:文学,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东方的文学,大体都有这么一些类似的特征,我觉得我的写作也在这个框架内——引用弘一大师之语,就是“悲欣交集”四字。因为我们承载的,不是具体的个体生命——你应该知道,若追根溯源,我们都有很悠远、怅惘的历史担负,它的一切都不是全新的,但我力求做到:说出我的感受和发现。我迄今的整个创作都有这种“生命写作”的特点,只不过《主观书》更为明显。《主观书》与我的生命之途休戚与共。也可以说,它的每个字,都有具体的来处,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来自生命体本身。
山西晚报:它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当你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就打算一直写下去了吗?
闫文盛:关于创作的最初,有两个方面我现在可以记得起来:一是对当时自己既有的创作感到了厌烦,有一种求变的希图,另一方面,也恰好是经过了之前《失踪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等散文系列的书写训练,开始感觉到自己已经具备了“写出一些刻骨铭心的文字”的可能。也就是说,我的练笔期在当时近于结束,《主观书》呼之欲出。这是一部向无数“辛勤而诚恳地活着(活过)”的经典作家及他们的创作人生致敬的书。但开始写的时候,我对它的未来无法判断,之后的规模和成效是时间给出的答案。
山西晚报: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主观书》的?这部书由片断的内心独白组成,现在已经有10卷120多万字了,打算写多少字?
闫文盛:开始写作《主观书》的准确时间是2012年10月28日。没有具体写多少字的计划,但下限应该是150万字,上限不能确定。其实字数本身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在编辑出版时会有筛选。最后的定本,必然从150-300万字中间选出来,或仅100万字?或有200万字?这至少也是十年后的事了,甚至二十年、三十年后。
我这样写,是觉得它更为宽阔、包容
山西晚报:一部作品埋头写这么多年,且不说付出多大心血,仅持久不懈的耐力就令人赞叹,为什么这样坚持?
闫文盛:因为开始动笔以后,我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念头,就是我总想写出一句话,而这句话一直没有写出来,后来就越写越长了。这种书写本身,对我来说,其实无从辩驳。它只是一个已经形成的非常具体的写作现实。
山西晚报:已出版的《主观书》三部——《我一无所是》《主观书笔记》《灵魂的赞颂》各有什么特点?
闫文盛:三本书,可以视作《主观书》跋涉长旅中的三个版本。第一部《我一无所是》编辑完成是在2018年年中,第二部《主观书笔记》是在2019年年中,第三部《灵魂的赞颂》则到了2021年年中,在不同的阶段,《主观书》的总体量应该分别是:60万字、80万字、120万字。第一部和第三部是以60万字和120万字为基数的精选版本。只有第二部完全回避了与第一部的重复,而且是更为自由、率性的笔记体。第一部和第二部各10万字,或觉有些单薄,所以到第三部时,体量扩大到了20多万字。我现在觉得第三部更有概括性和涵盖性,自然也是迄今三部中整体价值最高的一部。
山西晚报:《主观书》问世时,有人说这是一本“令人惊诧的书”,有人说“它应该被视作一种独立制造的文类”,还有人说它“是接近散文神髓的文字”……你怎样定义你创作的《主观书》?认可大家对你这套作品的定位吗?
闫文盛:如你所见,《主观书》书写我的日常呼吸(生命的律动,如潮汐般的涨落)。你选择的这几条评价,我自然认同。他们从另外的角度,完善了我对自己的写作注释。
山西晚报:你笔下的事物、人物、情绪,几乎都不可能构成惯常散文的元素,有着之于个人的思想、情感、生命和灵魂的艺术自发性,即便读完,也有点搞不清楚是散文吗?或者是文章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文学创造?
闫文盛:文无定法。而且西方作家中,这类思想随笔并不鲜见。我这样写,是觉得它更为宽阔、包容,可以将我想写的许多东西都放进来。
山西晚报:对这样的文体有过担心吗?
闫文盛: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过,但并不严重。因为我不是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主观书》有自察、自照,它与作者本身、与读者都还是有呼应的。但在两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感觉不到这种呼应:其一是我觉得读者的不解无须担心,因为有可能他们的阅读与我的写作并不契合,读者根本没读进去,所以在我这里就不认为是真正的问题,便直接选择无视;其二,也可能是我自己力所不逮。但这种写作不可能是静态的,我一直在写作中思考,在思考中探索,在具体的呈现中给予它各种调试和修饰。
它是在写万千信息中与心灵关涉的那部分
山西晚报:我在《主观书》里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厌世者、一个过于热爱尘世的人,仿佛是一个纠结的思想者的心灵呓语,为什么会有这繁杂的个人思绪?感觉茫无涯际、千头万绪。
闫文盛:此问,难以一言以蔽之。但简单来说,我们的生命本就这样,我只是在部分程度上,艺术化地复原了这个过程而已。
山西晚报:你在自序里说:我只是以一种尽可能平淡的方式来对应凡俗而亘古如新的日常(生活)。它以一种横断分切的形容步入向死向生的通途。你的写作,看起来一点也不平淡,因为抵达的是“向死向生”这样的命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境况?
闫文盛:紧张的思考本身就是有张力的,也有源头。如果从精神自传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就可能很清楚了。因为人类本身要面对这些,而我在书写中要求真,也就无法回避,所以感叹书写人生,自然“悲欣交集”。
山西晚报:《主观书》能带给读者惘然或自省,不知道这种读者感受对不对?您是想通过这本书让读者感受什么?或者说收获什么?
闫文盛:我力求真实地写出我自己,而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如果我不是那么失败,我相信读者在阅读这部书时,能常有心会。我们在纸上相逢,看到如群山般连绵的生活和历史,能懂得命运的语言,能追逐文明的烛火——但这些,也谈不上就是对读者的希望。因为一千个读者心中自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有希望,我只是时刻警醒自己:此书应该有立体的形容,而不仅仅是一根单薄的线条。
山西晚报:这样写有高度的私人化倾向,是想与这个世界进行对话?还是在与自己对话?
闫文盛:与思考对话。万物,你我,皆在其中。
山西晚报:看《主观书》,这几本下来,有种感觉:好好写着人,突然这个人消失了;好好写着事,突然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你的个人情绪都会把这些覆盖了。但如果是在好好写一种情绪,以为会有什么感悟,其实也没有,而你只是在那里追问。追问、质问都比较多。你是在寻求哲学意义上的答案吗?可不可以通俗化讲讲这些内容,让读者能对《主观书》有个好的打开方式。
闫文盛:通俗讲,《主观书》就是书写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所获得的万千信息中,哪些是与心灵关涉的,而哪些不是。我尽力在写“是”的那部分,因此,有很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也谈到了,它是一本“精神之书”。我认同这个说法。
山西晚报:《主观书》写了快十年了,自己在写作上、在生活、在心灵上都有什么收获?
闫文盛:它其实不断加强了、也在不断开拓着我对世界和自我人生的观察。通过这种写作,我觉得自己离这个世界更加近了,离自己也更加近。但我确实希望“入得进去”,又“出得出来”。因为无论何种写作或人生,其实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书写既是掰开这体验,分析这体验,同样也在不断地循环、建立这种体验,去除这种体验。通过写作这本书,我更加知道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许多迷惑和未知,我希望自己的书写,能使我先靠近它,再离开它。写作者既当持守如一,也该喜新厌旧。这是很辨证的话题。
有认同者,吾道不孤
山西晚报:除了《主观书》独特的散文文体,你的表达、你的语言也非常吸引人,《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形容你的文字“精到、老到、结实、准确”,你对自己的文字怎么看?
闫文盛:我的写作生涯从诗歌开始,迄今也一直在写,因此如果说,我的语言有一点可取之处,或许与此有关。但这么讲,也失之简单了。文学艺术以文字为承载,掌握好语言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我觉得我的文字尚在锤炼之中。
山西晚报:翻阅《主观书》,看着是“真散”,但实际上你对叙述、结构的把控能力极强,是吗?你对它是有控制的,对吧?
闫文盛:语言是通过控制而达意的。它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一盘散沙。“散”是表象,背后会有许多思索和用力的地方,只是看似不加显露罢了。
山西晚报:这样的文本被印成铅字上市了,你希望以这样的形式寻求知音和共鸣者吗?
闫文盛:没有太多的刻意,但读这本书的人中,有非常喜欢的,也有竭力批评的。这都很正常。
山西晚报:你也写小说但无论哪种体裁,都异于同类的常规写作,这和你最早写诗有关吗?
闫文盛:这与诗歌写作关系不大。我其实写过与同类创作区分度不高的作品,但觉得“自我不立”,因此,渐渐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你看到的,可能多半是我后来的作品。
山西晚报:散文,“形散神不散”是对它最通俗的解释,你怎样理解散文?
闫文盛:我前面讲过,我一直在寻找一句话,在寻求一种表述,所以无论过程如何,结论都是这样的:文字有其神。或许你说的对,散文“形散神不散”就是一种最通俗的解释罢了。
山西晚报:《主观书》结集出版,就有了一种气势,能让人想起本雅明、佩索阿、卡夫卡,这些作家对你是有影响的对吗?还有哪些人、哪些作品对你影响比较大?
闫文盛:是的。我喜欢你提到的这几位作家。还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诗人、思想家,中国古代的诗人、文章家的文字我都喜欢。这个名单不太好罗列,因为太多了。中国当代诗人中,我尤为喜欢昌耀的诗歌。
山西晚报:《灵魂的赞颂》封底上印着西川、何平、董立勃、耿立等名家对书的评价,获得许多知名作家的认可是种什么感觉?
闫文盛:吾道不孤吧。虽然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有认同者,会多少消减一点写作中的孤独感。
山西晚报:你接下来的创作还是以《主观书》为主吗?有什么目标吗?
闫文盛:《主观书》会继续写。还有一本关于中国古典小说家罗贯中的传记,是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正式签约项目,已经写了七八年了,工作接近尾声,会在一两年内出版。之后,我准备恢复自《主观书》写作后暂停了十年的小说创作。我希望写出一些自己真正想写的“不一样的小说”。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