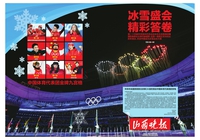今说古法——一个法官对古代法律的解读
贾充与《晋律》
对贾充的知悉,还是阅读《三国演义》时留下的印象。他率领群臣恭请司马炎受禅称帝,为建立西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晋书》对贾充亦有列传,记载其生平和主要事迹。他有个非常有名的女儿——贾南风,嫁给痴呆皇帝司马衷,成为皇后擅弄权术,导致八王之乱,甚至五胡乱华皆由此始。
贾充(公元217年-282年),字公闾,平阳郡襄陵县人(今山西省襄汾县),三国曹魏末期重臣,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贾充先后辅佐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参与镇压淮南二叛和弑杀魏帝曹髦,深得信任,又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地位显赫。同时,他擅长律令,受命主持制定《泰始律》,即《晋律》,历时六载方才完成颁行。法律颁布后,百姓赞扬新法便利,晋武帝下诏赞赏,赐贾充子弟中一人为关内侯。
晋律共分二十卷620多条,凡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求、告劾、捕律、系迅、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同时,杜预、张斐等人总结古代律学,对晋律立法理念、律文适用、疑义剖析以及量刑原则等作出详细的注解。这些注解与晋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也成为《唐律疏仪》的先声。因此,可以说,《晋律》总结以往法典,撷长去短,前承汉律,后启唐律,影响颇大,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区分律、令的性质。我国古代法律中,刑、法、律同义,商鞅改法为律,历代统治者定罪科刑均称为律,或者称典、令。一般而言,令与律相辅而行;总体上看,律重在惩罚,令则重于教诫。到了西晋,大臣杜预对律令加以区别,“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明确典章制度用令,违反令以刑治罪用律。西晋法律明确以律正罪名,以令存事制的标准,将具有稳定性的条文作为律,共二十篇;将临时性的条例入于令,为《晋令》四十卷。在律令以外,还有故事。故事,即成规,从汉朝的故事发展而来。西晋以各级官府的品式章程为故事,与唐朝的格和式相似。唐朝法律以“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在西晋已经萌生了。
二、礼、律并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者把儒家许多学说法典化了,引礼入法。司马氏本为儒学大族,自不待言,贾充也是“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其他制律大臣,如郑冲、荀凯、羊祜、杜预等多为儒学之士。因此,晋律带有明显的礼法并重色彩,充分运用德防于前、刑防于后的方法,如重于孝之诛、诈取父母卒弃市、禁以妾为妻、惩治居丧婚嫁请客等行为,弘风阐化,维护统治秩序。
三、首创以服制定罪。古代在丧服制度中,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为五等,对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根据血缘关系上的尊卑亲疏的丧服制度,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晋律首创这种以服制定罪、加重或减轻刑罚的制度,“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如犯父母名讳、居父母丧生子、冒哀求仕等违反礼教行为,被规定成犯罪。以服制定罪,实际上是对礼教的无限扩展,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制度,是一丘之貉。以后历代刑法典沿袭之。应该说,晋律开了个坏头,以亲疏尊卑关系定罪量刑,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四、宽简法典体例。纵观古代法典体例,大都呈S形,从简约到繁冗,又从繁冗回归简约,再从简约发展至繁冗,如此而已。从《法经》至《秦律》,篇章由简趋繁,至汉律极为繁冗苛杂,三国时魏明帝“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到唐律,又增繁加冗,循环往复。宽简法典体例中的“宽”指刑罚有所减轻,“简”指法律条文节省并削减。汉魏两代,法网严密,程序繁琐,不利操作,弊病很多。西晋刚建,需要缓和矛盾,凝聚人心,形势造就。《晋律》条文620条,加上令,共2926条,比汉律令减少2000多条。
五、发展刑法学理论。晋武帝颇重视制法,命贾充、郑冲、杜预、张斐、刘颂等十四人制定晋律,历经六载完成,培养了许多法学家。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我国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刑法理论。《晋律》进一步把《刑名》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张斐对犯罪、量刑等法例作出精确解释,以统帅各篇条文。他还阐明罪与刑的概念,区分犯罪行为与刑罚适用关系;在犯罪手段上注意区别暴力与非暴力界限;还注意区别犯罪责任能力,区别教唆犯(教令)与实行犯,区分行政犯(公罪)与刑事犯(私罪)等等。这些刑法学理论,与同时代的罗马法学相比,毫不逊色。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