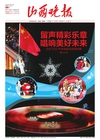那个人人称颂的好人走了
那一日,突然接到定海电话,说续枝走了,嘱余撰写碑文。听闻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一下愣住了,张着口竟不知如何应答。
续枝、定海和我是同龄人,我们生于上世纪50年代。应该说,比我们上代人生于战乱年月,已是“生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但因百废待兴,物质匮乏,贫病饥寒仍如影随形。尤其国家由乱而治,民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吃饭问题愈加突出。续枝家的情形与我家相仿,均系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务农,兄弟姐妹加老人,全家十余口,老的老小的小,缺乏壮劳力,难以挣到工分。而农业社粮食分配多以工分为主、人口为副,于是,我们这类农村的所谓“四属户”便成了主要的缺粮户。口粮不够怎么办?一是靠父亲微薄工资从黑市高价购粮补贴一部分,二是挖野菜刮树皮充饥。遇到水旱年景,“吃糠咽菜”“忆苦思甜”这类专用语所描述的景象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为了补贴家用,我们很小便捡柴、拾粪、担水、挑菜、刨茬子,一应家务活帮着大人干,甚至假期参加生产队劳动去挣工分,大人一个工记十分,我们小孩则记三两分。既然有此相仿的家境,我儿时所历续枝必定经历过,而且以我父工资高过她父工资而论,她所吃之苦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与续枝相识其实比较晚,是在静乐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与定海已相熟,因为我俩都在静乐中学读初中,而且来自一个公社,上下邻村,相距仅十余里。
1971年初,经选拔考试,我又一次踏进了初中时就读了两年半的静乐中学。重回故地,加上新生中近一半熟面孔,虽说是高中新入学,却已失去了新鲜感。好在还有另一半生面孔,仍然能带来一丝好奇与兴致。续枝便属于这另一半生面孔,来自县城之外的娄烦、杜家村两所县办初中和公社的七年制学校。当年,尽管已进入新社会、新时代,但乡下人重男轻女的思想还较为严重,女孩子小学读完,便开始学女工、做家务,早早为找婆家嫁人做准备,能读到高中的可谓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我们同届学生六个班三百六十余人,女生不足百人。女生中除去一多半去城里走读的,住校的女生也就仅有三四十名。
学校上下两排几十个学生宿舍(窑洞),女生只占下排四个,成为校园中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那时,我们正值十六七岁,情窦初开,对女孩子已经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晚上就寝后,男生们对每个班的女生评头品足便成为话题之一,有好事者还会给每个女生打分甚至起绰号,排遣烦恼寻开心。说实在话,以我当时之印象,续枝个头高挑,五官端正,算不上校花、班花级别的漂亮出众,但朴实、稳重,落落大方,依然可以说是风姿绰约。
那个年代,人们还很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从小被灌输,已经深埋于意识之中,尤其女孩子,稳重大方,不外露,忌轻佻,是为人品行的基本要求。因此,男生可以相互跨班级串宿舍,却很少敢去女生宿舍串门。男女生路上碰面,除极个别胆大的或者非常熟识的敢于说话聊天,多数则脸红心跳,羞涩地低头快速逃离。
我与续枝的认识过程当然也不例外。全年级六个班中,定海在七班,我在八班,续枝在九班,三个班的教室紧挨着,均在前排,每天课间活动见面的机会自然比后排三个班同学要多。除此之外,我们均来自当时静乐南部地区的几个公社。1971年在校期间静乐娄烦分县,将我们所在公社划入了娄烦县,无形中有一种地域亲近感。同时,来自农村的学生与城里学生相比,因“吃毛粮”与“吃细粮”之分而区分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平等的地位使得农村学生相互交往无等级意识障碍,且又都住校,接触机会相对较多。于是,一回生二回熟,见面点头、微笑打个招呼,便算是认识了。但说实在的,两年隔班同学,在校期间并未有更深交往。
中学的日子是异常艰苦的,苦到现如今孩子难以想象的程度。冬天零下二十摄氏度,每个宿舍火炉每周定量五十斤煤,两天便烧完,剩余五天只能硬生生挨冻,半夜冻得瑟瑟发抖,只能尽力挤到一起抱团取暖。来自县城南部的学生家距县城都在八九十甚至百余里以上,寒暑假回家、返校全靠步行。有一年寒假放假我们双井、罗家曲两个公社的几十号学生,由于行李已提前集中存放,无处睡觉,有人提议与其坐等天亮莫如趁夜赶路,于是午夜十二点便相跟着浩浩荡荡起身出发,一路高歌、吼叫、打闹说笑。
走出五十余里在东六度村口供销社台阶上歇脚时,无意间发现自己的两只耳朵已经失去知觉,用手前后掰了掰,居然如冷冻肉一般失去弹性,掰前掰后都无法自然恢复原位,回家后便是流水、化脓,长时间无法痊愈。寒冷虽说难耐,但毕竟一年中仅三四个月。而最难熬的当数饥饿,它如影随形,一年四季与我们形影不离,几乎无一日不在。
当时国家给学生规定的每月三十五斤粮食的定量,比国家干部还要多出五斤,但是架不住我们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的年纪,一个个食量奇大,加之伙食费太低,缺乏副食,同时集体食堂司务长、厨师一干人等难免多吃多占贪污克扣,吃到我们口中的仅能达三四分饱,也就是说,每日有一多半时间在饥肠辘辘中苦挨。尤其是晩上,六点开饭,每人仅有二两粮的玉米或高粱糁糁小米稀粥,不等晚自习结束,早已腹中空空。下自习回到宿舍,心急火燎,若百爪挠心。躺到床上,肚子翻江倒海抗议,只好到水房打一大搪瓷碗温开水灌下,直到肚子稍一晃动便咕咚作响,暂时有了饱腹感,才能免强入睡。
中学的日子也是无比快乐的,乐到忘记艰苦,只觉光阴荏苒、时光飞逝。高中阶段,已进入“文革”中后期,教学虽开始步入正轨,但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成绩仍无硬性要求,因此我们学习没有一点压力,刻苦与否,全凭个人自觉与兴趣。加上课外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墙报组、文艺宣传队、篮球队、乒乓球队……可谓快乐无比。
结束了两个寒暑的苦乐年华,我们带着满满的同学情谊和人生中那段最值得怀念与珍惜的美好记忆,离开学校,各奔前程。
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吃“毛粮”的农村孩子来说,所谓前程,其实不敢有多大的指望,更遑论什么远大理想,能够跳出农门,“毛粮”变“细粮”,结束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像城里人一样端上公家饭碗,已经是烧高香了。憧憬未来,那只是学生时期懵懂幼稚的幻觉,一旦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便是另外一个艰难天地。
我们天各一方,疲于奔命,苦苦奋斗,寻找各自的最佳归宿。毕业仅两月,续枝最先觅得新职,一个偏远山村小学代课教师的岗位,教学生活设施简陋,条件十分艰苦。因为系临时工性质,月薪仅二十余元,在当时基层公职岗位中属最低。即使如此,仍会招来不少艳羡的目光,因为同时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还在四处漂泊,无所寄托。从此开始,续枝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教育战线摸爬滚打,直到光荣退休。
继续枝履职半年之后,我也加入代教队伍,但仅三月有余,便入伍参军,远离故土。两年后,定海入学太原铁路机械学校,“公家饭碗”也十拿九稳,近在咫尺。
再见到续枝的时候已是高中毕业七年之后。1979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其时续枝正在我们村七年制学校任教,因此得以见面有过短暂交流。记得碰面是在我家院外街边,村里男女老少经常集中聊天拉家常的地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学校放学后续枝正坐在街边石头上与村民们闲聊,我从家里出来恰巧碰到,便也加入群聊。看得出,续枝与村里人尤其学校附近的我家这一片居民非常熟悉,熟悉到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外来教师,反倒像本村一员。这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她父亲时任我们公社副书记,经常到村里下乡,与村民很熟;二是我们村有两个她的高中同学,其中一个还是同班同学。但更主要还是她的人格魅力,随和、开朗,善解人意和乐于助人,使得调来不长时间便让村民把她当自己人看待。一次议论起学校的老师,说到续枝,母亲谓之“是一好闺女”。母亲一生不善言谈,说话简洁、直接,这一评价,包含了人品、能力等诸多方面,对于母亲来说,已是对人的最高赞美,因此,足见续枝在我母亲及整个村人心目中形象有多高。
在我探亲期间,同样的场合,与续枝又见过几次,之后又是天各一方,许多年未见。也就在同一年,续枝和定海结为伉俪,开启了人生另外一场精彩大戏。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某一个体来说,一生中发生交集的关系人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相互之间能有交集产生某种关系,必是缘分使然。
成为同学,本已是一种缘分;结为夫妻,终生不离不弃,更是缘分之缘分。多年后我与定海交往多了,也未曾问过他是如何与续枝走到一起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俩的结合无疑系天作之合,堪称世间绝配。
又过了十余年,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定海有事找过我一次。那时,我到省直机关工作已有六七个年头,且小有进步,工作生活均已稳定;定海则撂下公家饭碗下海创业,开始了他辉煌人生的后半段。那次找我,是他承包了灵石县交警队一个建筑工程,大门外墙上需凿刻单位名称书法大字,于是找我书写。
我与定海更频繁的交往是在他创办花果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之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娄烦人,他对本土传统农业及其食品加工技艺的继承、保护和开发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著,经多年奋斗,开发出了与娄烦地域文化紧密结合的“楼烦王”“花果山”品牌系列传统小杂粮、调味品产品。在此过程中,曾多次给我“安排”任务。由于对他这种执著精神的钦佩,更主要是深深的同学情谊使然,尽管有时我事情繁多,却无理由不欣然领命。
在与定海交往的过程中,有时也会见到续枝,特别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对他两口子的情况有了更多更细的了解。
定海的创业路十分坎坷,当过包工头,开过矿山,办过食品加工企业,几十年磕磕绊绊,中途艰难相随,险象环生,终于修成正果,花果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为娄烦域内知名企业。有道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贤良的女人。这一点,续枝作为家庭主妇,不仅完全称职,而且堪称典范。她承担了全部家务,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抚养子女,照顾孙甥,每一样都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她全力支持夫君事业,身体力行,出谋划策,乐善好施,拓展人脉,桩桩件件皆头头是道,得体合理。令人钦敬的是,她并非如人们日常所指,完全牺牲自我去成就男人,而恰恰是在成就男人的同时,自己也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她入职教育行业,从一个临时工性质的偏远山村小学代课教师做起,做到转正,做到校长,做成劳动模范,年年带毕业班,升学率学区第一,直做得调走时村民挽留依依不舍,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风范。
毋庸置疑,续枝是一个好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或者从她所处角色诸如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姐姐等而论,都无可挑剔,十分优秀。她也是一个好人,一个好老师、好同事、好领导、好下级……但凡与她有过交集、打过交道的人,无不翘指,极力称道。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称颂的好人,如今却走了,在她不该走的年龄,悄无声息地走了。她走了,却将悲伤留给了活着的人。首先是夫君定海,老年丧妻,情何以堪;其次是子女、公婆、兄弟姐妹等至亲,手足永诀,痛彻心扉;即使我等朋辈乃至一般相识者,亦禁不住扼腕长叹,悲恸唏嘘。
古语有云:好人有好报。既如此,为何不予续枝百岁?又有言说: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真是岂有此理!二者孰是孰非,实难定论。
以我愚见,人生在世,所谓生老病死皆有定数,皆以每一个体完成其为人之任务情况而定。
上帝说,人来现世带着原罪,终生都在为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赎罪,因此从生到死都要不断忏悔。
佛说,人一旦降世便入苦海,苦海中挣扎,直到六根清静,顿悟了,便可回头上岸或者渡至彼岸,去往极乐世界。撇开此二说,以现代科学而论,凡自然界物种,要保持物种不灭,其物种个体唯一任务就是物种繁衍,人类亦然。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何无后为大?因为无后意味着家族灭绝,进而到种族灭绝,再进而到人类物种灭绝。人之一生,从小学习生存本领到成年婚配生育,从抚育子女到赡养老人,全部围绕物种繁衍展开。为完成此艰巨任务,人类须向自然索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为此必须不断奋斗,付出劳动,付出艰辛。
所谓好人,正是遵上帝之命,听佛之规劝,顺应自然规律,勇于吃苦,甘于奉献,从而获得精神之升华和心灵之愉悦。所谓坏人,则心中只有自我,无主、无佛、无自然,只想索取,不愿付出,欲壑难填,怨天尤人,辄生邪念,心绪难宁。如此看来,人生吃苦受累,乃自然安排,天经地义。人生之意义,正在于以己之力去惠及社会,惠及亲人。
一旦失去付出能力,则完成规定任务,该谢幕走人了。续枝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所有亲朋好友留恋和怀念的好人,好到病倒一年有余便匆匆离去,生怕成为亲人累赘。续枝也是一个有福之人。她奋斗过、付出过,也成功过,遍尝世上苦乐酸甜;她有一个好夫君,一双好儿女,上敬公婆,下佑孙甥,尽享人间天伦之乐。一言以蔽之,六十八载光阴比之寿者虽不算长,却扎实无虚,精彩纷呈。因此,既上天有召,应去而无憾。
说一千,道一万,斯人已逝,吾辈尚且苟活。
苟活者之所以苟活,是因罪未赎毕,苦未吃够,人生任务尚未结束。比如当下,我们还要追忆逝者,超度亡灵,承受失去骨肉手足或挚友至交之痛;还要接续好人续枝优良精神,使之万古流芳,以至永恒。
续枝西归既是天命难违,吾辈自然无力回天,无奈只得祈愿百年之后再与续枝相晤,若有来世,定海已誓言仍做夫妻。余则谓:还是同窗好友。
若此,则幸甚之至。
赵克谦(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