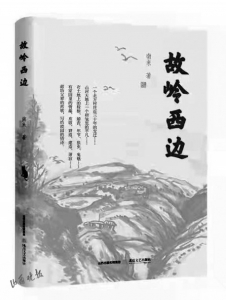我们该如何向她告别
——长篇乡土散文《故岭西边》读后
《故岭西边》南来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该书描绘了一个北方村庄近三十年的变迁图景。作者从童年说起,从自己家四合院的加密锁说起,带着读者游览了家园——有勤劳节俭的爷爷,把家里分到的不好的地块儿辛辛苦苦养护三年,在土地以丰收回馈主人时,爷爷却病逝了。写父亲,一个农民能摆弄无线电,做醋、卖醋、养猪等等。书中有梦想的破灭,有田园的荒芜,有对花果的爱怜,有对牲灵的情殇,表达了作者对家园和乡村的留恋和热爱。
在秋天,我们走出了家乡,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尽管远处是荒凉的沙漠。在陌生而凄凉的远方,我们带来没有烟火缱绻的自由,虽然我们的心是痛苦的,我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此后余生,故乡只出现在游子无穷的夜梦里。
作家南来在《故岭西边》里没有在夜梦里委弃,他在核桃熟了的白露时节回到了故乡。我想那时的窗外应该有一轮明月。带有故乡的文字从来都不少,我们能看到的大抵都是那片乡土中的“我”,而南来却清楚地记得属于西岭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人间的另一个世界于我们而言不再是遥远的想象,她的模样那样清晰,离我们又那样近。
像太岳一样伟岸的期许让我们忽视了少年也存在于情感和人性友爱的生活中,南来简洁的叙述里交织着土地生灵、家园至亲和廓大的梦,这一切怎能遗忘?西岭村的梁梁峁峁上,那么多生命和希望,在生生灭灭地繁衍。
地窖里冒出的白烟,泡桐上落下的甜花,村庙里点着煤油灯的复式小学,阴雨天哞哞叫的地牛,坟墓边突突的鬼火,磨坊里二哥画下《春归图》的黑板,泵房里母亲缠上毛布条的阀轮,槽头打着响鼻的马骡……穿越了浩瀚的时间,在南来的记忆里漫长地弥留,无法告别。
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运命窥伺在人左右。面对生命的哀艳与无常,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默默地凝望,默默地凝望。爷爷辛苦地养护着破碎瘠薄的土地,即将等来水重深且林修茂的时节,然而他离开了。父亲把果木园里的五六十棵果树一棵一棵地锯倒裁短,一棵一棵地刨出根来,赶着马骡一车一车地将枯枝树根拉拽回院子里,填坑平土,除茬耙叶,运粪洒肥,修坝筑堰,种播秋粮……秋粮丰硕,然而他患病了。
写作,是压在肩头的生命重量。然而所谓幸福,和我们形影不离。回想起爷爷手中抚弄的芍药,糖罐里盛满的含饴弄孙;父亲摆弄无线电时的凝神,核桃树上牵系的父爱深沉。如此等等,终究没有被光线消逝的凄哀蛊惑,这些永恒的印记,烙在南来生命中许多飞逝的瞬间。
那么乡土里的南来呢?廓大的少年之梦唱着浩大的盛夏挽歌,一口地地道道的晋语摧毁了成为播音员的梦想。然而人终究是要回到生活里的,苦痛的复读过后,终于等来了本以为是人生该有的旅途,那天他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二八自行车从北到南疯狂地试探自己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来结束属于南来的往事里最不堪又最果敢的青春。
繁华朝起,慨暮不存,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村子身底的煤窑被大矿兼并,他的家也随之破碎了。那些祖辈留下来的椽廊、铭柱、蜈蚣墙、月亮门,那些爷爷一手抚弄起来的玉黄树、芍药花、葡萄架,那些父母经历了烧砖、塌架、灌窑,用汗水和泪水修建起的砖瓦大院,在一个下午,全部被轰隆隆的挖掘机推进了深沟……
悬在空中的尘灰,是不是标志着一段故事结束了?不,它像尖塔一样屹立着,永远停留在南来心头一个美丽的位置,他要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城市,像伏在槽头吃着草料的马骡一样,一字一句地写下逝去的家乡故园和家乡故园里的一草一木。断断续续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尘灰包裹的往事写满了书页,进入了所有的年代。在漂泊不定的生涯里,他从来没有放弃向至近和疏远的人诉说关于西岭的种种情状。
在只有白天和黑夜的时间里,母亲生了两次大病,日渐蹒跚老去。她不愿意离开,不愿离开西岭故土,不愿离开太行山里温热的气息,不愿离开带有丈夫的记忆。然而,西岭却永永远远地在行政序列里消失了。无论山河如何变迁,南来相信当青绿的果实从树上落下,当坚硬的果壳在阳光下风干,那都是岁月留给后人永恒的福享,都是故岭对游子们深沉的召唤。
到了离别的时候,南来目光里最后的闪烁,停留着和西岭相互的怀想。那么同样无法告别的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回到自己的故乡?清楚地记得,沉痛地记得,永恒地记得。
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