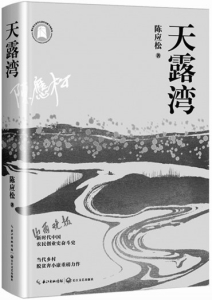陈应松:作家是为故乡而生的
当千百年来耕种五谷杂粮、稻麦黍稷的家乡田野,某一天蓦然窜出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藤本植物——十多万亩的葡萄,它们铺天盖地、气势磅礴,你会怎样想?
“长江以南是不适宜种植葡萄的,教科书这样说,几千年没有人尝试,我甚至到青年时代还不知葡萄为何物。我的生命被稻浪喂养,现在我被葡萄滋润。在谷粒的软糯和浆果的甜蜜之间,我经过了漫长的年月,无法料到,有一天,那曾经粗粝深重、沉默寡言的土地是一块流蜜之地。天降的甜蜜,是劳动和智慧的恩赐与传奇。”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应松是这样想的。
他不仅为此思考,还为此书写。
他自问:这个关于土地的神话,有追溯的必要和书写的意义吗?
他自答:我想试试。
于是,读者等来了陈应松的这本家乡书——《天露湾》。
《天露湾》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代背景,抒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创业史,全景再现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巨大变革历程。陈应松说:“我通过写这部作品,想告诉大家,农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最伟大的人。”
陈应松,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陈应松文集》40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3卷。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日、韩等文字,八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人民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钟山文学奖、中国好书榜奖等。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说:陈应松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创作和探索、他的思考与实践,对促进和推动整个文学界的思考,有着足够的力度。他的“神农架系列”,就是凭借对文学理解的定力,借助生活所赐予的情感财富,做出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新作出版之际,陈应松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分享了《天露湾》的创作故事。他说:“只有真正到田野中、到生活中去行走,才会真切地感知到农民身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品质。”
我就是想写一群农民写两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山西晚报:您创作这本书最初的灵感来自哪里?
陈应松: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家乡,也来自生活,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家乡和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因为我的故乡,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是被国家授予的江南葡萄第一县,有十多万亩葡萄,五六十个品种。公安过去没有种葡萄的历史,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几个农民尝试种葡萄,打破了长江以南不适合种葡萄的断言,改写了教科书,成为一个田野和土地的奇迹与神话,让我很有触动和感觉。
山西晚报:这样的变化的确能影响人、打动人。
陈应松:每当夏天,田野上果实累累,万紫千红,葡萄大棚一望无边,很令人着迷和感动。
我也开始思考农民对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说农民是落后的,但在我的家乡,葡萄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农业产业,恰恰说明现今的农民在这个时代不仅不落后,而且比我们想像得更加聪明和先进。时代就是这样,以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速度在进步着。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写了多长时间?
陈应松:我是2019年开始采访的,有两三个月,回去几次,在之前我也采访过,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慢慢有了写一个长篇的打算,真正动笔是2020年,在疫情期间我开始写这个小说,写了两年。葡萄只是一个背景,我就是想写一群农民,写两代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他们奋勇拼搏、脱贫致富、可歌可泣的命运。
山西晚报:在家乡采访数月,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陈应松:我们无法想像这些农民,他们怎么有这样聪明的大脑和开阔的视野?农村在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时代能给他们提供这样广阔的施展身手的天地,激发出他们的聪明才智?葡萄种植中包含了许多农业高科技,但我们的农民掌握了。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农耕时代的人,他们亲手结束了农耕时代,开启了农业现代的大门。我采访了这么多人,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故事,我都把他们放入到我的人物中去了。比方说有的葡农把葡萄当做一种田野艺术来经营,葡萄的枝条非常漂亮,像艺术品一样。他们高呼,农业就是大地的艺术,种地能种到这样的境界,可见江汉平原的农民们是多么令人敬佩。有的葡农,紧紧盯着国外最先进的葡萄种植技术。还有的农民把一个葡萄的产业做得非常之大,非常之丰富,这是要有气魄和想像力的。还有一个回乡种葡萄的年轻人,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返乡,他种的生态葡萄与众不同,有相当的土地情怀,这样的事情令人非常惊讶和感动。我希望大家能在这部小说中,看到这些每一个具有传奇性的农民的故事。
山西晚报:在阅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您通过作品传达出的这种惊喜与欢欣,您在创作过程中也同样怀有这样的心情吗?
陈应松:我的确也怀有这种心情,我希望把这种心情比较准确地、全面地、直接地传导给读者。“讴歌土地,赞美农民”,在这部小说中,我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总结我的心情。我热爱农民和土地。通过这个小说的写作,我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和通道,所以写作真的是充满快乐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确是我所有写作的一个另类
山西晚报:《天露湾》和您之前的作品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陈应松:这本书的确是我所有写作的一个另类、一个异数。我过去是以写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文坛立足的,小说比较沉重,或多或少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以神秘、神奇和魔幻为读者所熟悉。但《天露湾》这部小说,是我对家乡的农民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所写,没有那些神秘魔幻,是以纯粹的、不走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我过去写的多是高寒山区的贫困生活,现在我写的是富庶的平原水乡生活,小说的色彩和调子都与过去完全不同。以前我也从没有写过这种时间跨度三四十年的小说,这需要一定的掌控技巧。《天露湾》是一个真正正面书写农民形象和农村改革的小说,在写作上完全口语化、生活化、地域化,力戒知识分子腔和小说翻译腔,并着力刻画人物,这部小说中有几十个人物,我争取都让他们各有性格、栩栩如生。
山西晚报:这些人物都有原型?
陈应松: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群像,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我不喜欢虚构。当然通过书写,把所有的原型和他们的特质放进一个主人公或者两个主人公身上,这是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表现能力和塑造能力。
山西晚报:您觉得当代农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怎样的变化?
陈应松:他们的精神变化是巨大的,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中国的农民在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敢于探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有强烈的求知欲。现在农民种地要具备全方位的科学知识,特别是新的经济作物的栽培种植。这些作物品种本身就是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不去利用它们、学习它们、掌握它们,农民将无法生存,种不出一粒粮食。
我通过写这部作品,想告诉大家,农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最伟大的人。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主动还是被裹挟,他们都跑在时代的前面,而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所谓城里的作家,却成了落伍者,是真的被时代抛弃的人。另外,我想到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过去是洒下多少汗水,怎么勤劳苦做,而现在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怎么精心打扮它,怎么用科技之光照亮它。
山西晚报:您怎样看待现在的乡村?
陈应松:现在的土地,是现代的、先进的、时尚的、更加美丽的。新农村普遍开花,国家投入巨大,走到乡村许多地方,所谓的桃源仙境现在才是真正的出现了。农业是朝阳产业,大有可为,农村前途无限。而且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对绿水青山的向往,对乡村的喜爱,对大自然的喜欢,农村成了我们最美丽的乡愁,最幸福的去处,成了我们灵魂的归宿。
写作就是老老实实地向生活、向现实学习
山西晚报:您如何理解主题出版与文学创作二者的关系?
陈应松:主题出版与文学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作家来说还是不必要考虑为好,这是出版单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不能考虑主题出版这样一个概念。写作就是写作,写生活就是写生活,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
当然主题出版它可能会给某部作品加上一些标签和符号,这也是应该的,是出版的一种策略和手段,但对于作家来说,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创作规律去写作,不要被所谓的主题出版所局限、所束缚。写作不能先入为主、主题先行,不能思想大于形象,不能喊口号,不能扎堆、起哄,不能为了完成某种主题出版,去迎合、虚构、编造、夸大某种主题。作家永远是在生活中,在真实的感动中。如果你撞上了某种主题出版,只能证明你撞上了,而不是命题作文、应景之作。作家内心的写作动力是生命中的感动。
山西晚报:您的作品总是直面社会现实,去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白狐》也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您说过“作家要离现实近一些,离现实主义远一些”,应该怎么理解您这句话?
陈应松:我也忘了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我说的,我也认了这句话。离现实近一点,就是离生活和人民近一点,把自己融入生活和现实当中,做现实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写作方法、一种流派,我们真的不要管那么多,现实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可能不太适合我。说到底,写作就是老老实实地向生活、向现实学习,贴近现实写作,永远是对的。
山西晚报:很多作家也会坚持现实写作的方向,但也有很多作家笔下的现实是他们“想象的现实”,如何避免这一点?
陈应松:避免想象的现实,那就是要向生活学习,要真正地深入到生活和人民当中去。不要关在自己的书斋里,去想象现实和人民的生活。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同样是热气腾腾的。从泥土当中生长出来的才叫庄稼,而闭门造车,无土栽培,是没什么出息的。
山西晚报:在当代作家中,您的语言是非常有特点的。一方面会大量运用地域色彩强烈的民间语言,质朴、粗粝;另一方面,可能和您是诗人有关,也具有很强的诗性,空灵、优美。您是如何把这两种风格糅合到一起的?
陈应松:这两种语言都是纯粹的文学语言,所以它们是能够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你在写生活的时候,你要写你的生活语言,你该抒情的时候,你就抒情,也就是将口语和书面语结合,慢慢地融合,天衣无缝,水乳交融,是能够做到的。汉语的书面语言非常的典雅、雅致、精粹,但是汉语的方言,非常活泼灵动,充满泥土气息和生活气息。方言是地域的标志,也是文学最有表现力的语言,运用得当,就不会生硬和互相排斥。
山西晚报:您的创作有突出而鲜明的风格,这样会陷入一种固定的创作模式吗?
陈应松:我根据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作,每一个作品都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个创造,没有相同的。恰恰相反,我从来不会根据模式写作,我的作品永远在创新,就像评论界和读者说的,我的写作,总会给读者带来惊喜。我会继续努力。
故乡就是心越走越近而人越来越亲的地方
山西晚报:写了这部家乡书,您对故乡有哪些新的认知或感悟?
陈应松:所谓故乡,就是心越走越近而人越来越亲的地方。我对故乡新的认知及感悟,就是用文字重新发现故乡,重新发现土地,重新发现农民。再通过故乡的书写,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文学,重新发现作家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
山西晚报:您以后还会为故乡书写吗?
陈应松:我从来都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写了几十年乡村和自然,我的小说肯定是乡土小说。只不过我过去主要是写神农架,写高山和森林。现在我回过头来书写我出生的水乡和平原,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哺,重新唤起我过去的记忆,重新回到故乡,书写那一片我更加熟悉的土地,更加熟悉的乡亲。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和应该承担的写作责任。作家是为故乡而生的。毫无疑问,我在以后的写作中,肯定会继续出现水乡和平原的故事与风景,生活之树常绿,故乡永远年轻。更传奇的故事、更伟大的变革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它是作家们写作的源头活水,我们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我们的文字也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山西晚报:有具体的创作计划吗?
陈应松: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做创作计划的,突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今后我还会有关于家乡的作品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山西晚报:那有关神农架的作品还会继续吗?
陈应松:我主要是在神农架山里面居住和写作,因为空气特别地好,特别清新、安静。《天露湾》是我的第一家乡的题材,神农架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作品我会交替写作,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写作状态非常好,另外一部关于神农架的长篇小说,就是在我完成了《森林沉默》之后,也已经开始动笔了。
山西晚报:您的“神农架”现在已经和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等一样,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地域符号。在您看来,一个作家是不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精神故土”,才能构建起自己的文学国度?
陈应松:作家应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可耕地。往大处说,作家要建构自己的大地,以及大地上属于自己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禽兽、地质地貌、气象物候,建构自己的天空和云彩,土垄和耕作方式。这个地方是你来命名的。作家要当好自己的上帝,成为造物主和命名者。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说:“仅仅依靠语言与上帝抗衡,甚至要胜过上帝,这便是作家。”美国作家布考斯基说,写作是“所有上帝中的上帝”。过去我把它叫作家的根据地,如今我叫它文学的可耕地。
山西晚报:当代作家都有这块“可耕地”?
陈应松:当下作家是没有大地的人,不知大地为何物,还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或者更古老的土壤上,比如传统审美意义的自然山水中的想象与表达。更有甚者,他们的草木是从百度和《辞海》上移栽过来的,没有生命的草木,他们对自己作品是从哪儿长出来的茫然无知,他们的生命与生活是建立在现代电子垃圾上的废墟。
山西晚报:大地应该是什么样?
陈应松:只有在大地上才能建立自己的文学大地,否则,凭空想象的大地不是大地,在客厅和阳台上构思的大地不是大地,是沙堡。这就要求作家脚踏实地,疏散到自然的各个角落,认真地埋头营造自己的大地。这块土地越是打下自己的烙印,越能超越自己。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