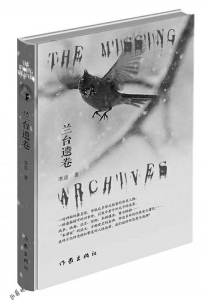由一封海外匿名信开启的“探秘之旅”,跨国寻访、酝酿八年,《兰台遗卷》节选——
匿名信风波
《兰台遗卷》李彦 著
作家出版社
作者被一封匿名信牵引着,像一位敏感机警的侦探,追根溯源,搜集海量琐碎资料,遍访国内外相关人士,开启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探秘与写作之旅,最终揭示了一段血雨腥风、惊天动地却又不为人知的历史,发现了一场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国际运动。她将目光投向神秘历史的同时也聚焦繁杂的当下,不乏对人性、理想与信仰的审视,对中西方文化意识差异、人类与自然共存共荣等现象与问题的思考,从独特视角阐释了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增强历史自信、理论自信等重要内容。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兰草凋零,枫叶泛黄。一封匿名信,从天而降。
晚餐后,洗净锅碗,泡壶绿茶,端入卧室,我开启了电脑。邮箱里蹦出来的,是校长文笛的信。
“晚上好,彦!紧急求援。今收悉多伦多红衣主教转来的一封密函。此事关乎李添嫒牧师的声誉,异常棘手,甚至可能导致学校陷于尴尬困境!请阅读一下附件中的英文信并尽快将那份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知你本已超负荷工作,为此我深感不安。谨表谢忱。”
文笛校长是位白人女性,履任仅短短数月,我甚少与之交谈。见她虽寥寥数语,口气却异常紧迫,我便匆匆打开了附件。
跃入眼帘的,竟是一封用英文撰写的匿名举报信。长长的大标题,颇为骇人:
李添嫒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圣徒还是撒旦?
李添嫒?我脑中浮现出一幅油画肖像来。
学校图书馆的大厅宽敞明亮。在东北角那扇直通天花板的落地窗下,专门辟出了小小一隅,命名为“李添嫒牧师阅读角”。豆绿色的细碎格子布面沙发,配上淡黄的实木茶几,清清爽爽,赏心悦目,实乃静坐读书的好地方。
两面墙壁上,高高低低地悬挂了十多幅国画,山水花鸟,风采各异,中华格调浓郁。唯有一幅油画,却是人物肖像,一位已到暮年的华裔女性。她双颊的肌肉略显松弛,唇角含了一丝浅笑,近视镜片后的目光沉静安详,凝视着沐浴在阳光下的阅读角。
盯着荧光屏上那唬人的标题,我的思绪回溯到了多年前。
那时,学校突然间收到了一批画作,说是多伦多某位老华侨捐赠的。谁呢?直到那年秋天的校庆日,我才有幸一睹捐赠者的庐山真容。
一辆轿车停到教学楼的门口,众人搀扶着一位身量瘦小、着黑色衣裤的老太太下了车。只见迎接的人都毕恭毕敬,亲切地唤她为“季琼夫人”。
老太太拄一柄手杖,哒哒哒敲着地面,步入了大厅,在众人簇拥下,她笑容满面,一一回应。我站在走廊里,也与她握了手。见我是华裔,她立即改用广东话和普通话,轮番寒暄。那种与其外表不相吻合的敏捷,在我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感谢季琼夫人的慷慨馈赠,校领导宣布,将为其过世的亡姊创建一个“李添嫒牧师阅读角”,以纪念这位全世界第一个被任命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女牧师的老人。
掌声中,在前排就座的季琼夫人伸出干枯的手掌,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方素白绸绢,摘下眼镜,轻轻擦拭着布满皱纹的眼角。
季琼夫人离去后,学校公关处求我帮忙,把她所捐赠的这批国画上的中文全部翻译成英文,以备存档。
那时,我虽然讲授中国文化课已十多年了,却堪称画盲,仅仅耳闻过齐白石、徐悲鸿等几个丹青大师的名字而已。不消说,当我的目光扫过那一幅幅镜框,看到阮性山的干枝蜡梅、汪亚尘的彩墨池鱼、叶醉白的骏马奔腾、高逸鸿的雄鸡欢唱、屠古虹的巫山云雨时,便只是觉得赏心悦目罢了,却不懂妙在哪里,更不知画家们为何方神圣。
看着看着,眼前却豁然一亮。手下闪出来一幅画,上面的落款是“张大千”。这个名字,可算是耳熟能详了。
定睛细瞧,画面上倒没有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墨荷,仅有一位孤零零的老者,鹤发童颜,皂靴僧袍,伫立山巅。心下便琢磨,这是原作真迹,还是复制品呢?若是真迹,季琼夫人是何身份背景?怎舍得把如此名贵的藏品捐献出来呢?
接着翻看,竟然还有一幅,也是标着“张大千”,且都题了款,落了章。
暂且不论真伪,我将疑问列入备注,向公关处汇报之后,这两幅二尺大小、色彩黯淡、毫不起眼的“张大千”便被挑拣出来,郑重其事地悬挂在校长会议室里了。
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事变更频繁,校长们已经走马灯似的换过四茬了,可我发现,每当同事们聚在校长会议室里开会时,除了自己之外,竟再无其他人朝墙上那两幅画多瞥上一眼。
不由得就想,简单地归结为“对牛弹琴”“有眼不识泰山”,似乎有欠公允。一旦失去了吹喇叭抬轿子、哄抬炒作的商业环境,那么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品,便只能返璞归真,依赖人们对“美”的真实感受了。无人稀罕,也不奇怪。
一晃,八年光阴便流逝了。
在看到这封标题耸人听闻的匿名信之前,我在图书馆内查找资料时,曾多次从那幅油画肖像前走过,却甚少驻足,仔细端详一下这位华裔女性。并非她衰老的容颜不再吸引目光,只因我是个大陆来的新移民,对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知之甚少,更是从未听说过“李添嫒”的大名。
她究竟做了什么?我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匆匆阅读了这封英文匿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