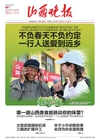夏季麦收
下午,从学校回来,我习惯骑上自行车,去县城东外环看看那些开阔的庄稼地。
曾经一望无垠的麦地,如今很多已被果树和药材代替了。偶尔有一些麦地,还是让我倍感亲切的。麦秆,已经由绿变黄;麦穗,已经饱满充盈;麦香,已经清晰可闻。一阵风袭来,那些麦子如波浪状,一起一伏。再过不到十天的工夫,就该开镰收麦了。
布谷鸟开始叫了:“布谷布谷,开镰割麦。”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多年前:
麦子成熟了,父亲早已磨好镰刀,准备好收麦的工具;母亲早早蒸了两锅馍。我们兄妹五个,正是饭量大的时候。
天还很黑,我们就被父亲叫醒,睡眼蒙眬中,洗上一把脸。吃毕母亲已做好的早餐,头上戴一顶草帽,便上路了。
麦地离家有三四里的路程,大哥和二哥替换着拉小平车,车上装着镰刀、绳索、馍布袋和一桶米汤,我呢,是家里老小,理所当然也很坦然地坐在车上,享受着坐车的悠闲。
我们来到地头时,天稍稍泛亮。
哥哥姐姐都已二十岁,当仁不让地成了割麦的领头人,一人割五行麦子。父母心甘情愿地把领麦行的地位让了出来,因为他们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呢,只能割两三行的麦子,就这,还老被他们落了长长的距离。大姐二姐不时地帮我割一段麦子,才使得我不至于太尴尬。
麦行里,时有蚂蚱蹦来蹦去。我便扔下镰刀去捉那小小蚂蚱。蚂蚱捉住了,捏在手里玩。玩够了,扔在地上,它就煽动着翅膀飞走了。
父亲和母亲主要负责捆绑麦子。打捆时,父亲从麦堆里抽出一把长麦秆,分成两半,先是把麦穗缠扭一起,然后用双腿夹紧麦子,让它们更加紧密,并把缠扭在一块的“腰子”从麦堆下面穿过,双手使劲一拉,膝盖抵住麦子迅速打结,而且打结很紧,这样,挑麦子装车的时候,麦子就不会散落一地。
中午两三点,太阳最毒辣,仿佛能把人烤焦,然而,大人们可不管这些。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虎口要抢食哪”。
走进浓密的麦行里割麦,那滋味真不好受。身上也仅仅穿了一件汗衫,还是热。倘若脱掉汗衫,那麦芒会扎得胳膊痒痒难受;不脱吧,又热得让人浑身淌汗。一趟割完,母亲便叫我从地头提米汤过来,让大伙喝口米汤解解困。这时候,最盼望的是,有一朵阴云飘过来,能将太阳遮住。然而,这样的时候,毕竟是不多的。
“卖冰棍啦,五分钱一根;卖雪糕啦,一毛钱一根。”卖冰棍的老头,仿佛算计好似的,总是在最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带着一桶冰棍来麦地卖。
各家的大人们纷纷围了过来,一家买几根冰棍,一会儿工夫,那个冰棍桶就底朝了天。母亲给我们买的是五分钱一根的冰棍,至于一毛钱一根的雪糕,我们想也白想。
吮冰棍时,我总是吮得很慢很慢,那仅有的一点甜味被我吮得只剩下冰冷冷的冰块。
冰棍吃完,身上凉快一点,再割起麦子就精神许多。
当天,割完的麦子,是要运回到自家的麦场去。主要是怕晚上下雨,淋了麦子。“六月天,娃娃脸。”这时候的雨,说来就来。
麦子收完,是要捡麦穗的。收割完麦子的地里,或多或少,都会散落一些麦穗。
我和哥哥姐姐,相跟着在自家的麦地里捡拾麦穗。二姐捡拾麦穗的速度最快,我们的筐里只有一少半时,她的筐子差不多已满。
……
“布谷布谷”,布谷鸟的叫声将我唤回了现实。我走进麦地,随手揪下一棵麦穗,在掌心里揉搓出饱满的麦粒,丢进嘴里,细细咀嚼,新麦的香味顿时浸入心脾。
□薛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