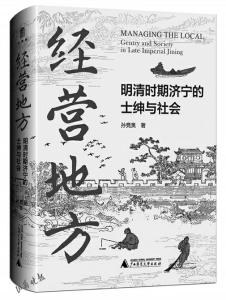展现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城市生活,《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节选——
江南水乡般的城市景色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孙竞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以山东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著作。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江南地区的情况,本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北方城市山东济宁,并注重将江南地区与济宁进行对比。济宁士绅在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中,展现了地方力量与国家权力的精彩博弈,也通过与“商”这个阶级的紧密联系,呈现出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城市化生活。
明清时期的济宁居民不仅致力于修缮和恢复历史遗迹和建筑物,还在城市和郊区修建起新的精致建筑。城墙内外流行的花园建筑与其他人造和自然景点,赋予了济宁的风景以独特的江南风格,有助于扩大和提升其文化声望。
迄至明初,济宁只是作为一个被称为任城的古城而知名。济宁的崛起通常被认为是大运河大规模复兴的结果。《(康熙)济宁州志》收录的一篇文章将济宁的重要性和繁荣归因于其地理位置和物质环境:
济宁壤接邹、阜,封域脉络,联续泰、峄、汶、泗诸山川,含英蕴华,隐郁停伏,至济乃发而南驶,与黄河会流,成汪洋巨津。下吕、梁,入清、淮,注之海。是以我国家肇造洪基垂二百年,济之英贤杰士后先接迹,视东省诸郡邑为独盛!
继而描述环绕济宁的河渠湖泊之水网,并留下了“济固多才之地也”的感慨。这段文字通过对区位优势、水资源、人才等因素的观察,描述了从明初开始当地人如何将济宁的生态条件与城市文化和社会重要性联系在一起:历史遗产、河湖水系、名士贤人等,构筑了城市的特有形象。《(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将济宁人的生活空间与花园联系在一起:“州素号繁华,人物风雅,园亭池馆之胜甲于诸州。”许多优美的花园、府邸和名胜沿着与大运河相连的水道建成。清中期的一首流行诗歌,用“小苏州”来描绘济宁的水滨景象:
《济宁州竹枝词》
(清)林之鹓
济州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城中阛阓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
在明清济宁的城市景致图案上,城墙也是富有特色的形象的一部分。像其他城市一样,济宁城墙的建造也是出于安全防御和政治权威等方面的功用考虑。明代的卫所分布在城外的近郊,卫所与其他守备军士部署在运河与驿路要津,构成济宁城市防御的缓冲地带。然而,城墙也构成了文化与旅游的资源。济宁的城墙上有四处门楼,其中南门塔楼尤为巍峨壮观,还有大大小小的建筑如角楼、亭阁矗立其上,既为防卫,又为美观之用。实际上,太白楼、浣笔泉、南池,以及其他的名胜如运河祠,都坐落在南城墙内外或城外运河岸边。以南门城楼为中心,聚集着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文化、旅游、宗教景观。
城市花园文化的出现,是济宁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新标志。随着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私人花园的建设在宋代变得流行起来,并在明代的许多城市和城镇中更加盛行。苏州、杭州、扬州等长江下游城市以其秀美的园林而闻名。这种习尚向北延伸至济宁,使其城市景观与江南城市相似,并具有类似的功能,吸引了外部游客的进入。所有现存的清代和民国初期济宁地方志都强调了城市园林的意义,其中《(康熙)济宁州志》与《(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包括带有说明性诗歌的图像,在城市环境中展示当地的“名胜”。郑与侨在其回忆晚明济宁园林的《名园记》序言中感叹道:“不出园,而济可知;不出济,而天下可知。”作为明朝遗民,郑与侨对亭园的追忆可能有所夸张,但其言显现了晚明济宁盛行而卓著的园林文化。
济宁的园林是由士大夫、地方士绅,以及富商在宅邸内建造的。地方志中许多园林所有权变更的记载表明,这些园林可以买卖。《(康熙)济宁州志》列出了三十三个著名的园林(分类为“园亭”),如拙园、避尘园、大隐园等,其中大部分是在明代修建的,但至清初大都只存其名了。从清初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著名的济宁园林都属于本地士人,如明代中后期的郑真、靳学颜(1514—1571)、靳学曾(1516—1564)、孙景耀、杨洵(1592年中进士)、徐标等,其中靳学颜拥有三处。通过将这些已不复存在的园林与名人联系起来,地方志编纂者提升了他们家乡昔日的声望。对著名文人雅士的强调,也意味着还有其他富裕的非士绅家庭所拥有的园林,并没有被放入官方记录。建造园林和相关游憩建筑的风尚自然也会诱使富人在城市投入巨资。
大多数园林宅邸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被毁坏殆尽。在新政权确立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后,一些旧的园林得以重建,也有新的园林出现。按李继璋的说法,虽然毁弃不断,但花园的建设并未中断,直到太平军及之后的捻军肆掠这一地区。时至1920年代,该地仍保留有几处著名的花园式府邸。一位老人回忆他在1940年代曾光顾十几处私家花园,彼时风采依旧,有些构筑年代可以追溯到清初。其中有一处远近闻名的花园式建筑群,保留至今。
与江南都市形象塑造的广泛趋势一致,济宁精英同样创造和展示了流行一时的城市园林文化。济宁花园建筑采用拱门、塔楼、凉亭、桥梁和假山等方式来突出景观,投射出江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