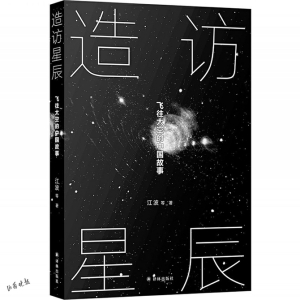讲述飞往太空的中国故事,科幻小说集《造访星辰》节选——
微小天体碰撞空间站
《造访星辰》江波等著 译林出版社
以中国空间站为起点,江波、宝树等国内一线作家小说集结,用11篇小说书写“飞往太空的中国故事”,开启星辰大海的征途。该书以浪漫而现实的想象,记录着中国人造访星辰的点点滴滴。从精密运行的航天仪器到异想天开的太空火锅,江波、宝树等一众作家,畅想着未来中国空间站的种种可能。他们写作的背后,既有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浪漫想象,也有中国当代航天人的不懈追求。中国人对于星辰的向往,古往今来,始终如一。
赴九天,问苍穹。从叩问星辰到造访星辰,每个中国人的一小步,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一大步。
我叫钟立心,是一名宇航员,二〇二八年七月十四号到八月二十一号,我在蓬莱空间站执行任务,期间驿站号国际空间站发生了失火事故,我奉命和老段——段国柱同志——一道执行了营救任务。现把具体过程汇报如下。文中的基本事实根据本人回忆记叙,文中的对话为避免回忆模糊带来的偏差,根据录音资料进行了对照修正。
八月十六号凌晨,我在值夜班。空间站里的值班制度和地面相同,按照二十四小时分昼夜。因为生物实验舱的实验需要人工确认数据点,所以老段和我会分别在凌晨两点和四点起来进行一次巡视,主要任务是在夸父号实验舱对生物生态实验柜进行一次记录。
我起来的时候,老段睡得也不踏实,还翻了个身。连续三天打破作息规律,每天睡四次,每次两小时,对我们两个都是极大的考验。除了对实验舱进行监控,我们本身也是K13生物钟试验项目的志愿者,虽然疲惫不堪,但为了科学事业,这点付出完全是值得的。
我从核心舱钻到节点舱,再转入夸父实验舱。夸父实验舱里有六个实验柜,包括我们的重点关照对象,生物生态实验舱。面板上的所有数据都在正常范围内:压力、光照、温度、电路监测……我按照标准要求逐一记录上传,然后拉开柜门,查看内部的幼苗生长情况。
幼芽在无重力的环境下偏向光源,所有的苗都齐刷刷地偏过一个角度生长,很整齐。这个生物培育项目我太太周茹云也参加了,所以她拜托我拍下生长过程给她看。虽然从地面站可以通过摄像头不间断地监测植物发育的情况,但茹云坚持要我用相机拍给她。拍摄不暴露任何空间站其他设备,只拍幼苗,所有传输的文件也会由数据中心监测,所以在空间站纪律允许的情况下,我每次检查都会拍一张。这一次拍完,我打算等地面上天亮了,就给她发过去。
生态实验柜在第四象限,我转身的时候,正好转过一百八十度,转向了第一象限。(蓬莱空间站中没有上下,为了区分方位,按照顺时针方向把四个方位称为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第一象限的储藏柜刚接收了大鹏号飞船上卸下的货物,我就顺带也检查了一下物资。资料上说总共二十八件共计六吨的物资,是为太空天梯项目做准备。我一直想参加天梯项目的实验,但是按照计划,这应该是下一批航天员的事。所以心里感到挺遗憾的,检查物资就格外仔细。
夸父号和不拘号这两个科学实验舱都设计了标准暴露载荷接口。这些接口可以从外部打开,利用机械臂直接把大鹏飞船上的物资转移到舱里。大鹏号飞船运送的货物就是从这些接口直接被送进了空间站。
夸父实验舱里的标准箱内标注的都是聚合纳米管丝线,一共有十六个标准箱,数字都对得上。检查完这些货物,正准备回去,就突然听到了警报。
声音很刺耳,整个舱室里都在回响。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上天这么久,从来没有听到过警报。
我很快反应过来,向节点舱滑去,在节点舱一打弯,就看见老段已经在核心舱里,浮在控制面板前。我一边飘过去,一边问:“发生了什么事?”
老段的表情很严肃,眉头紧锁,说:“对地传输信号中断了。”
我问:“有故障诊断吗?”
老段说:“我们还可以收到地面站的信号,但是向地面站传送的信号全面中断。不是卫星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射装置出了问题。”
空间站借助通信卫星对地传输,在任何一个时刻,至少有三颗通信卫星在空间站的可通话范围内。三颗卫星同时出事的可能太低,所以我判断,一定是空间站的反射接受装置出了问题。
我说:“我去检查。”说完后我打开工具柜,取出通信链路定位仪,然后向老段示意了一下,又回到节点舱。
我在节点舱把定位仪的插头插进断点箱里,输入指令。跳出来了错误信号,这个信号不断闪动,我心跳也加快了几分。诊断显示故障在舱外。
我立即向老段喊了一句:“老段,我要出舱操作。”
他很利索地回答我:“十分钟准备。”
我穿好宇航服钻进了出舱的气密门里等着。透过头盔,可以听见咝咝的泄气声,外舱门一点点打开,外边的星空一点点露出来。每一颗星星都亮得不像话,有点刺眼。我深吸一口气,钻出舱门,灵活地翻到了船舱外部,站直身子。
月宫号核心舱就在眼前,舱体就像一条白色巨轮,正行驶在无边无际的黑色大海之中。五星红旗贴在舱体右舷位置,在强光的照射下鲜艳夺目。前方,地球占据了大半个天空,像是一个带着辉光的水晶球。空间站正从太平洋上空掠过,地球一片碧蓝。虽然已经多次出舱执行任务,这一次出来还是让我感到整个世界的庞大和美好。我脚下的空间站,就是人类飞向遥远太空的一个中继站、一块奠基石。
我顺着舱体行走,虽然这是训练过上千次的项目,但每一次行走都马虎不得。保持身体重心,确保安全绳绑定,双手交替用力,任何时刻不得松开双手,除非是在已经将身体固定的情况下……我飞快回想一遍技术要领,然后跨出一步,然后是第二步……太空行走是一门技术活,更是对胆量的考验。周围是无尽的黑暗深渊,唯有脚下白色的舱体是唯一的依靠,航天员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早已经习惯了无视深渊的存在,但每一次出舱活动,还是像面对一场战斗,高度紧张,全力以赴。
一米多高的天线就在我身旁,看上去一切正常。我向前走了两步,绕着天线检查,立即发现了异样。就在天线的基底立柱上,原本刷着白漆的舱体表面被刮去一块,露出里边银色的金属,像是微小的撞击留下的痕迹。
这个痕迹并不是什么实质损伤,但有微小天体碰撞了空间站,这就是一个事故。我向老段报告,同时把头盔摄像头对准痕迹,让老段能看得清楚。
老段指示我继续寻找故障点。
我顺着舱体继续向前,发现了更多碰撞痕迹,深深浅浅,有四五处。这是一次密集的微小天体碰撞!这样的情况已经属于严重事故。我的心情越发沉重。又做了两次断点测试,却一直没有找到故障点。
做完第三次检测,还是没有发现故障点。
我撤下检测仪的时候,正好抬头,看见了月宫号核心舱巨大的太阳能帆。太阳能帆板上似乎有一块黑色圆痕。面积不大,局限在太阳翼的一角,如果不是恰好正对着我的视线,没有那么容易发现。我眨了眨眼,确定自己没有看走眼,然后通告老段:“太阳翼第三帆板似乎有些异常,电量供应系统没有问题吗?”
老段检查了之后告诉我,发电量降低了百分之十二,但没有触发系统警报,时间上也和通信丢失的时刻吻合。那么就是这里了。
我把检测仪扣在宇航服的挂钩上,空出双手,微微蹲下,然后用劲一跳,身子腾空而起,向着太阳翼扑了过去,准确地抓住了太阳翼上的扶手落下。
伸展的太阳翼有十多米长,电池板折叠排列,让它看上去就像一条天梯,通向无限幽远的太空。发黑的部位靠近根部,近距离看上去,有脸盆般大,在银白色的翼片上格外醒目,在这片黑色的中央,有一个小孔,只有指头粗细,毫不起眼,贯通了翼片。
这就是罪魁祸首了!我猜想是微小天体的碰撞损坏了太阳翼,电池燃烧,通信线路的供电受到影响,还让天线失去了功能。
我向老段报告了撞击痕迹,同时将检测仪接在了链路上。
诊断结果证明这的确是故障点。老段让我回舱,他要启动备份。
老段将左二太阳翼从系统中断开,并且让系统自检了三遍,万无一失之后启动了备用电路。
通信恢复了。
当屏幕上出现来自地面站的画面,我和老段情不自禁击掌相庆。
老段把空间站出现的异常情况向地面站的张鸣凤指挥汇报了一遍,然后等着指示。
张指挥眉头紧锁,似乎正在消化我们报告的情况,长久没有说话。
张指挥从来都是快人快语,憋着不说话可不像是他的风格。我有些疑惑,转头看着老段。“我们收到了驿站号国际空间站的援救请求!”张指挥终于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