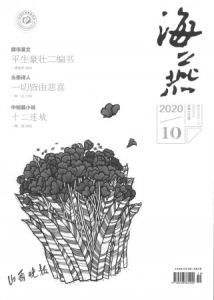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作品展示 梅钰短篇小说《十二连城》节选——
我要走出这山旮旯旯去北京
获奖评语
《十二连城》所呈现的是人与乡村的关系。三代女性都曾有机会走出乡村,但她们却都不约而同地被生活阻滞。女人们像土地一样孕育生命,可自己的生命却被困囿在土地之上。似乎脚下的黄土,总是以某种方式与人保持着不可磨灭的羁绊。十二连城,作为村庄的象征性标志,审视着乡村带给人们的命运,又如宿命一般被凝视、被铭记。
《十二连城》写生死,写无常。小说写到亡故人六位,明笔四人,暗文两人,或寿终正寝,或病亡,或遭横祸,尝透了生活艰难生命脆弱,死亡作为生命个体灰色的终极事件,已然是不可逃脱的厄运。每个人或奋力上跳演绎扬发和悲壮,或顺势而下敷衍沉沦和湮灭,是文学辗转的场地,也是哲学腾挪的地带,围绕她的言说和阐释就光影闪烁烟雾缭绕。而同时,死亡不时提醒生存虚妄,无常,徒劳,“原来活成个人,就是为个肚圆”,让人自证无效,陷入绝望,绝望过后,仍如牛湾村的老柳、老槐、老柏一样老态龙钟老而不死老而弥坚,活得不管不顾不屈不挠坚定昂扬。
《十二连城》的意义因之突显:顺意生长,不问意义,不惧消亡。
十二连城不是十二座城,是十二棵树,齐排排站成一座城。这是我娘家的标志,每次我看着它们离开,又盯住它们回来,日子在来来回回里一窜一窜,不知不觉就过了八年。我儿说我有白头发了,早起爬在脊背拔,拔一根往地上撂一根,很快密密麻麻一层。在此之前我跟他老子干仗,他抓着我头发,我揪着他蛋,都想把对方往死里整。他说你不能去,说下个天来,你也不能去。我说我就要去,天塌下来我也要去。跟过去一样,他说不过就动手,我也不是软柿子,由他随便捏。这事早有预兆。成亲时我左肩膀披一块红被面,右肩膀披一块绿被面,被人拉来拽去,他们说红男绿女,绿压住红,结婚后你才不会吃亏。迎亲的人不同意,非要红压绿,压来压去他们都烦了,手一松,我这边绿压着红,他那边红压着绿,各压各的,谁也不吃亏。唢呐嘟嘟哇哇把我引回去,往窑里一放,我和他窝里斗的光景就开始了。
我发誓,他要不松手,我也不松。他把被我拽得脱形的裤腰整理好,喘着粗气问,你为甚一定要去北京?咱农民祖祖辈辈就是种地,为甚你就不行?
种地有甚出息,从年头忙到年尾,挣的钱不够买种子化肥,连个香胰子都舍不得用。
到北京你能干甚,你会干甚?
甚也能干,甚也会干。
他作势要拿鞭子,我顺手捞起菜刀,我说跟你这么个窝囊废过光景,还不如死了呢,来,你来。他一怂,我推起洋车子就走。当初爹让我在缝纫机和自行车里选一样陪嫁,我还没想好,老大就给我做主了,说五里路也是路,给三女长条腿。老大说这洋车子太难买了,百货公司排起一长溜队,都想要,他城里的战友跟经理打好招呼,还等了三个月。车子捎回来后,我用蓝胶带把大梁架都包起来,给它织了个把套、座套,又拆了件烂棉袄,絮了个后座垫子。我除了回娘家骑它,平时就把它藏在后窑,要是让我那两个小叔子骑走,不烂成一堆废铁他们才不肯还我呢。
我儿在身后撵了几步,跌在地上哭。我心一软,过去把他提起,扔到洋车子后座。一跨上车子我就自由了。山桃山杏一簇粉一簇白在半山腰笑,成片的枣树展开了腰,路边的青草冒出头。山路十八弯,转了几个弯,就看到了十二连城。我蹬得更欢了,听见风在耳边呼呼哨哨,我儿大声数一二,三还没出口,我已经停在村口老槐树下。
姥姥给我招手,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你做甚呢?她说我能做甚,等死呢。她张开没牙的嘴,口腔和眼窝都黑洞洞的,有点吓人。打我记事姥姥就是这个样子,成年四季穿黑蓝粗布偏襟袄,宽腰裤,腿被布带裹得细细的,露一双小脚。她并不做饭,却总系着腰布,走路时眼睛瞄地下,看到有用的就兜回家。有一次我们趁家里没大人,把罐头瓶里的东西倒在炕上,扣子、玻璃弹珠、硬币、滚珠、钢笔尖,就这些破东西,有甚珍贵的呢。二姐一口咬定她把钱和好吃的藏起来了,说她见过北京的姨,人家的房子有两层,你在上面放个屁,下面都能闻到臭。姨和姨夫亲口说的,每个月都给姥姥寄钱寄东西,乡里的邮递员骑个绿车子,可不只是送信。我们又掀开被面褥单枕巾,细细揣,除了棉花瘪谷,甚也没揣见。宽三尺五,长五尺六,炕尾这床被褥就是她的地盘,她还能把钱藏到哪儿去。后来我们就都嫁了,姥姥颤巍巍给我们添喜,手上握的一块钱,跟她一样黑。
我问姥姥回呀不,她不说话,脸朝着十二连城那边。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腻了,说牛湾村有个人得了宝贝,扔颗花生进去,是一盆;扔颗玉米进去,也是一盆;扔个铜板进去,还是一盆。原来是个聚宝盆。这人要出门,怕被人抢占,就把盆埋在山上,在上面栽了一棵柏树,将树梢梢朝左扭了一把。谁料等他回来,漫山遍野全是柏树,树梢梢一律朝左。这些我长过十岁就不信了,要不为甚十二连城是十二连城,不是一百连城呢。我大声又问了一遍,姥姥还是没动,我就不问她了。
我儿问,老姥姥有八十了吗?有九十了吗?有一百了吧?我不理他,撅起屁股朝坡上推车子。斜坡上去有棵老柳,浑身都绿了,枝条垂下来,被一个灰小子拽着,另一个用小刀割,见着我,喊姑姑我们要拧柳哨。我把车子锁在大门洞,踮起脚尖扯了几根扔过去。他们呼一下跑远了,我儿跟在后头,不一会儿就变成个小点点,消失在灰土路。
院里乱纷纷的,到处是人,七眼窑中的一眼锁着,另外六眼的门帘挑起,露出六个黑洞洞,不知谁吼了一句三女回来了?我嗯了一声,没细回声。我娘正拉风箱,被我的黑影子遮了脸,说不年不节的,你回来做甚?我说我想通了,回来跟老大说一声,我要去北京,当保姆就当保姆,伺候人就伺候人。娘问乃成能行?我说他爱行不行。
炉灶上搭只头号大铁锅,直径一米五,正冒热气。我揭开锅盖,笼屉木制,形状半圆,空出锅边一尺,一防溢锅,二是简便,舀米汤舀烩菜不用来回提。米粒翻滚,蒸汽袅升,一笼屉山药红薯刚被蒸软皮。我说饿死了,有甚吃的?娘说有吃的能轮到你吗?家里大小二十几口,瓮里的黑豆都被偷出去换了豆腐饼子。我说谁让你生九个,你像姥姥一样只生两个不好吗?娘说生两个还有你吗?以前社会没办法,怀上就得生,又不能在尿盆里溺死。我说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怎么就不能溺死?还能掐死、闷死、打死,你就是没有武则天狠。你要有那么狠,当初上大学的就是你,去北京工作的就是你,看大彩电的就是你,你就是城里人、上班人、公家人,何至于把我们都生在这小沟沟里,受一辈子罪。娘说早知道你这么说,我先把你溺死。
天窗上漏进来三条光,浮在窑顶闪,我一前一后晃身子,拉得风箱呼呼响。六年前姨回家探亲,我就坐在这里看着她,蓝涤卡西装板板正正,腰是腰,胯是胯,裤缝尤其笔直,别人进门先上炕,她不,先舀水,问就用这个盆洗吗?怎么这么脏,洗衣粉来回洗涮,最后把手浸进去,还用香胰子搓手。怪不得她那么白呢,头发用发卡别在脑后,显得耳朵尤其白。我看呆了也听呆了,她说毛巾得一人一块,擦脸和擦手擦脚得分开,洗脸盆和洗脚盆也得分开,拉完屎不能用黄土块擦,女人来事儿不能用柴灰烂棉花套,不卫生。天神爷,卫生是个甚?二姐说你去一回姨家,就知道甚是卫生。卫生就是家里没有土,外面也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说没有土咋种地?不种地吃甚喝甚?二姐说人家吃商品粮。商品粮不是地里种出来的?第二天一早,姨就走了。娘说人家嫌不卫生,不习惯。那时我还是小,要是现在,我就把她拦下:你凭甚嫌弃我们?要不是我娘,你能上得了大学?你能嫁得了北京人?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一年到头土里刨挖,被苍蝇蚊子臭虫叮?娘说各人有各命,我没你姨心气硬。
娘就是绵善。她上学时还没解放呢,村里办新学,老师是外来的年轻人,头发三七开,腰板挺得板直,在黑板上写好现代诗,小棍子点着一首一首教。她念得好,也欢喜念。可等姨到了年纪,娘就去不成了。村里说各家派一个,你家也只能去一个。姨不吃不喝不睡觉,头磕在门板上咣当咣当,听见姥姥说让你去让你去,才停了。那年姨八岁,娘十一岁。娘从此纺线织布,长到十八嫁给爹。
我说你傻呀,她哭你不会哭?她闹你不会闹?她不上学活不成,你不会也寻死?娘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要那么闹,让你姥姥怎么办?性格决定命运,娘就活该受罪,活该早早嫁给爹,活该一气生九个,活该受死。我不能跟她学,我要向命运抗争,离开这土山土地土圪崂。当保姆咋的!只要去北京,讨吃要饭我都愿意。
锅一揭盖,灰小子们就闻到味儿,都从烟囱里爬出来一样,黑脸黑手朝灶锅冲,争着抢着去拿碗,谁也不让谁,扣碗的柳筐筐被他们拉得东倒西歪。抢完,大人也来了,集体食堂一样,自己拿碗自己舀饭,炕上脚底都是人,坐的蹲的站的。娘说人多饭香,不让谁吃也不行,让我去叫姥姥。我刚出窑,就见姥姥正往回走,身子在门洞里一扭一扭,小小的,弱弱的,一阵风能刮到天上一样。我说姥姥跟这群灰小子一样,鼻子长着呢。娘说她袄襟襟里藏有钟表,会看钟点呢。隔着门,我见姥姥从窗台上拿起笤帚。阳光很强,她在光下是个黑影子,不紧不慢地扫。扫完前头扫后头,扫完上头扫下头,还把小脚抬起来,仔仔细细扫鞋面。这小脚老太太,从北京回来十四年,还这么讲究。我兑了点温水,把脸盆端出去,让姥姥洗手。她花一样笑了,把手伸进去。
老实说,我对城里人没好感。比如姨,好看是好看,懒得很,寡得很,没人情得很。回来一次,也不问姥姥身体怎么样,吃甚喝甚,平时做甚,也不问娘拉扯这一大家子,辛不辛苦,劳不劳累,也不帮着做做饭洗洗锅,就会噼里啪啦挑毛病。茅厕有蛆虫啦,水里一股死气味儿啦,窑里有霉味儿啦。一想起北京那家人也一样,我就不舒坦。可再一想,人家为甚能挑出毛病,那是人家平时活得好,见识多。你随便拉出个牛湾人让他挑毛病,他都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生下来就这么过,哪知道文明和卫生是个甚。再说了,我到哪儿不是洗衣服做饭,又想过城里人生活,又想挣钱,不走出这山旮旯旯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