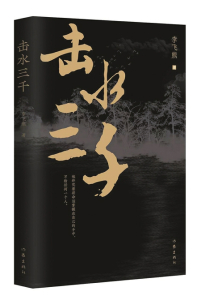提供了一个审视人生的新维度,《击水三千》节选——
庙隳
《击水三千》李飞熊著
作家出版社
从头再来不难,难的是从头再来的勇气。这是作家李飞熊新书、长篇小说《击水三千》想要跟读者探讨的话题。
张厚坤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成了到处躲债的老赖,他叫自己懦夫,因为他选择结束生命来逃避一切。王元吉是个亡命徒,为了摆脱贫困,为了争一口气让别人瞧得起,他什么都敢干。在被抓捕中,侥幸逃脱的王元吉救了跳河的张厚坤。王元吉救得了一时糊涂的张厚坤,却救不了早已迷失的自己。
《击水三千》把生活的真实与复杂,从各种粉饰太平中剥离出来,展示给读者最纯粹的状态。
午后,烈日炙烤大地,龙门桥纹丝不动,身边荒凉的土堡一派死寂。土堡中央关帝庙门楣上的金色匾额闪着刺眼的白光,映照在暗流涌动的水面,似乎要与白日的晖光一争高下。
皇渠到此一分为二,形成一个反写的“人”字,一撇是进水闸,一捺是退水闸。两座落下的闸门阻塞溢满干渠的水流像一艘肚皮滚圆的羊皮筏子,赭黄晶亮的渠水与关帝庙斑驳褪色的墙体形成鲜明的反差。
张大头昏昏欲睡,一斤高度白酒折磨着他的胃,令他头脑肿胀、肚腹绞痛。坐在凤凰城酒店包间宴席的主位,张大头索性不顾左右,倒头撞在餐桌上睡着了。
铺天盖地的黄沙遮蔽日头,白昼宛如黑夜,张大头拼命揉着双眼,想看清楚路在何方。他走啊走啊,灼热的黄沙令他的双脚发烫,浑身起泡,脑袋冒烟。
昏睡的张大头张开的嘴巴里流出口涎,餐桌旁有人要叫醒他,被人拦住。何必呢,让一个喝醉的人多睡一会儿是一种恩赐。
张大头全然不知宴席上这些朋友对他的冷嘲热讽,他们甚至向他张开的嘴巴里扔了一只苍蝇。可谁知道呢,那只苍蝇竟然是活的,在他的口中撞了几圈,当张大头感到发痒就要闭嘴的时候,苍蝇落荒而逃。
张大头转过脑袋继续做梦。黄沙太沉,席卷天地,沉重的腰身怎么摆动都是一团迷雾,越走雾越大,越走路越远,越走天越黑……他渴望一场暴雨,宛如他再次张开的嘴巴渴望一杯温热的白开水。
没人记得是几时几分,凤凰城龙门村炙热的天空不知从哪里翻滚过来的黑色云团,瞬间笼罩村庄和城市。暴虐的狂风夹杂着黑豆大小的雨点从天而降,仿佛有人斗胆触及龙王爷的胡须,毫无电闪雷鸣的前兆,硬生生的暴雨倾泻而下,好似龙门桥被水冲毁了闸门。
很少有人见过这么大的暴雨,天地一片,乌蒙蒙,黑乎乎,仿佛黑夜一般。日后,张大头的父亲告诉他,也就是早前没粮食吃的时候见过这么大的雨。
可能是雨声太大,餐桌边昏睡的张大头突然立起身子,没有任何征兆地醒了,把一桌人吓一跳。来吃饭的有两位朋友急着要走,张大头赶紧去结账。
他翻遍全身没找到一分钱,身无分文,银行卡里是零。堂堂凤凰城有头有脸的工程公司总经理张大头的荷包里没钱,连请客吃饭的钱都没有,怎么可能?谁会相信!
张大头窘得脸颊涨红,要不是喝了酒,红z着一张脸,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所有人都会看见。幸亏摸到两张信用卡,张大头舒了一口气,用其中一张结了账。
第二天,有人告诉张大头,关帝庙塌了。
当时,张大头刚从一处装修工地出来,这是他承接的最大的装修工程,需要垫资400万元来做。张大头咬牙接下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肥肉不好吃。
七月流火,却不见秋凉,工地外是烈日,工地内是蒸笼。走出蒸笼的张大头汗流浃背,衣服粘在身上,汗不停地从后脊梁骨往下流,打得内裤焦湿。他骂骂咧咧,埋怨工人们只顾进度不管质量。
就在这时打来一个电话。
“张总吗?”
“你好!”
“告诉你个好消息——”
“说。”
“关帝庙塌了,你亲手建造的。”对方挂断电话。
“喂——喂——你谁啊?关帝庙塌了!扯呢吧,喂——”看对方挂断电话,张大头越说越急。
这是一个陌生来电,张大头打过去,无人接听。
关帝庙塌了,怎么会呢?才修好不到五年,怎么可能塌!难道是个骗子?张大头正在想,电话又打进来,公司会计说有人来催债。
“催什么催,告诉他,老子做完这个工程,一次性连本带利全还给他。”
“他们都来三次了。”会计怯生生地说。
“不就三次吗,你应付,让他们走。”张大头挂断电话。
张大头又接了几个项目上的电话,肚子饿了,才知道已是中午一点半。他来到一家餐馆吃饭,想起昨天中午的梦。
昨天酒喝多了,为了感谢两位朋友在生意上的照顾,张大头必须喝多。这是在表忠心,客要请,酒也要多喝,多喝才显得有诚意。
他的梦是黄色狂沙,细腻又粗粝,远看像移动的城堡,近看像黏糊的河沙,如同龙门桥下皇渠里炼乳般黏稠的黄色渠水,又如他体内灼热酒精流过时的内耗。他安静的躯体里面藏着追击黄沙的豪气,可惜那一刻只有不能自持的口涎流了半个胸襟。正是这些口涎压得张大头喘不过气,宛如被弥漫的黄沙遮蔽双眼。突然一声巨响,晴天一个霹雳,张大头醒来,看着餐桌怔了几秒,露出他惯常狡黠的笑容。
难道是那声巨响?张大头叼着烟在想,难道关帝庙真塌了?他拨通父亲的电话。
“喂,大头啊。”
“爸,关帝——”
“关帝庙啊!”
“说是关帝庙塌了,有这回事?”
“我正准备给你说呢,好端端的庙怎么塌了。”
听到父亲的话,张大头愣住,举着电话,屏住呼吸。父亲还在说什么,张大头没有再听。挂断电话,他决定亲自回去一趟。庙是他修的,纵然坍塌,他也要亲眼看一看。
开车从高速公路拐入通往龙门村的乡道,一路上脸庞紧绷陷入沉思的张大头眉目缓缓舒展。阳光透过路边的杨树叶射在他脸上,无数颗亮晶晶的星星向他眨眼睛,刺目的太阳变得柔和起来。这条路走了许多年,每次回来都感到亲切。
张大头是个绰号,本名叫张厚坤。小时候,张厚坤在本村孩子里长得最高,也长得最瘦,精瘦的身子顶着一颗硕大的头。这颗大头爱出汗,经常冒着热气,像一把流动的开水壶在村里串来串去。这把开水壶实在太显眼,村里人记不住他的大名“张厚坤”,只记得他的头大,见了张厚坤都叫“张大头”。久而久之,父母也叫张厚坤“大头”。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厚坤的身子不断长大,而他的头似乎在童年长到位,长大的身子和童年的大头越来越协调,竟看不出他的头比身子大。
成年后,一米八三的个头怎么都看不出来张厚坤曾经有一颗大头,不过父母和村里人依然叫他“大头”。熟悉的人也叫他“张大头”,这像一个爱称,张厚坤觉得无所谓。
十年前,过完生平第二个本命年生日,张大头决定退役。抱着“大干一场”的雄心,揣着几千元的转业费,张大头脱掉心爱的军装,汇入凤凰城的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