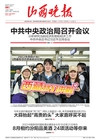难忘乡村的拨浪鼓声
我的老家在平定农村,家乡石门口村从村东头到村西头,连个小杂货铺都没有,文化生活匮乏,能让村民兴奋起来的,当数刘老头的拨浪鼓了。
种秋罢,农民就清闲了,每隔两天,总会有位老头在太阳当头时出现在村里,黝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身材不高,穿着朴素,一说话就笑,拨浪鼓在他手里不停地转悠,用粗犷的声音喊着:“拨浪鼓摇三摇,大嫂小姐都来瞧,买哩买,换哩换,买哩没有换哩贱!”刘老头的叫卖声,宛如现在的流行乐曲,听着舒服,一会儿就能招来一群妇女儿童,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日子久了,村民们都习惯叫他拨浪鼓。“拨浪鼓”卖的全是日常生活用品,有母亲缝衣服用的针线纽扣,有姑娘们用的红头绳、胭脂、发卡,还有木梳、篦子,就连小孩爱吃的江米糕、花米团、糖豆都有,俨然一个移动小超市。拨浪鼓的交易方法很灵活,有钱的用钱买,没钱的可以用废品换。我与村里的小伙伴就经常用破铁烂铜和穿破的旧鞋,换他的花米团和糖豆。那花米团的纯香、糖豆的甘甜,至今想起来还淌口水。
那时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大集体,农民收入很低,日子过得很拮据,连衣服和鞋都买不起,从来就没听说过化妆品。衣服都是用粗棉布缝的,衣服破了,补了缝,缝了补,一件衣服穿好几年;鞋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出嫁的姑娘穿的花布鞋和床上的被子,大多数是请心灵手巧的大娘大婶缝制的。这样一来,自然缝补浆洗之类的事就多,使用针线纽扣的量就大,拨浪鼓的生意也很红火。
“扑腾腾,扑腾腾!”每当拨浪鼓的声音在村里响起,村民们总是拿着准备好的废品,急急忙忙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娘大婶换针线,姑娘们换红头绳、胭脂、发卡,小伙伴换花米团、糖豆。你挑我捡,我喊你叫,那热闹劲儿差一点把整个村子淹没。要说最兴奋的还是那些姑娘们,换一段红头绳往头上一扎,换一盒胭脂往脸上一抹,好像公主,走起路来轻柔柔的,悠悠然、飘飘然,看人的眼神都变得傲慢神秘了。我经常把搜集的旧鞋底与小伙伴们的合在一起,换花米团和糖豆,这样不仅换得多,而且每样都能尝尝,每次将换来的花米团、江米糕、糖豆分完后,那种喜悦一天都难消下去。记得有一次,小伙伴都没搜集到废品,拨浪鼓一响,急得直打转,急中生智,把蔡大锤家的一口旧锅给砸碎了,换了很多糖豆、花米团,小伙伴们美得跟过新年一样,但又怕大人知道,整整跑出去一天没回家吃饭。
晚上,蔡大锤被他娘打得嗷嗷直叫,我也被母亲狠狠教训一番。拨浪鼓刘老头听说后,严肃警告我们:今后再换东西,大人不跟着不换给。害得我们为讨好母亲一起去换糖豆,干了很多家务活。有时一不听话,母亲就会以不一起去换糖豆吓唬我们。
那时的“拨浪鼓”就象一道美丽的风景,几天不见,大人小孩都想他。有一年秋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一连滴嗒七八天,就不见拨浪鼓来,村子里闷得喘不过气来。下雨天地里的庄稼活无法干,正是做针线活儿的好时光,家里的针线又用完啦,母亲急得团团转,硬逼着父亲穿着雨衣去请“拨浪鼓”。“拨浪鼓”刚到村里,就被村民们堵在牛屋里,买这换那,那场面热闹得很。“拨浪鼓”着实没少给村里行方便,他也因村民们的推崇,红遍村村庄庄。有的地方哄宝宝入睡,也唱拨浪鼓歌谣:拨浪鼓摇三摇,风儿轻轻来围绕,春天让我来祈祷,宝贝宝贝快长大,妈妈教你唱歌谣,小小黄鹂轻点叫,我的宝贝熟睡了……
现在农村里早已听不到“拨浪鼓”的叫卖声了,但梦回故乡时依然常梦见刘老头肩挑货担,手摇拨浪鼓,微笑着向我走来。
安秋梅(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