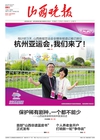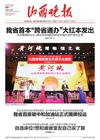百年之后遇知己
陶渊明的隐士差点白做了。隐士是士,不是农。士者,先要奋勇作诗,拼命作文,由农工转士首,由文青变大咖,由大咖成乡贤,隐士是士隐,非农隐,要先做了士,再去当田农、菜农与林农、渔农。若以为隐了就是隐士,那何以没一个农民称隐士呢?你是县市作协会员,六十花甲,归居林下,也没人叫阁下隐士。隐士者,先入世赢取大名,后出世赢取更大的名,要言之是,身藏乡下,名扬天下,才叫隐士。
陶渊明做隐士做得有些失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您说是陶公的安宁,我说是陶公的寂寥。
山村是有些偏远,不通马路,不通高速,这个不是隐士之居无车马喧的理由,诸葛亮住在深山更深处的卧龙山庄,刘备等人把进村的路都踩烂了;陶公居栗里陶村,风雅者与附庸风雅者,走错了都没走到这里来。来陶公家的,不是田舍翁,便是事儿婆,既没有浔阳文联领导,过年过节来走访慰问,采风活动没喊过他,更无建康纯文学大编向他约稿,更不必说登门索稿抢稿,李白还有蛮多汪伦接他去采风,乐乐农家乐,陶公顶多是村里的与附近村里的,给他送壶酒,借升米。
这不是陶公做隐士没做对,还是他做隐士没做出名,跟陶公玩的,往来无鸿儒,谈笑有白丁,与陶公所谓疑义相与析的,都是村夫子,陶公隐居后的农村生活,东晋有名人去过没?陶公最喜欢记日记,以诗记日记,日记真没一个大儒,陶公以诗记史,记个人交往史,要么田哥,要么田嫂,好像出现过一两次县令之类的,也是当年世交,祖上结缘的。这是陶公做人失败吧,不是,是他人做人失败。陶公做了蛮多诗,不出名,不是名家,更非显宦,没谁来跟你嗨,更不说给你打赏与救济了,陶公常常借米,借的也多是邻居的,非老板代言费,虽然他为三农代过很多言。
陶公做隐士,做的不是士,就是农民了。陶公诗是做了蛮多,东晋文坛诸公,没谁把桂冠诗人之名号冠盖与他。南朝钟嵘,文艺理论家,注意到了陶公之诗,评价不太高,只列中品。中品者,一般般也。文艺理论家第一责第一功,是发现文学家,将文学家摆位置。钟嵘貌似没把陶公摆到正位上。唐朝是诗歌年代,对诗人是惺惺惜惺惺的,陶公也不曾入法眼,没谁把陶公当“隐逸之宗”,李白是“我爱孟夫子”,有些朝宗隐逸的意思,而李白到死都不隐逸,一生激情满怀,摔了蛮多跤,闯得头破血流,也没见他有消极情绪。李白一生都在吃春药,吃诗歌春药。
陶公摆对位、摆上位,五百年后的苏轼是第一功臣。苏轼没做过任何人的粉丝,陶公却是苏轼的神龛级偶像。苏轼是最知陶公的,“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心目中,陶公之诗,不是中品,是上品,是上上品。曾国藩自说是蟒蛇转世,苏东坡自说是陶渊明投胎:“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苏轼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诚心当了陶公骨灰级粉丝,他做了120首和陶诗,几乎陶公每一首诗苏轼都做了一首和诗。一个人做一首两首和诗,不难,难的是一口气做了一百二十首。文坛大佬互相打趣,有电视访谈,则曰“您是我偶像”,一句而已,没谁说一百遍,打趣而已,当不得真。苏轼对陶公,实意拜服,真心学陶,如《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苏轼这诗,放在陶公诗集,鉴宝专家,我说的是没领红包的鉴宝专家,恐怕也鉴不定了。
苏轼自己拜陶公为诗坛宗主,他还大力教其生其友,一起来崇陶,敬陶,学陶,习陶。苏轼门下有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在诗歌界是大佬,还有苏轼老弟苏辙,也是文坛重量级,苏轼都让他们以陶公为宗师,写过和陶诗。有苏轼一人来举陶公之旗,已耀目天下,摇动天下,一个团队来一起举旗,自然是旌旗猎猎,迎风飘扬,顺时飘扬,飘扬千年。陶公之诗,这才站文坛高端,站在该站的位置上;入文学史页面,也打波浪线了,划重点看,打三角形符号了,袁行霈先生说:“苏轼和陶诗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带给诗坛一阵兴奋,从此和陶遂成为延续不断的一种风气。苏轼确有开创之功。”
这事有意思。当时人不识,他代有知心。陶渊明不在他的时代内,陶渊明在他的时代外。时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反过来说是,时内无知己,比邻若天涯。这是么子道理?时人无欣赏能力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同时代的文界、同等级的名家,不太会有苏轼崇拜陶公之事;没名气的,有脾气啊,蛮多文人的脾气,比名气来气大多了。
清之郑板桥,也是项高于顶的人物,没服过谁,同台有著名诗人,也是“时无英雄,使竖子出名”,郑老不服谁,却拜明朝徐渭为天王,“愿为青藤门下走狗”。这话说得非常粉丝,只有粉丝才说得出这种话。
徐渭卒于1593年,郑公生于1693年,整整一百年,一个大世纪。拜前贤,不失格,拜时贤,蛮掉价。要郑板桥当时人门下走狗,估计打死也不会。你要做的话,得给他端茶送水,三跪九拜;兴冲冲正在高谈阔论,忽地师傅来了,不能开口展才华了;有个么子奖了,是师傅先得,还是后来居上?自然,有师傅是好的,师傅给你拉人脉,给你荐文稿,那却是要敬师傅三杯酒,要在两节三寿送两瓶酒。这是涌泉之恩,滴水以报,提携之恩,提酒以报。这是对恩人,不是待圣贤。同时代者,熟悉的地方有恩人,熟悉的地方没伟人。
苏轼找陶公当宗师,不是这样的吧。苏轼先前也没以陶公为榜样,官场几次沉浮,搞得他没脾气,没志气了,苏轼理解陶公了。虽然,苏轼一生都没隐过,但他拿起锄头把,担起有机肥,开荒东坡,种起了白菜萝卜,“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李白受过多次挫折,没想去种豆南山下,李白是不会拜陶公的。苏轼一生转悠在入世与出世两重世界中,他身没转出来,他心转出来了。
文人包括落魄归隐的文人,没几个去学陶公的,回老家去山林也是举笔头,不举锄头。笔头锄头两头都举,唯有陶公与苏轼。苏轼敬陶公,是心敬。身敬是皮相,心敬是灵魂。陶公欣慰,比邻若天涯,时外存知己,无为在地下,老泪共沾巾。
□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