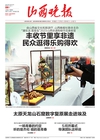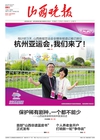架子车
前年,农村家里盖了新房。一是父亲于上世纪80年代盖的八间对檐土坯厦子已是风烛残年,遇有秋季持续月余的连阴雨时,我在外总是惴惴不安;二是母亲健在,得为她改善下住房条件了。父亲辛劳一生,终没住上楼房,已成我一大憾事。
如今拆房,特别是土坯房,都是搬出“贵重”的“古董”家具后,请挖掘机掀倒,然后捡出大点的木料当柴烧,再用推土机反复压碎砖瓦胡基作为地基即可,因为它们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变得如垃圾般毫无用处了。家里的老架子车就是我们拆房前移出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件之一。
前几天回家,看到缺胳膊少腿的它仍靠在新房外墙上,模样好像又缩小了一圈,犹如缺钙变矮的老人一般,令人唏嘘不已。
在朦胧的泪眼中,我好像又看到了早已故去的父亲弓着背、肩搭袢绳用它出圈平地拉麦时那奋力前行的身影,推土交粮拉粪时那急促的喘息,那已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袢绳似乎还留有父亲的热汗味……
据母亲说,我家架子车制作于1976年冬天,因为她在招待木匠的同时,还抽空送了远去新疆当兵的表哥,而表哥确是1976年的兵,这从侧面印证了架子车的准确出生时间。
我记得这车当时做得就有点小,可能是缺少木料吧,小限制了它的装载量,但也使得它轻便灵活,拉着比较称手,这也是父亲几十年来对它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车型小,穿的“鞋”自然也小,为此,父亲专门为它配了对轻便轱辘。从此车蓬和轱辘就成了黄金搭档,再也没有分开。晚年的车轱辘总是“气短”,父亲虽经常“动手术”为它补内胎,但每次使用前还要用气管子使劲给它打气加油,为此延误农活儿没少遭母亲训斥。
过去的农村,架子车拉人拉土拉粪、装蔬菜装水果装粮食无所不能。春天,父亲套着老黄牛用它给地里一趟趟送粪、送化肥,那纵横整齐排列的粪堆就是来年丰收的希冀和营养;夏天,父亲用架子车拉着高高的麦垛往返于场院和田地间,那时我在车上装,他则一边指导一边用木叉挑着往车上装,平路了我就坐在车顶压车防止翻车,上坡我在后面掀,下坡了我则沿在车尾巴上当配重保持平衡,这也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因为可“显悠悠”。
收麦的夜晚,等风扬场或看麦时,我就睡在放平的架子车上,看着不远处的父亲边观风向边高扬麦粒,那满天的繁星和空气里充斥的新鲜麦灰味儿,如今再看不到、闻不到了,偶尔失衡“挑担”的感觉也永无体验的机会了,我当时的纯真梦想和美好憧憬如今也不知实现了没有;秋天,挖红薯收玉米时,父亲把长长的梯子放到轱辘上,制成加长豪华版架子车,把十个左右盛满红苕或棒子的笼挂满梯子两边,运力大大增强,场面蔚为壮观;冬天,一年一度农田基本建设的号角吹响了,父亲们用耙子挖开冰封的土地,用架子车把高处的冻土拉到低处,如今村里南塬上、东洼里平展展的土地上依稀还有父辈热火朝天平地的背影……
后来,二姐夫学会木匠活儿后,曾给父亲做了个新架子车,尺寸是按当时的标准,轱辘也是加重的,父亲用了几次后,总埋怨太“笨”了,说手都抓不住车辕,拉着很不称手,就索性把新车连同轱辘卖给了同村人。后来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就又拉起了旧架子车,这个老车最后也陪着父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人不如物结实。如今父亲走了,他拉过的架子车还在,睹物思人,怎不叫我抚今追昔、泪眼婆娑……
□孙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