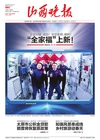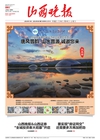细说从前——一个80后的这些年
万物皆可盘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儿子的手中竟多了一串珠子。贼光耀眼,分明是廉价的玻璃,他却片刻不离手。
我看着好笑,问他:“小小年纪,倒盘上串儿了?”他皱着眉盯紧了面前的作业,使劲咬着圆珠笔的尾巴。手里下意识地拨弄着珠串——咯吱咯吱。我偏要打扰他:“嘿,哪弄的这么个玩意儿?”他不满地回过头白了我一眼:“啥?”我努努嘴:“珠子,买的?”臭小子不耐烦地挥挥手:“少管闲事!”瞧这话,问不得吗?我试探道:“女朋友送的吧!”他登时羞恼起来,但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气急败坏:“胡说啥啊,这叫解压手串!解压!懂不?”
“还真不懂。孩子家家有啥压可解?我上学那时候……”见他越来越恼火,我赶紧住口退了出来。
沙发很硬,身体很软,周末就是这样闲适但无聊。我没得到明确的答案,只好心不在焉地打开了一本书。为了显得专注,又装模作样地掂了支笔。指尖不自觉地舞弄着,“啪嗒”,笔便旋转着掉在了地上。丢开书摸索着把它捡起来,过不多时,又一声“啪嗒”,这次却不知道滚去了哪里。刚刚吃力地挪开沙发,儿子便气鼓鼓地冲出了房间:“一会一声,成心啊?!”我举起才找到的笔,讪讪地说:“解压,解压嘛。”
沙发上滚过来一对铁球,叮当作响。“闲得慌盘健身球去,还预防老年痴呆呢!”你看这孩子,说的怎么这么不中听!我强笑着打岔:“都忘了这东西了。你喜欢?拿去拿去。”他没兴趣搭理我:“自己留着吧,盘什么不是盘啊?”
人总是这么矛盾。他在里头一声不吭,我就疑心是在作妖;见他真正专注地连续学了几个小时,我反倒心疼起来。“好啦,休息会儿出去转转,也要劳逸结合嘛。”儿子随手拿起个苹果,却不吃,只在两手间抛来抛去:“化学还没写完呢。”好容易有个喘气的机会,我赶紧拉住他闲扯:“听说现在都流行盘串儿?你在哪买的?”儿子紧盯着苹果:“怎么,你也要?”我说:“紧跟潮流嘛。我看所谓解压玩具都成系列了,什么啪啪币、萝卜刀,为啥你偏选了手串呢?”有了话题,这气氛就缓和了许多。儿子放下苹果挠挠头:“什么叫我选了手串,是大家最近都玩这个。其实都一样,你不是也转笔么,紧张的时候手里就总想摆弄点东西。”
“我还以为这里边有啥寄托呢。”我承认,还是担心他早那个恋。毕竟他这个年纪,毕竟我也是过来人。
“寄托啥啊!”他显然听出了话里的揶揄:“都快忙疯了,我顾得上么!”如此说来,倒让我松了一口气。于是拉开抽屉,拿出一串乌溜溜的珠子丢了过去。“喏,给你个老玩意儿。”臭小子一把抄住:“你啥时候买的?”“那说来可早了,你妈送给我的。”他噗嗤一笑:“定情信物?”我毫不掩饰:“反正好好攒着吧。”儿子的笑容越发古怪:“紫檀还是花梨?”妻子闻言走过来,端详了一番道:“从哪儿找出来的啊?便宜货,好像叫崖柏吧。”小家伙半郑重半玩笑地把珠子又塞回了我手里:“这我可不敢要,寓意深刻着呢。”妻子说:“拿着玩呗,又不是啥名贵材料。”儿子扯着嗓子道:“你没听我爸说么,寄托,关键是寄托!”
一家人笑闹了半晌,又分头做各自的事去了。我玩味着刚才随口说的“寄托”二字,忽地又想起一件东西来。
那是个巴掌大的葫芦,我姥爷当年经常把玩。每天早晨吃完油条,总要拿着葫芦摩挲一番;教我认字或下棋的时候,又爱用它在自己的秃脑门上起劲儿地蹭。经年累月便包了浆,油光锃亮而又温润如玉。老人去世后,家里的物什都分了,只是不见了这葫芦。我失神许久,拨通了表哥的电话。他听我问的竟是葫芦的去处,回忆了半晌,到底没想起来。
“我也记不清了,或许是给老爷子带走了吧。”见我还在沉吟,他继续道:“就是姥姥给他买的一个普通葫芦,那‘龙头’还是我小时候不留神弄折的。本以为要挨打,结果他也没生气。”我怕表哥会错意,赶忙解释说是因为儿子盘串儿的事,想起来便随口问问。他说正好有一挂金刚菩提,孩子喜欢就拿去。
辞谢了表哥,妻子悄声问我:“你刚说什么信物?珠子是女生送给的?”我说应该不是吧。她还不放心:“那怎么老拿在手里?”我摆摆手:“别乱猜了,就让他盘着呗。解压嘛,无非是个寄托。不是情感的,就是心理的。”
“你还说什么葫芦?哎,不想让他玩,你怎么倒玩起来了!”
我拨弄着木质的珠子笑了:“也是个寄托,不是心理的,是情感的。”
在水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