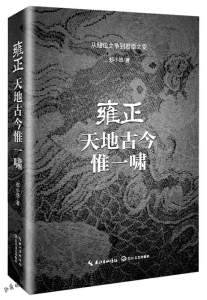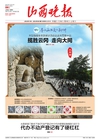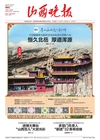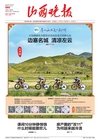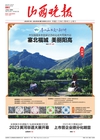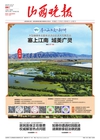郑小悠: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讲述皇朝秘辛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是改诏?是逼宫?还是继位?借由一代权臣之死,勘破变幻莫测的帝王心术。身兼历史学专业学者与网文写手双重身份的作家郑小悠携新作《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转身,拨开波澜诡谲的历史疑云,娓娓道来皇朝秘辛。
郑小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已出版《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等书。其文风老到,擅长从细微处着笔,采用古典式白描笔法,寥寥几笔尽得风流。
《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是作家郑小悠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该书近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耗时多年,精心打磨,是其畅销书《九王夺嫡》与《年羹尧之死》的虚构版,聚焦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的王朝政治与人物群像,以历史史实为蓝本,加以符合时代背景的虚构想象,还原了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以及年羹尧与雍正君臣关系的演变历程。在坚实学术训练基础之上进行通俗小说的演绎是其作品的一大亮点,郑小悠以小说家笔触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底。其情节的架构与细节的描绘,做到了每一处皆有来处。
马伯庸评价此书是“一部于细微处见功力的历史小说,考据精实、情节厚重,诸多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铺排错落有致,读来余味无穷”。近日,郑小悠接受媒体群访,讲述了在创作《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时的感想与体悟。
我眼中的雍正可远观而不可近距离接触
山西晚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来创作?
郑小悠: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专业是清史方向,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和制度史,就是研究清代法律方面的制度。但我从很早以前就对清代的政治史,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这个政治史比较感兴趣,所以写了一系列和这个相关的非虚构作品,比如《九王夺嫡》《年羹尧之死》。
山西晚报:书名为什么会用“天地古今惟一啸”?
郑小悠:“天地古今惟一啸”是我这本小说在写作初期的又名,在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建议我加一个主人公的名字,让它的主题显得更突出一点,所以就成了《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
“天地古今惟一啸”这个说法好多人觉得像个武侠小说,其实不是,它是雍正自己一首诗里的一句。雍正在做皇子的时候,蛮喜欢写诗的,而且写得还不错,有点像王维的田园诗。
他在做皇子的时候,他要突出自己做富贵闲人、与世无争的这样一种心态。“天地古今惟一啸”就来自于非常典型的他这种人设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标题叫《热河闲咏七首·其七》。我给念一下,“闲来忘暑兼忘我,浩气冲融贯太虚。城市山林君子宅,山林城市帝王居”,就是我是隐于市,就像在山林里一样的一个富贵闲人。“不寻仙客谈元旨”,就是我不找道教的道士去谈论这个道教,“懒觅高僧讲梵书”,我也不去找这个僧人,然后就是“天地古今惟一啸,悠然自得有谁如”。
这种悠闲的对天地古今、万事万物融入一心的状态,在“一下长啸”中“悠然自得”。我当时很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其中这个悠然自得,还有我的名字(笑)。而“天地古今惟一啸”又反映了雍正在做皇子时期的这种富贵闲人的人设,当然这是假的。这句诗也表现出他这种自我压抑、自我隐忍中的那种自高自负,以及隐隐地显现出他在即位后的这种追求,就是天地古今都在我的这一声长啸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反映他早年心态的。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的开头还是写了九王夺嫡的情节,通过对史料的阅读,您觉得九王夺嫡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郑小悠:其实我在《九王夺嫡》这本书里主要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们根据新发现的这种满文史料和一些日常逻辑判断,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些皇子之间的实例排序,包括康熙自己晚年的一些表现,包括他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判断是康熙直到他去世之前,直到最后,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确立一个继承人。他对立储这件事情,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康熙这个人呢,用我们现在说就是有拖延症,然后又碰到这种重大决策,他就不能下定决心。而且他对有一个太子和自己同时存在这件事情,也有心理障碍。他两废两立太子,就是觉得君主不能并立,因为并立就分权,而且大臣们就开始站队,就开始为了储君去背叛现任的皇帝,所以他对立太子这件事心理压力很大。
他其实是有三个比较接近于目标的候选人,就是从年龄、威望、和他的关系,以及能力各个方面有三个可能,就是三阿哥、四阿哥以及十四阿哥。我在《九王夺嫡》那本书里写了认为他是有三个候选人,他还在观察看看哪个更合适。如果他在西北的这一仗能够顺利的完成,那十四阿哥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如果在此之前,他的身体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年纪更大的两个人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在这个犹豫的过程当中,突发了一个事情,就是老年人着凉,肺部感染,突然去世了。这个去世是很突然的,所以我自己在那个书里的判断是,雍正其实是在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的过程当中,就是老皇帝没有说我要立谁,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人知道他要怎样。雍正利用非常短的,可能一两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在他昏迷的这个状态,召集了他身边唯一的重臣亲信就是隆科多,两个人形成一个默契。因为十四阿哥远在边疆,三阿哥他没有在皇帝身边,也没有他自己的人,所以雍正他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上位的。
山西晚报:您能不能用很简短精炼的一句话概括一下雍正。
郑小悠:一句话,就是可远观,不可近距离接触。
山西晚报:您给解释一下。
郑小悠: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的作为、这个人的特点,“可远观,不可近距离接触”。
康熙时代是一个稳定社会的时代,他在制度上的变化相对于明朝后期来说其实是不大的,因为他要先把这个政局稳住。但是到雍正时期呢,好多社会矛盾都出来了,就要去解决它。所以我从一个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政治的角度我还是很欣赏雍正这个人。作为君主,他的政治素质是很高的,他的政治眼光,他做决策的能力,做判断的能力,然后寻找帮手,用人的能力,这个是他最重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让我做他周围的人,那我拒绝,因为他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对人的判断,对人喜不喜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力怎么样。你的出身背景、你的名声、跟他有没有私交等等这些都不重要,他唯一看的就是你有没有能力。但另一方面,他喜欢有能力的人,但你这个能力必须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你一旦超出了,让他觉得你不太可控了,哪怕这种威胁不是真实的,只是他认为的,就像年羹尧、隆科多这样的人,那他是会下死手的,他是会重重打击的。
所以我总结雍正一句话,就是可远观而不可近距离接触。
儿时看《雍正王朝》就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
山西晚报: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
郑小悠:我上小学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是二月河先生帝王系列小说出版的时代,那时候没有什么辅导班之类的,放了学我也不太喜欢运动,就是在家看课外书,四大名著、金庸武侠、琼瑶小说什么都看,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也是那会儿看的,我很喜欢。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评书、戏曲,就是跟历史故事相关的这些都喜欢。
山西晚报:是什么让您对“清史”更青睐?
郑小悠: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拍一个电视剧,做一个小演员。但后来那个剧没拍成,导演就觉得很对不起我,说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当时是1999年,《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正热映,那时候我们家有VCD机,但那个正版的《雍正王朝》VCD影碟要卖上千块钱,父母肯定不会给我买,我就跟导演说,我的愿望就是想有一套《雍正王朝》的正版碟,然后他就送给我了。我拿到那套碟后特别珍惜、特别喜欢。另外,当时有一个我父亲的朋友不知道辗转怎么认识了二月河先生,他送了我一套《康熙皇帝》的那个书的签名本。那个时候,1999年的一个小朋友,能拿到《雍正王朝》的碟,然后还能拿到二月河先生签名的正版小说,觉得好激动,我就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了。
山西晚报:然后就开始尝试写作?
郑小悠:2003年我上高一,开始上网。因为我喜欢与历史相关的,就看了好多与历史相关的论坛或者一些帖子,还加入了一个论坛,也发过帖子。上大学后,时间比较充裕,我就不甘心光发帖子了,还会解读,后来还想充分释放自己的主观想法,就开始写小说。读硕士后,我开始在晋江文学网上连载《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网上连载这个东西就是信马由缰,思路是没有界限的,就是你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就写了60万字。
我觉得那时候写东西最大的一个收获,不是你写出了多少字、写出了什么、编出来什么故事、塑造什么人物,重要的是结识了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好、关系特别密切、有共同语言的朋友。我写网文积累了很多粉丝,大家在后面跟帖互动,然后从论坛互动演变成私人之间的交往,这些朋友会给我留言,给我提意见。
读博期间课业压力大,我没继续写。工作后,为了不丢掉原来的写作兴趣,我用零碎的时间把原来的知识,加上我后面积累的学术的这种背景开始在公众号上写作,把我原来积攒的知识系统化,就写了那个“九王夺嫡”的系列和“年羹尧之死”。这些文章发了之后,就被我的老师转发到朋友圈,又帮我联系了出版社,就陆陆续续把《年羹尧之死》和《九王夺嫡》陆续出版了。
山西晚报:大学期间写的《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反而没有最早出版。
郑小悠:我在《年羹尧之死》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了这个小说,但也只是提一下。没想到碰到了一个有心人,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阳继波先生,他是买了《年羹尧之死》看了那个序言后,就通过各方面的渠道联系到我本人。当时我好紧张,我说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最多也就是写一些历史的通俗读本,主要还是写论文出身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正式的文学作品,网文应该不能算。
“雍正”这个作品60多万字,它是那种比较杂的网文,没有逻辑、没有主线、没有主体,人物太多,而且前面后边都写乱了,有的人物写着写着就忘了。如果出版就需要大规模的修改,要用很长的时间,我就问阳先生能等吗?他说他愿意等,而且愿意给我机会,我就答应下来。然后我大概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拼命砍、拼命删、拼命压,压成一个逻辑完整、主线清晰、结构相对分明的新稿。我把好多人物都砍掉了,如果老粉记得的话,会有好多人物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将那个60万字的稿子改到30万字。改过后的作品从一个完整的历史小说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还是比原来有较大进步的,这跟我这几年读的书,特别是专业的学术训练给我的这种对逻辑、对结构的追求,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不是大家的鼓励我很难坚持下来
山西晚报:书出版后,粉丝怎样评价这部作品?
郑小悠:这本书一出来,有一个评语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写的书的行文风格,或者这个历史叙事比较像高阳,这个让我特别开心。因为虽然我对雍正的爱好是来源于二月河的作品,但其实从我最喜欢的现当代作家来说,历史小说作家我最喜欢高阳先生,就是许晏骈,他的作品中,特别是晚清,像《慈禧全传》《胡雪岩》等,我都特别喜欢。我喜欢他那种叙事的自如,以及对官场、对政治、对人物的拿捏的细节。语言对话很生活化,虽然生活化,但是又不俗,就是不装不端着,但又很雅逊,有一点点古味的白话小说。我也有一点点在刻意地向他学习,所以我看到那个评语就很开心。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些批评我的意见,比如说我对雍正写得太狠,有点苛刻;或者说我小说初稿那种感情色彩的基调完全变掉了。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成熟,我二十岁的时候喜欢那种狗血的表达,那种情感过于充裕的表达我现在显然已经不喜欢了,这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我的阅历、我的阅读,是我对社会、对人的理解的变化造成的,这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不可能30多岁写出来还是一个20多岁的人的心态和审美。
山西晚报:您是专业从事历史研究的,在写小说时是怎样将生硬的史料融入虚构作品中的?
郑小悠:这的确是个问题。在做研究之后,我就老想卖弄知识(笑),就老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但是很多内容又不适合做成文学情节,而它又是一个知识点,又想告诉大家,怎么办?我会使劲控制自己卖弄专业知识的欲望,全部改成对话,或者改成场景。
我自己很得意的一段的是第30章,就是写胤祥和雍正他们俩一块看宋版书的场景。怡亲王就是胤祥,他是一个藏书大家,他的藏书其实很有名的,所以我特别想写一段,就是那个他跟古籍、跟藏书有关的东西。但这个古籍版本要放在小说里,我觉得太烦了,这个肯定没有人看,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雍正和胤祥讨论来切入。我的入手点就是抄家来的善本书,这个就很符合雍正时代的这个特点,雍正把抄家的这些好东西赏给他最信任的这个弟弟,这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先写他们看了一个原版书——《梅花字字香》,这是一个国图藏的书,确实是刻得很漂亮,是一个原刻本。我在作品中写“皆以楠木书盒盛装略无缝隙,打开书便觉一股浓香飘来,上下用两片樟木甲板,以防虫蠹,内即旧团花龙凤纹锦四合书套,象牙别字撒金的瓷青书衣……”这个就是我在卖弄我自己的那个专业知识了。
能够把这种纯粹的知识和这个情节的架构融合到一起的话,读者读起来就会顺畅。
山西晚报:您这部作品会接着往下写吗?现在才写到雍正三年。
郑小悠:这个要写完的话,其实还挺长的。从康熙末年到雍正三年就30万字了,如果慢慢写的话,起码得再写个两本这样厚的吧。起码这一次就这样,先告一段落,以后有没有机会继续写下去,那得看时间的问题。
山西晚报:《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写了年羹尧之死,那以后还有隆科多之死,还有这么多人要纷纷退场,得有个交代吧。
郑小悠:可以一直写下去。我觉得我以后可能还会写那种案子,就是我自己做法律史,我之前出过一个书叫《清代的案与刑》,那些案子其实蛮适合写成小说的,而且适合写成那种连续性的,就是跟连续剧一样的,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虽然他们都不是一个时代,但是你可以把它强行挪到一个时代里面来。因为我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得也比较多,当时写博士论文搜集了好多特别奇葩的案例,我觉得以后写成小说也挺好的。
山西晚报:您最后有想对读者说的话吗?
郑小悠: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是从十几年前,我在晋江上胡说八道就支持我的老粉,一支持说是十几年。而且大家都是一直盯着我,说新出了什么书,然后就马上去买了。如果不是大家的这种鼓励、这种支持,没有这个动力,我很难坚持下来。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