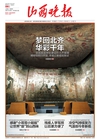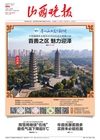铜簋:息族消逝的秘密
文物档案
主角:铜簋
体态:高21.5厘米、口长23.7厘米、口宽19.5厘米、底长19.6厘米、底宽16.8厘米,重7.54千克
出生时间:商
出生地:山西省临汾市庞杜遗址
藏宝地:临汾市博物馆
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庞杜村西北范河南岸的台地上,有一片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商周墓地,2002年,临汾市文物局发掘了其中4座墓葬,出土了一批文物。这些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并有商人埋葬习俗的殉人、殉狗现象。最引人注目的是M2,不到11平方米的墓穴中随葬品丰富,有青铜器、玉器、陶器、蚌器、漆器多种种类。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容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最为重要的是青铜容器大多铸有铭文,铭文内容指向一个古老的氏族——息族。
M2出土的青铜容器分别为“息父庚册”铭铜鼎1件、“息父乙册”铭方簋1件、觚2件、爵2件(其中有铭文“子刀”)、“息册”铭尊1件、“息册”铭卣1件。鼎、簋、觚、爵、尊、卣……这几种容器在商代均为核心礼器,有着较为复杂的组合形态。晚商至西周早期,两种器物组合最为常见。鼎与簋的组合发展到西周时期,奇数的鼎与偶数的簋配套成为礼仪活动的主祭礼器,由此形成制度。觚与爵的组合,每种都存在器形、大小相同相似两件组合的情况,即汤毓赟先生所概括的青铜器“觚爵成套+偶数配列”的组合现象。而这些同出的两件器形、大小相同相似的器物,也是列器的形式。这种现象存在于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以觚爵这对主要礼器套数的多少形成等级,并伴有其他的青铜礼器。尊与卣的组合在殷墟文化末期觚爵制度走向没落之前兴起,在西周早期用来弥补礼器组合中觚爵的减少,基本上以1尊1卣和1尊2卣组合为主。值得一提的是,M2还发现同青铜礼器叠放在一起的8件漆器,器形不辨,存有红漆痕迹,其中2件口部为圆形,还有一件饰有蚌饰,很有可能也是礼器。在礼器组合中,也时常用不同材质来表示不同器物,这是早期礼制的特点。
商人重酒,周人重食。M2里觚爵组合各为2件,形成这一墓葬礼器组合中的重心,与商人重酒不无关系。然而晚商礼器同时也在逐渐凸显食器的地位,觚爵组合加配鼎的形式,再加上簋,形成觚、爵、鼎、簋的配置。学界认为,殷墟三期改青铜礼器重酒组合为食器和酒器的复合形式,这是铜器组合“有了根本的变化”,鼎簋觚爵组合几乎占了一半的数量。殷墟三期簋在礼器组合中的出现,已经有了重食的倾向。鼎与簋的结合,与觚爵并行,在M2里显示了重酒重食的复合组合,其中重酒的程度略高于重食。
M2的这件铜簋簋身形制类似圆腹圈足簋,但底座为方体,因此这件簋应作方簋。敞口方唇,折腹圜底。依据考古报告描述,簋腹两侧各有一粗大的兽耳,呈现两条卷龙的形态。腹部及底座束腰处四角及其每个面的中部各有一条高扉棱,每面扉棱两侧均以雷纹铺地饰有对称的双首联体夔纹。底部外侧留有合范铸造的菱形方格,内侧铸铭文“息父乙册”。四腹纹饰相同,中部靠上有一道凹弦纹,将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饰对称鸟纹,下部饰凤鸟纹。
根据统计,殷墟青铜器中方形器数量和比例要远远超过西周青铜器,所以,方形器是商人的传统。在整个晚商,方圆器的搭配十分常见,M2圆鼎方簋的组合也说明了商代礼器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件方簋在纹饰上装饰了仅在商末周初流行的大凤鸟纹,学者韩炳华认为,大凤鸟纹应该是多种文化融合的创新艺术形式,此类纹饰在地域上集中于宝鸡一带,是初到宝鸡地区的殷人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创新的艺术形式,随着一些殷遗民的分化与迁徙,这种艺术形式很快消逝。
M2出土的青铜器里4件铸有与“息”相关的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这是息族器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河南罗山蟒张、天湖一带出土了大量铸有“息”族徽的青铜器,由此确定河南罗山蟒张、天湖附近就是商代息国。根据甲骨文可知,息在商代为商王朝的重要封国,并有女子嫁为商王后妃,称为妇息。作为国族名,“息”最早见于殷商卜辞和商金文,其就封或与商王武丁征伐荆楚、获取长江中游地区铜矿资源的军事部署有关。
李伯谦、郑杰祥先生认为,息国至商代末期依然存在,进入西周初期,该国或徙或亡,始由西周姬姓贵族所代替。周代的姬姓息国可能从商代息国的旧地东徙至今河南息县,史称“新息”,是周王朝在江、淮之间的重要屏障,进入春秋后被楚所灭。
有学者认为,周灭息后,息族一部或被西迁至今天的关中西部地区;一部或被赏赐与成王之弟唐叔虞,北迁至今天的山西临汾庞杜一带;一部或被赏赐给西周开国之臣齐侯姜尚,东迁至今天的山东地区;一部或被赏赐给曾国,南迁至今湖北随州一带。同样也有学者推断,息国入周后被迁徙至山西汾河下游,这也是山西临汾地区出现“息”族墓地的原因。
除罗山天湖墓地和临汾庞杜之外,晚商“息”族铜器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岐山也有发现。分析者通过对这些铜器铭文彼此关系、字体时段等方面的研究推断,庞杜出土的“息”铭铜器的铸造者和最初使用者,乃是一位或一群迁居晋南地区却依旧秉持商文化传统的“息”族人。而带有“息父乙”“息父庚”铭文的铜器,应该是为祭祀他们埋葬于天湖墓地的父亲“息乙”“息庚”所铸造的。
铭文中的“册”,现在普遍认为是代表“作册”这一职官。据学者张亚初、刘雨考述,“作册”始见于商代,盛行于西周早中期,消失于西周晚期,西周中晚期以后被内史及内史尹所代替。作册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人,是各种礼仪的参与者,是各种政治、宗教活动的参加者。
十余平方米的墓葬充满了诱惑,关乎礼制,关乎氏族,关乎方方面面。“息”灭之后,一“息”尚存,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历史疑问。
唐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