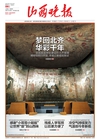取经传奇——两位文化学者笔下的高僧法显
中医振兴话法显
著名法显文化研究专家,曾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袁维学先生,在其长篇历史小说《法显》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法显西行之开端的细腻描写:“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三月的一天,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出了长安城,沿着一条大道,往西而行。法显身着缁色直裰,脚穿黑色布履,右肩背着一个包裹。包裹内除了换洗衣裳外,还有文房四宝、针灸用物等。”
这段描写,可谓袁先生的神来之笔,因为在法显自己所写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中,关于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出征,只留下了寥寥几行字:“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
也就是说,法显自己并没有对西行之始的随身行李究竟带了些什么留下记载。但是,袁维学先生的描写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西行之始,法显已经65岁,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西行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虽然不是了如指掌,至少应该是有所预测的。正如我们今天每一次长途旅行都一定会准备些基本药品一样,法显他们随身携带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是太正常不过的。更何况,在历史上,许多大德高僧本来就与医学名家合二为一。《襄陵县志》(光绪版)就有这样一段记载:明代时,襄陵县圣寿寺中有一位叫做金碧峰的高僧,“尝游五台,后成正觉,洪武太祖诏旨阙庭,言论称旨,御制诗以赐之。后还,仍赐金织袈裟一袭,佛经一函。年逾七十而化。”就是说,在明代洪武年间,圣寿寺中曾有一位叫做金碧峰的高僧,因为医术高超,太祖曾诏其入宫看病,看完之后还赐予其金织袈裟一袭。
同是《襄陵县志》,又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曾诏一位姓崔的道士进宫为皇后看病,并赐予其“真人”名号。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国古代,无论佛家,还是道家,甚至一些名仕大儒,往往在医学上都是有所钻研,有所成就的。譬如狄仁杰,唐代传奇小说《集异记》就曾记载,狄公因其祖上多为武将而世代相传中医绝学,尤其是跌打外科、针灸之类。概因作为武将,既要行军作战,行伍之中出现诸般外伤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将领,把统军作战与野战医生合为一体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以,青年狄仁杰在奔赴长安赶考的途中,路遇一儿童身患“不治之症”,家长在大路旁悬赏求医,狄仁杰欣然揭榜,用针刺穿透法,顷刻之间便为患儿去掉鼻腔间肿胀的肉瘤(应该是水肿),而后又在家长欲重谢时一笑拒之。
返回来说法显,还是袁维学先生,在他的《法显》一书中还有法显医己医人的故事情节。当初法显一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时候,法显就因缺水加风寒而陷入昏迷,在此危急关头,是同行的伙伴救了法显,也是法显自己救了自己。因为同伴的不舍,使得法显在喝了几口水之后,渐渐清醒,而后又是法显自己为自己针灸,使得病魔没有再行纠缠下去。这也印证了法显将银针作为随身器物的必要性。在到达天竺之后,法显又至少几次用针灸将贫穷人家无钱看病的老人和儿童从生死边缘抢救回来,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爱戴。这些故事体现在袁维学先生的小说之中,更加映衬了法显作为佛学大师自渡渡人的德行。袁先生在南亚担任外交官多年,收集了许多当地流传的有关法显的故事,这应该是他创作《法显》的底气所在,这不仅有助于法显形象的完整与高大,同样也印证了我国传统中医学术的博大精深与无可替代。
郭天印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