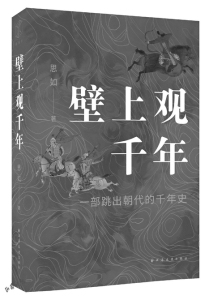《壁上观千年》,一种另类的读史视角
《壁上观千年》思如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书在尝试一种新解法,选择了公元1-1000年这个人类历史蝶变的重要千年,以百年为限,观察从长安、洛阳直至遥远的中亚索格狄亚那,从王莽篡位直至刘娥临朝,从汉人、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直至吐火罗人、粟特人,从儒学今古文经纷争直至佛教流布中土……发现其间看似割裂的人物和事件,实际是相扣的环节,共同组成历史之链,从而抛开断代的常规思维,清空那些似是而非的认知,去引导一种独立思考:历史原来可以这么读。
谈论中国古代史时,无论是宽泛讨论抑或细致研究,“断代”已成为一种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朝代”的概念具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的意义:某一段时间和某一个政权。这里的断代不仅指的是狭义的朝代,也包括了一些比较宏观的、广义的时期,例如魏晋南北朝虽然涵盖了很多个朝代,但它也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断代”。
但“断代”这种分类方法不一定公允,因为历史不是简单地记流水账。每一个朝代的历史往往有着各自最为后人所关心的焦点。虽然这些不是历史的全部,但会成为先入为主的片面理解,比如秦史中大家比较关注为什么“二世而亡”,晚明史更多聚焦于“亡国的历史教训”。由于核心焦点的差异,故而不同朝代的历史为后人所汲引的角度不同,一些共通点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叙事样貌。因此对某一朝代的充分了解是知识的基本储备,而对其它朝代历史的认识是与整体古代史对话的基础,在一个朝代中看起来颇为普通的问题若置于更宏大一些的视野中(尤其是相关联过渡时期),看到的历史纵深往往大不同。
这本《壁上观千年》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读史视角。它更像是随机地从历史长河里捞了一截,恰好千年长,根据科学研究的态度,均匀切分十段百年观察,提供了十分新颖的历史评论,足可资鉴。这一千年以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为始,以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刘娥为终,从西汉末到北宋初,从公元1年到公元1000年,朝代如走马灯般更迭,但这仅是浮在表面的上层权力置换,真正的历史发展在民族、疆域、文化等更广泛的层面展开,当我们感叹王朝兴亡、唏嘘英雄起落时,常常有意忽略这些深层的看似不那么戏剧性的实则巨大的变化。
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对史料的运用和解说流畅自如,通俗幽默,相较艰涩的史书或有门槛的学术著作,阅读难度是大大降低了,完全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而在政治制度、民族融合等多视角的连续变化中,一气呵成地回望过去,为更理性地认识过去和当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视角。
《史记·项羽本纪》曰:“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壁上观”常比喻坐观成败,不偏向任何一方。书名缘于此,也是希望能不带入个人情感地冷眼看历史,在秉持春秋笔法的历代史书中,淡化笔削之义,发掘历史真相。
海燕
《壁上观千年》节选
王莽改制的幻灭
王莽改制是一场依据《周礼》的复古运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进行的理想化运动。《周礼》被不断“改造优化”,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圣经》,周公也被塑造成为道德楷模,因为他是孔子的楷模。
王莽像极了一个满腔热血的20世纪进步青年,空有理想抱负,却不能结合时政,这种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社会的改革举措不仅不符合贵族世家的利益,就连“仁政”维护的百姓也难以幸免,何况这种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势力乘乱而起。再加上在公元8年至23年间自然灾害频繁,旱灾、蝗灾、涝灾、水灾、地震等灾害接连不断地在各地发生。最终,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爆发,随后墙倒众人推,官僚贵族和地主豪强也纷纷打出反王莽的旗帜。公元23年,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彻底碰壁,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失败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改革措施过于超前,但却没有配套的跟进技术。例如贷款利率的计算和货币改革的推广,货币制度是很复杂的工序,涉及大量的运算、换算等复杂的会计成本,但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提供这些人才。《汉书·王莽传》有曰,“农商失业,食货都疲惫,百姓哭泣在市道”,在缺乏基本社会条件下推行的改革,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大家根本没办法做生意。
二是过于迷信严刑峻法和道义,忽视了自然形成的社会惯性和人的自私本性。王莽自以为执行正义,所以无所畏惧,遇到所有反对的声音,他的唯一对策都是镇压。根据“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的描述记载,当时全国各地都络绎不绝地运输着各种囚车,里面关押着反对王莽新政的各种犯人。
以废奴制为例,道德层面的确至高无上,但真正实施起来呢?首先奴隶主就反对,因为奴隶就是他的财产,怎么可能简单地放弃自己的财产呢?奴隶们也反对,因为在土地兼并严重的封建时代,卖身为奴可能是唯一活路了。况且如何安置突然释放的众多奴隶?活不下去只能造反。
白居易《放言五首》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似乎一语道尽了后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