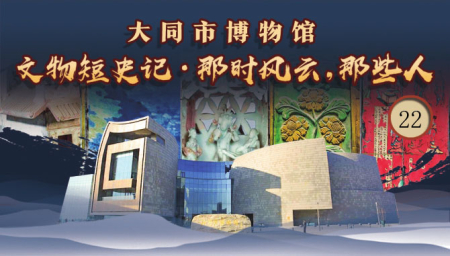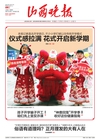元代王青的65年人生
一个八品小吏在时代齿轮中的浮沉
王青是谁?
不过元代一个八品小吏罢了。
晋南的平阳府是他的故里,
晋北的大同府是他的生长之地。
扛着刀枪的父亲壮年早亡,
幼年的他跟随母亲改嫁,
自此,他姓了继父的姓,
改名王青。
从小小军户的小兵,
一步步成长为大同府的录事司,
虽只是八品小吏,
倒也是生活无忧。
儿孙满堂,承欢膝下,
若不是这墓志寥寥数语,
谁能知道历史上还曾有个他?
1957年,在大同北郊白马城发现了一座元代墓葬。墓室平面呈方形,坐北向南。墓室后部砖砌棺床,停有木棺两具,棺内分别安置男、女尸骨一具。墓葬中出土各类遗物54件,包括陶家具、铜镜、墓志、藤帽、拐杖、念珠等。
墓中出土墓志一方,内容如下:
“大同府录事司,赞德坊居住……祖父实平阳府汾西县……父因兵革而至西京,自幼亡其父……后改王成为妻,随与继父王成同……庄附籍签充军户,世为农商,同母兄弟四人。寿年六十五岁,于元贞二年(1296年)八月十九日亡化。妻高氏、卫氏,长男仲璧、次男仲信、次男仲诚、幼男金刚奴,孙男典驴、次孙帖疙疸、次孙伴哥、次孙迴光奴、孙女妙哥,大德元年八月末旬吉日男王仲璧志”。
墓志虽有残缺,但只言片语中,依然有很多信息,为我们勾勒了元代一位名叫王青的八品小吏的人生轨迹,也揭示了元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一、晋南祖籍,平阳汾西
墓志记载,王青“祖父实平阳府汾西县……”,此为王青祖籍。根据《元史》记载,“晋宁路,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九年(1305年),以地震改晋宁路。户一十二万六百二十,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领司一、县六、府一、州九。”晋宁路(平阳路)治临汾县(临汾市尧都区),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石楼、灵石、榆社、和顺等县以南地区。府领六县:临汾、襄陵、洪洞、浮山、汾西、岳阳。王青在世时,晋宁路尚名平阳路,墓志中所称的“平阳府”,沿用了金代旧称。王青祖籍,大致在今临汾市汾西县一带。
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南下出兵攻打北宋,占领宋朝河东路(今山西),天会六年将宋朝河东路分为河东北、南两路。河东北路,治所在太原府(今太原市),下辖山西北部1府12州。河东南路,治所在平阳府(今临汾市),下辖山西南部2府10州。包括汾西县在内的平阳府全境,都归入了金的版图。
二、幼年丧父,随母改嫁
根据墓志中记载的卒年和年龄推断,王青出生于1232年。此时,蒙古与金的战争正处于关键时期。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与木华黎的遗志,按照成吉思汗制定的“联宋灭金”战略计划,“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直捣大梁”。1234年,蒙古灭金。墓志记录王青父亲因战争而至西京(今山西大同),其父参与的战事,可能就是蒙古与金朝大小战争中的其中一场。
沙场隔断了王青父子之间的亲密,幼年王青还不曾明白父爱为何物,父亲就已早亡,母亲改嫁王成为妻。自此,王青便跟随继父姓王。在元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妇女再嫁者比比皆是,“江南风俗侥薄,妇人有夫,尤受雇於人,夫亡不嫁者,绝无有也。”王青父亲因兵革而至西京,其父亲大概是兵将之类。关于军妻再嫁,《元典章·兵部》中有记载,元廷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规定,“今后莫若将此等鳏夫寡妇,照对年貌相应,官为配对成户。”元廷会强制丧夫的军妻嫁给丧妻的军人,所生的男子将继世为军。
三、附籍在册,签充军户
随母亲改嫁后,王青附籍,签充军户。附籍,即登记入户籍,获得官方的户籍许可,相当于现在的上户。蒙古灭金之后,开始在原金朝统治地区清理户籍土地。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任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对中原户籍的全面清理,得户八十七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史称“乙未括户”。王青的附籍,极有可能就是在这次人口大普查中完成的,其户籍类型为军户。
军户的划分出自元朝的“诸色户计”制度,色指种类,计为统计。元朝将全国的人户以职业、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划分为数十种户计,如民、军、站、匠、盐、儒、僧、道等。其中军、站、盐、匠等户是国家强制签充的,儒、僧、道等户是国家通过考试或其他方式认可的。每种户都对国家承担特定的封建义务,如军户出军、站户当站、僧道念经等,赋役负担各不相同。
军户有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户和新附军户之分。专服军役的蒙古人户称为蒙古军户和探马赤军户。从窝阔台在位到忽必烈至元初期,多次签发汉地产多丁壮的“殷实人户”充军,世袭军役,称为汉军户。汉军户按贫富相资,规定富家每户出兵一名,称独军户;贫家合两、三户出一名,称正军户,其余为贴军户;士卒之家,为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充军,称余丁军。元朝灭南宋时收集南宋的军队,称为新附军,有家属者便称为新附军户。
四、步履维艰,官至八品
元朝军户必须出成年男子到军队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代相袭。王青成年后,自然也按照军户要求,在军队服役。想来王青定是聪慧机敏,表现出色,才能从军队小小兵卒,一步步成长为西京的录事司。《元史·百官志》中记载,“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按照《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隶属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管辖一领事八州。一领事是录事司,设在大同。
关于元代大同录事司的考古发现,除了王青之外,1986年7月发现的大同齿轮厂元墓中,也有墨书题记“大元大德二年岁次戊戌五月上朔日建;大元国山西路大同府录事司毛宅封”。录事司的设置,“中统二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
五、桑榆晚景,儿孙满堂
虽然只是八品小官,但王青也算是生活安稳、衣食无忧。他娶妻高氏、卫氏,生有四子,长男仲璧、次男仲信、次男仲诚、幼男金刚奴。又有孙子孙女5人,孙男典驴、次孙帖疙疸、次孙伴哥、次孙迴光奴、孙女妙哥。值得注意的是,王青子孙的名字——金刚奴、典驴、帖疙疸、迴光奴、妙哥等,非常趣味且口语化,反映了当时起名的特色。
以“奴”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流行。如王献之小字官奴,刘裕名寄奴(“人道寄奴曾住”所云)等。金刚奴这种有明显佛教色彩的名字,则是与佛教信仰相关。父母会给孩子取宗教或神佛的小名,希望菩萨神佛保佑他健康长大。这种起名在辽代犹为多见,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小名叫“文殊奴”,辽国长公主耶律观音奴、将领萧观音奴等。王青的幼男名为“金刚奴”,应当也是受到这种起名观念的影响。
在王青墓中,合葬的女性墓主人身边,随葬佛念珠、莲花纹铜钵、铜盘等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文物,表明王青的这位夫人极可能是佛教信徒。由此,给幼子取名金刚奴也是情理之中了。以“哥”为名的多是契丹贵族女子,如景宗有女名淑哥,圣宗有女名燕哥、陶哥等。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右旗乌图山前(辽黑山)的《黑山崇善碑题名》,碑文中即载有“刘释迦奴”“孙王家奴”“孙西京奴”“六院司契丹郭家奴”“刘千家奴”“张百家奴”“田长讲奴”以及“妻永哥”“妻萧哥”“妻延哥”“妻巧哥”等类似称谓。元代显然也沿袭了这种起名方式。王青孙女名“妙哥”,想来是取“美好少女”之意。
“帖疙疸”之名,则更多地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影响。“疙疸”是晋北地区方言中的词语,如“乃心疙疸”,意为“宝贝疙瘩”。用于人名中,多为男性,家中兄弟数人者,常按排行取“二疙疸”“三疙疸”“四疙疸”等名。直到现在,大同地区也常见此类人名。
而至于“典驴”这样的名字,《辽代石刻文编·补编》于《耶律宗教墓志》下云:“按,《皇子表》耶律隆庆有五子:‘查葛、遂哥、谢家奴、驴粪、苏撒。’”《元典章》中记载了元代秀哥与王驴哥的婚书:“若女婿驴哥游手好闲,打出调入,不绍家业,不伏丈母教令,此文字便同休离”,以及至元三年孟野驴与哇哥的婚书:“已后并不得走出调入,不着家业,不做活计,此文字便当休离。”其中的驴粪、野驴、驴哥等名字,笔者想大致和“狗剩”这样的名字类似,取“起贱名好养活”之意。
文/白月 图/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