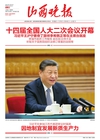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
中条山下盐湖畔 再现仰韶早商华光
发掘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林森
这里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存为主体的遗址,也是距运城盐湖最近的古代核心聚落遗址之一,这里就是夏县辕村遗址。
辕村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裴介镇辕村南部,遗址东、南部为崎岖高耸的中条山脉,西、北部为相对低缓的鸣条岗丘陵,南部为运城盐湖,遗址临芦沟河,属于青龙河的下游河段。
2023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对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青铜器、玉器、骨器等820余件,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考古遗存面貌提供实物资料,可探究陕晋豫地区及黄河流域仰韶中期聚落形态和环盐湖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特征。
从新石器至明清 遗存跨越五个时期
“本次考古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是目前对辕村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至夏商时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林森介绍,2023年发掘区位于辕村遗址的东部居中,靠近环壕,地势西高东低,文化堆积西薄东厚。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为配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1级考古学专业本科生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建设完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配合国家文物局开设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2023年8月3日起至12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对夏县辕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林森介绍,经发掘,整个遗址已知有两层。其中,第1层浅黄褐色砂质黏土,为近现代耕土层;第2层红褐色砂质黏土,为宋金时期文化层。堆积一般厚0.5-1.5米,部分探方深度超过3米。其间,发现丰富的遗迹,出土众多的遗物,包括陶器、青铜器、玉器、骨器等,遗存大致分为新石器、夏商、战国秦汉、宋金、明清五个时期。
此次发掘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可细分为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三里桥文化。庙底沟文化遗存发现最为丰富,遗迹以灰坑为主,还有部分房址和墓葬、窑址等。灰坑有弧壁圜底、口小底大的袋形坑,带有通道的洞室形等,坑内堆积多有分层,出土有陶球、陶盆、陶罐、陶钵、小口尖底瓶、葫芦口瓶、骨簪、骨锥、石斧、石陀螺形器、陶刀等,此外,还出土大量陶片和一些动物骨骼残渣,部分灰坑的性质为窖穴;房址内部多包括灶、居住面、柱洞、隔墙等遗迹,平面形状呈近圆形、圆角方形、五边形等,出土陶片有红陶、夹砂灰陶、彩陶等。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数量较少,仅见有个别灰坑和陶器残片,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表主要饰篮纹、附加堆纹,附加堆纹多呈条状。三里桥文化遗存数量也较少,仅见有个别房址,陶器残片,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器表饰以按压纹和附加堆纹,附加堆纹多呈条状。
夏商时期遗迹以灰坑和墓葬为主。陶器多为灰陶或灰褐陶,以夹砂陶为主,器表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等,以中粗绳纹最为普遍。器形有鬲、罐、尊、盆、豆、甗等,器物多见舌形和横耳等造型,其他遗物有青铜器、骨器、玉器等。
此外,战国秦汉时期遗存数量较少,仅见有个别灰沟,遗物以瓦片为主,泥质灰陶,制成火候较高。宋金时期遗存数量同样少,仅有少量墓葬与灰坑,出土瓷器、掌纹砖和青、白瓷片等。
出土820余件器物 彩陶器青铜器又有新发现
纹饰精美的庙底沟彩陶器、朴素轻薄的早商青铜器、光滑润泽的宋金民窑瓷器……此次发掘中,诸多珍品均有耀眼的亮点。
距今5000年前,庙底沟文化不仅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独树一帜,更是将其独具特色的彩陶艺术及其中承载的人文观念和精神信仰向外传播扩散,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林森解释,在当时,彩陶图案并不是商品化生产,所以,每一件彩陶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此次发掘中,出土了黑、红二彩相间并绘制弧边三角和圆点纹的彩陶盆、彩陶罐等,彩陶类艺术品出土数量较多,丰富了夏县辕村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彩陶文物的多样性。
青铜器和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生动写照,山西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相较于之前的发掘,此次发掘最主要的收获之一就是随葬青铜器和玉器的两座墓葬,墓葬规模并不大,但随葬的青铜器和玉器等珍品,规格高。很难得。”林森介绍,商代早期可以细分为二里岗上层和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下层还要更早一些,此次辕村遗址M12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两座墓葬均属二里岗下层二期,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发掘的青铜器是一个时期的,属于山西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
M12开口于红褐色砂质黏土层下,土坑竖穴墓,墓口长2.32米至2.54米、宽0.86米至1.12米、深0.6米至0.7米。墓主男性,年龄约35岁,人骨保存较为完整,随葬除陶盆、陶鬲外,还有青铜爵、青铜刀两件青铜器。林森解释道,商代重酒,多以酒器作为礼器,青铜爵作为礼器,在礼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突出“礼”的本质和社会功用。“发掘中收获的青铜爵器型比较轻薄,纹饰比较简单,呈现出来比较原始和朴素的风格,说起来看似像一个缺点,但其实这是年代非常早的青铜器才有的制作工艺。”林森描述道。
此外,此次发掘中,宋金时期墓葬中发掘到一些瓷器,如瓜棱瓷罐、瓷瓶等,工艺虽达不到官窑水平,但可以说是民窑中比较精美的,反映了晋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密集、文化传承有序的沃土,一直到宋金时期,这里依然是富饶之地。
据统计,2023年度发掘区共发掘房址21座、灰坑270余座、墓葬15座、瓦棺葬1座,灰沟5条、道路3条、陶窑2座、灶址2座、零星分布的柱洞6个,出土器物达820余件。
成果与学术共促 探究晋南遗存培养考古人才
夏县辕村遗址地层堆积清晰,遗迹间打破关系复杂,遗存年代跨度长,遗迹类型全面多样,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考古遗存面貌提供实物资料,可探究陕晋豫地区及黄河流域仰韶中期聚落形态和环盐湖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特征。
2005年至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多次在辕村遗址及周边区域展开考古工作,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的文化发展序列,为研究晋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演变、消亡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遗址所依盐湖,提供的盐业资源与遗址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对探索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资源控制与利用,具有重要价值。
2023年度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辕村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性质和遗存特征。该遗址是距离盐池最近、规模最大的仰韶时代中期环壕聚落,为了解仰韶中期盐湖附近生业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发掘的辕村遗址庙底沟文化遗存,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启示;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中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遗址内发现的随葬青铜器和玉器两座墓葬属早商二里岗下层二期,为探索晋南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和社会关系补充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23年度对辕村遗址的发掘,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更多有价值的遗迹文物被发现和出土,而且在于为国家培养考古界栋梁提供了田野实践的平台,可以让考古界人才在‘古中国’的土地上,完成田野考察和历练沉淀。”林森介绍,参加2023年度辕村遗址挖掘的团队包含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学生39人、国家文物局田野实践训练班人员14人,每个人至少完成了一个探访的发掘,相当于一套完整的考古操作的训练,非常难得。其间,考古的不可逆性,让大家谨记文物安全的重要性,每一铲都要经过科学规划、深思熟虑,从地层剖面认真分析、辨别土质土色,再从出土器物确定使用年代。
林森表示,人才建设是考古事业发展的根基,新时期的使命对考古专业人才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而考古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正是田野实践。考古人一次次躬身田野的执着,沉睡在泥土中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才得以被唤醒。2024年,还将有新一批的考古专业学生加入到辕村遗址新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中。
山西晚报记者 张彩云
1.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盆。
2.宋金时期的瓜棱瓷罐。
3.早商时期的青铜爵。
4.辕村遗址2023年发掘区航拍图。
5.夏时期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