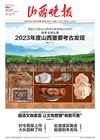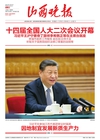喜看小村变化多
癸卯年腊月廿八,随着返乡的人流一道,我回到家乡漫云村。这个小村有山、有水,有澄澈的天空,有湿润的空气,有我熟悉的方言、至亲的亲人和朋友,还有让我一想起来就激动万分的家乡的气息。
屈指算来,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尽管我只在这个偏远小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但小村的一切却刀刻斧凿般烙在我灵魂深处,常令我怀想,常令我向往。
每年春节回乡是我的必修课,每次回乡,也都深切感受到小村点点滴滴的变化。
小村有一条老街,上世纪80年代最鼎盛的时候老街有近百户人家,五六百人,许多建筑都还是明清时期的木结构古居。那时候,老街最紧缺的是宅基地和住房,有人家十几口人挤在三间窄小的房子里。为争一块宅基地或只屋片瓦,父子、兄弟大打出手、反目成仇。有兄弟多的,实在没房子,只得去了外地入赘当女婿,这在当时是令人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走出山里的世界,慢慢有人搬离了老街,有人进城定居。
三年前,镇里统一规划建设新农村,沿老街背后建起了几十栋别墅似的小洋楼。新农村安了自来水,装了路灯,垃圾进行了集中处理,洋楼装修后,其条件完全可以和城里媲美,老街的人们相继搬进了新居。昔日喧嚣拥挤的老街渐显萧条与荒凉,有几栋搬走多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已经垮塌,令人惋惜。
我来到老街背后的山坡上,这里原本是一大片梯田,都是大集体时人工开出来的。刚分田到户那会儿,这些田被各家争抢着要,其中还有我家一亩三分地。那时候种蚕豆、种小麦,每年收成都不错,只是不通路,耕种收都得肩挑背驮,这一大片田地渐渐没人种了,也就荒芜了,杂草丛生,令人不由得惋惜。
去年冬,村里动用挖掘机修通了路,又人工清除杂草灌木等杂物,计划将这片土地复垦后种植瓜蒌子。弟媳是村支部副书记,据她介绍,村里去年发展瓜蒌产业,收获瓜蒌籽近两万斤;瓜蒌皮可以药用,也值钱,村里去年仅瓜蒌这一项产值六十多万元。如今,村里已复垦了数十亩地,如老街背后山坡这样偏远且交通不便被撂荒的土地,然后种植烤烟,年产值四十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有了较大幅度增长,留守在村里年龄较大的村民可以参与瓜蒌和烤烟的种植及管理,不出村就有了“工作”,收入稳步提高。人勤春早,正月初二,弟媳就趁着拜年的时机,和周边几家有挖掘机和农业耕作机械的人联系,确定好了去老街背后山坡那片地复垦开工的时间。
因为过年,回村的人不少,很多家的门前停着小车,车牌也来自全国各地,昔日略显沉寂的小村热闹起来,过年的气氛浓郁。正月初一,各家各户互相串门拜年的习俗还是没变,天刚亮门外就不断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断有人进来,吆喝着“拜年喽!”来的人许多我不认识,总是要居住在老家的弟弟一一介绍,说是某某家的某某,方能勾起一段记忆,叙上几句家常。
表叔国强来给我拜年,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他早已搬离小村在外买房定了居。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大学毕业去了深圳,过年没回来。小的这个12岁,在县城读书。当初生小的这个还没有放开二胎,还被罚了钱。国强叔一直在外打工,却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村里和镇上有小学和中学,他却坚持把这个二孩送到县城去读书,他老婆也就是我表婶,还在县城租了房子长期陪读,仅此一项每年得好几万元,为的是县城教学质量好。为孩子,他说这些钱花了值。据他说,像他这样在城里租房陪读的家庭很多,有的是妈妈陪,有的是爷爷奶奶陪。重教,在乡村已成为风尚。
时光的脚步总是匆促。正月初三返城,那天早上,邻家二婶给我送来数十个饺子,饺子馅儿是地里新采回来的荠菜。还有一大捆鲜嫩的菜薹,薹尖儿上挤挤挨挨地缀满了行将绽放的米粒般的花蕾。
春,已悄然而至。
□韦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