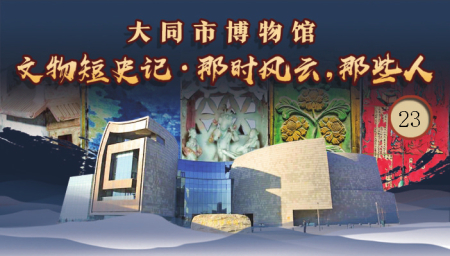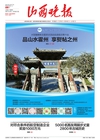元代崔莹:晔兮如华 温乎如莹
她不问出处,
但不能没有归宿,
一床一椅一供桌,
是“家”舒适的温度,
更是她“余生”的庇护,
在沉淀的历史中,
一直住着朴素的灵魂。
一、元代崔莹:莹莹之光迢迢相望
1976年4月,大同市北御河灌溉管理处工人在曹夫楼村挖自来水管道时,发现了一座方形券顶砖石墓,墓壁涂白灰,无壁画和文字。此墓出土随葬品46件,其中包括玛瑙耳坠、戒指及陶制器物等。墓主人为女性,她正是“崔莹李氏”。
“古人卜葬,必先作买地券,或镌于瓦面,或书作铁券,盖俗例如此。又必高估其值,多至千百万,又必以天地为证,殊为可笑。然此风自汉晋时已有之。”买地契自汉代兴起以来直至清朝,成为丧葬中的重要环节且历代不衰。
山西地区现有宋元时期买地券30块,其中,崔莹李氏墓中出土一件铁地券,长33厘米,宽20.5厘米。此地券部分内容为“维□统二年十月庚寅□□□□□□□□□子□□□□□今为祖考崔仲仁以庚午年□□□□□□□□□□□西京大同县东□□堂北原安□”。这块地券为朱书,“葬家听术士说,例用朱书铁券”。“朱书”之由,一是驱邪逐疫,二是道教对朱砂的推崇,再者推测是《地理新书》“朱书其文”的影响。
崔莹李氏与崔仲仁是何关系,崔仲仁又是否是清河崔氏都无从考证。但从地券内容“西京大同县”得知,大同称西京达244年之久,为辽金元之间,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大致推测为元代,又因“□统二年十月庚寅”推测此墓时代为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
二、陶制家具:痴于纹饰 醉于传承
“天赋巧。刻出都非草草。浪迹江湖今欲老。尽传生活好。万物无非我造。异质殊形皆妙。”大同元代崔莹李氏墓与同期道家冯道真、王青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家具相似,或木或陶,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家”的温度。
陶供桌
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可拆卸的雕花围栏,镶嵌的绦环板以浮雕手法雕刻细腻的纹饰,有较强的立体效果,装饰板件中的绦环板浮雕之风在元代十分盛行。同时,元代家具也受到辽金家具风格的影响,契丹工匠入驻草原,将简约实用、适用于游牧生活的辽人家具融入蒙古族家具制作中。辽代的典型榫卯连接结构——骑马榫,在崔莹李氏墓出土的这件陶供桌上再次出现,围栏横杆的交叉处以圆材十字相交、两端出头,呈扁圆柱形花饰,属典型的辽代十字骑马榫结构,这与现代蒙古族传统家具锅架上的十字榫十分相似,传承了游牧民族家具木工技艺手法。下半部为长方形桌,桌面下四周镶板,板面饰牡丹纹,腿部间旋雕花牙子券门,腿外侧与桌面结合处饰花牙子。根据家具装饰部位的不同,在元代家具中牡丹纹饰的表现形式既有写实也有写意,体现了纹饰图案来源的多元性和元代审美的融合性。
崔莹李氏墓出土的这件陶供桌和1986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出土的同类雕花木供桌,除加有上部围栏外,形制、装饰风格都十分相似。家具上设围栏的现象在辽金家具中多见,是北方游牧民族家具的一大特色。
总体看来,这件专为供奉而设的长桌制作工艺精湛,雕刻复杂,设色丰富,装饰华美,虽历经千年,仍未见明显的损坏,且色泽较新,足见当时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
陶太师椅
受宋辽时期文化的影响,高坐和高型家具进一步发展,成为元代家具的主要类型,并形成了以桌椅为中心的起居和生活方式。崔莹李氏墓中出土的太师椅长17厘米、宽16厘米、高26厘米,靠背装饰有凤鸟莲花图案,表现出如云气流般的气势,各种花卉植物纹样在家具中呈现,被赋予了不同的品质和寓意,边饰的卷草纹和造型秾丽的交椅相结合,突出了元代蒙古族对自然的热爱和吸收中原文化的融合气息。
与崔莹李氏墓中出土的陶椅相似,大同地区王青墓中出土的陶椅同样形如太师椅,还有延续到明式椅的“鹅脖”构件,且鹅脖的安装位置明显与前腿错开;崔莹李氏墓中圈椅由靠板和两根鹅脖作三点支撑。
《说文》中解:“枨,杖也。”即木柱,有支撑之意。一般用于加固腿足部件的连接,以稳定整体结构。枨的种类较多,可分为直枨(横枨)、罗锅枨、霸王枨、十字枨等。其中直枨是出现最早、运用最广的类型。崔莹李氏墓的陶圈椅足间有直枨,枨位较高,枨下有角牙承托,延续了宋式风格;王青墓出土的椅子四足间虽无直枨,单有云纹角牙,稳固性较崔莹李氏墓陶椅欠佳,而这样的造型也可能是宋式风格的延续。靠背椅的运用也证实了元代已经有了类似明式家具符合人体工程科学的意识,在宋代家具风格的基础上,稍作改动,也体现了元代家具不断过渡发展的演变过程。
陶屏风架
依据墓室考古壁画和书画资料,元代坐具较为多见,其次是架具和屏风类家具,架具的分类集中体现了元代家具功能细分的趋势;屏风的大量出现和使用,体现了屏风显示权威的功能逐渐减弱,更加重视其空间分隔的实用功能。屏风的类型主要有座屏,插屏,影屏,门隔扇。崔莹李氏墓中除陶巾架外,还有两件陶影屏出土,一件版心有连钱纹,一说为球路纹,但在《营造法式》中记载:“球路纹的标准样式应只有四圆相交,而纹样中间孔形为方形的球路纹,则不应该叫做球路纹,应称这种纹样为连钱纹。”这种说法不仅对连钱纹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同时也在侧面印证了连钱纹是球路纹分支纹饰的说法,这种纹样布局具有强烈的秩序感,富有装饰意趣;另一件版心镂空,镂空部位视线通透。
在元代北方家具中,透雕多见于衣架、屏风、绦环板等装饰部位。透雕比浮雕更进一步,虚实相间,镂空之处具有透气感,形成隐约可见的光影效果,不仅衬托出花纹的部分,还具有类似漏景的含蓄意味。
这件影屏顶部两侧设三叶卷云头,框架上部装饰两幅云纹图案,中部以菱形纹为中心,两侧对称装饰镂空卍字纹,下部有两幅似壸门的镂空图案。
卍字符是最古老、最常见的象征符号之一。卍字符最初被认为是吠陀神湿奴的太阳象征物火轮或是毗湿奴独特的发旋或胸前徽相。佛陀的胸前常画有卍字符。在金刚乘佛教中,卍形字符基本上象征着四大要素之一“地”及其不可摧毁的稳定性;在西藏苯教中,意为“永生或不变”,本质上与佛教的金刚相符。在古代中国汉地,卍字符最初是道教永生的象征,用“卍”字四端向外延伸,演化成各种锦纹,寓意绵长不断之意,也叫“万寿锦”。“万”字代表世间万事,其意为“福社”“好运”“成功”或“繁荣”。
三、精工巧匠:以匠人心 琢方寸美
历史变迁,见证了文物的演变沉浮。凝视文物,诉说着历史的悠远故事。在印刻着时代文明的记忆中,我们守望与传承;在岁月沉淀技艺的文物里,遇见背后的匠人。
元时期蒙古族自身工艺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仅能满足简单的日常生产所需。因此,当时统治者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在战争中注重工匠群体的保存,俘虏了大批的工匠,补充了蒙古族工匠人数,元初充作匠籍的各族工匠人数十分庞大。
元代以其辽阔的疆土,打通了东西交往的通道,道路畅通、商贸繁荣,来自俄罗斯、波斯、欧洲、北辽和中原等地的工匠、传教士及诗人涌现,增进了各地的交流交往,这些人员与契丹工匠、汉人工匠、草原蒙古工匠一起创造了造型多样、工艺精美的家具。工匠人群的多元化,也加速了文化文明的交融程度,外来工种和技艺不断输入,促使元代蒙古族手工艺快速提升,创造了大量的手工艺精品。尤其是元代陶家具大量使用浮雕或圆雕的植物纹样,在桌、椅面板下设置挡板,为元时期抽屉桌提供了前提;椅子扶手下方出现“鹅脖”构件……无不见证了高型家具由宋代普及型向明代成熟型发展的作用。
开放的民族政策,通达的丝绸之路使得多元文化在元朝汇聚,并不断融合。这种多地多民族的工匠迁徙,不仅为手工业生产领域准备了人才条件、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他们吸收不同文化元素,为各民族工匠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使得元代各族工匠之间有机会进行多元融合,从而创造出集不同民族风情、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家具风格——既有豪放不羁的格调,又有繁复华美的情趣。
文/文慧 图/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