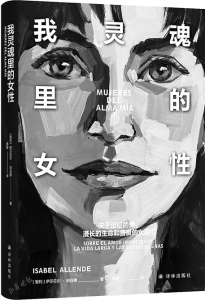一本献给所有女孩的人生之书,《我灵魂里的女性》节选——
如今正是我这漫长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我灵魂里的女性》[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著 谭薇译 译林出版社
目睹被父亲遗弃的母亲在没有工作、被人“指指点点”的情况下独自抚育三个年幼的孩子,阿连德决心为母亲无法拥有的生活而战。临近八十岁高龄的她,将毕生经历与思索书写成册,追忆三段充满激情的婚姻,趣谈衰老的不便与新知,痛斥父权社会下的性别暴力,以此向生命中“那些可爱而伟大的女性”致敬。是什么滋养了所有女性的灵魂?感到安全,受到重视,性别平等,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最重要的是:勇敢地爱与被爱。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家人还不知道女性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出生于1942年,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段遥远的过去。在我看来,我对男性权威的抗拒源自我母亲潘琦塔的经历:她在秘鲁被丈夫抛弃,只能孤身带着两个裹着尿布的孩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回到智利父母的家中寻求庇护。我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我外祖父母的家在圣地亚哥的普罗维登西亚区,这个区域如今宛如一片迷宫,商铺和办公楼林立,可在当时还是一片居民区。外祖父母的房子虽然很宽敞,却并不美观,就像水泥堆砌而成的怪物。房间的顶很高,四处漏风,里面有被煤油炉熏得发黑的墙壁,厚重的红色长毛绒窗帘,结实得能用上一个世纪的西班牙式家具,还有一些很是阴森的已故亲人画像和一摞摞落满尘土的书。从正大门看,房子颇为气派。客厅、书房和餐厅很是雅致,可很少使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一个乱糟糟的王国,它属于外祖母、孩子们(我和我的两个兄弟)、女佣、两三条看不出品种的狗和几只半野生半家养的猫。那些猫没完没了地在冰箱后繁衍后代,厨娘只得将它们下的崽拿到院子的桶里淹死。
伴随着外祖母的早早离世,那个家里的欢乐和光亮一并消失。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是一段充满恐惧的阴暗时光。
我在害怕什么?我怕妈妈死去,我们流落到孤儿院;我怕吉卜赛人抢我的东西;也怕魔鬼会在镜子里出现。但现在我庆幸有这段不幸的童年,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我不知道那些在普通家庭度过快乐童年的小说家是怎么想出办法来的。
我很早就发现,与家中男子相比,妈妈是低人一等的。她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结果就像她父母所预言的一样,婚姻失败了。她申请了婚姻无效,在智利这样一个直到2004年才将离婚合法化的国家,这是她当时唯一的选择。她没有工作的能力,没有钱也没有自由。与丈夫分开后,她依然年轻貌美,优雅迷人,为此她饱受非议。
青少年时期的我孤僻,不合群,只能由我可怜的外祖父来“对付我”。我并非一个懒惰或是胆大妄为的孩子,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好学生,乖乖地遵守集体纪律;但我心里总是憋着一股怒气,我发怒的方式不是捶胸顿足或是摔门而去,而是长时间的沉默。我有些心病:我觉得自己丑陋、无能、卑微,被困在毫无意义的生活中,孤单无助。我不属于任何群体;我和别人不一样,到哪里都格格不入。为了排解孤独,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且每天给母亲写信。那时母亲已经离开黎巴嫩去了土耳其,她也经常给我回信,信件总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寄到,我们却并不在乎。就这样,我们开始书信往来,并将这个习惯维持了一生。
从小,我就不能容忍这世界上的不平事。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的女仆们从早到晚地干活,她们很少出门,只能获得一份微薄的薪水,夜里就睡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里,一张简陋的床铺和一个破破烂烂的衣橱就是她们所有的家具(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当然智利已经今非昔比)。长大了一些以后,我对公平的关注更胜从前,在同龄的女孩都在忙着打扮和找男友的时候,我在宣扬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这样一来,我自然没有朋友。智利在社会阶层、机会和收入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这让我愤怒。
最糟糕的歧视就是针对穷人的歧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让我最痛心的是对女性的歧视,因为在我看来,人可以脱离贫困,但永远改变不了性别决定的状况。虽说在一些女性的斗争下,那时的我们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和其他的一些权利,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高,还能够参与到政治、公共卫生、科学和艺术等种种方面,但距离欧洲和美国的女性运动,我们落后的距离以光年计。当时在我的周围,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报纸上,都没有人关注女性的状况,如今想来,我都不知道那时的自己是如何产生那份觉悟的。
我的身体在老去,灵魂却变得年轻。我的缺点和优点可能也更为明显。比起从前,如今的我更为挥霍,也更容易分心,但发脾气的次数却少了,我的性格温和了一些。我更加在意一直从事的事业,也更关心我爱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人。我不再畏惧自己的脆弱,因为我不会再将脆弱与软弱混为一谈;我可以张开双臂、打开房门、敞开心扉来生活。我喜欢自己的年龄和女性这一身份,因为正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所说,我不必去证实自己身上的阳刚之气。也就是说,我不必表现得坚不可摧。我的外祖父一直告诉我,要坚定刚强,这个建议曾在我的生活中起过作用,但如今已非必须;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请求帮助,多愁善感。
在我的女儿宝拉去世后,我充分地意识到了死亡的临近。现在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死亡成为我的朋友。它并不是一具挥舞着镰刀、浑身腐臭的骷髅,而是一位成熟、高雅、友善,散发着栀子花香的女士。以前它在我的周围和对面的房屋逡巡,如今它在我的花园里耐心等候。有时我会从它面前经过,我们打招呼,它提醒我要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充分享受生活。
总而言之,如今正是我这漫长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在经历了绝经,完成了养育儿女的使命后,生活会变得更加简单,不过前提是降低预期,远离怨恨,松弛下来并且认清一个事实,即除了最亲近的人外,没人在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干了什么。不要再为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汲汲营营、装模作样、牢骚满腹或是大发雷霆。要爱自己,并不求回报地爱他人。这是人生中最为宽和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