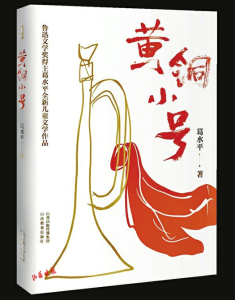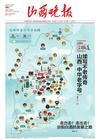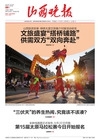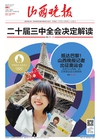山西教育出版社再推佳作
葛水平新作《黄铜小号》重磅首发
山西晚报讯 讲好山西故事,传承红色基因。8月1日,山西教育出版社与长治市新华书店联合举办了“八一”建军节特别活动——葛水平新作《黄铜小号》作品分享会。中共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霍冰、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刘立平等出席活动,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韩石山、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杜学文作为特邀嘉宾致辞。活动以“《黄铜小号》吹响在太行山上”为主题,这不仅是一次关于文学创作与全民阅读的分享交流,更是一次重温红色记忆、阅读红色好书的生动实践。
《黄铜小号》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山西省文联主席葛水平全新创作的一部红色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全书图文并茂,书写抗日战争期间在黄崖洞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少年英雄、小号手崔振芳的感人事迹,是一部赓续优良传统、弘扬抗战精神的优秀作品,表现了太行儿女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展现出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长治是葛水平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葛水平回乡首发新作的消息一发出,就吸引了大量的书迷、文学爱好者前来,现场不乏小学生和满头白发的老者。分享会后的签名售书环节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在当天的活动上,韩石山先生说,长治人杰地灵,孕育了葛水平这样一个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文学才华的作家,她深深扎根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她热爱这片土地又能跳出这片土地的局限。她笔下的文字,有灵性,有温度;她创作的《黄铜小号》,充分观照主人公小英雄崔振芳的内心成长和革命意识的萌芽、生长,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文学性,其对小英雄展现出的母性的悲悯情怀,使得图书甫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喜爱和赞誉。
杜学文祝贺山西有了一本描写脚下这片土地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儿童文学作品。他总结,《黄铜小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兼顾真实性与可读性;第二,细节方面做足了功课;第三,美好民俗与残酷战争形成强烈对比。读者能在阅读这样一本描写黄崖洞抗战小英雄的儿童文学作品时,在阅读熟悉的故事的过程中,产生全新的审美体验,并引发对人性、对战争、对文学的深入思考。
作家葛水平最后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她笔下的文字,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开作家的良知。长治是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里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著名战役,葛水平以一位作家的敏锐,将目光落在一把黄铜小号上。“写作情感的限度,事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她写崔振芳这个孩子,“只想祭奠一代英灵中一个汉白玉雕的未成年孩子,他在山水交融的角落里和一些细小普通的人物中,获得崇高”。
1日下午,长治晶海藏书馆举办了“作家葛水平携新作《黄铜小号》与读者面对面”文学沙龙。活动开始,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立平率先致辞:“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感谢葛水平老师将心血之作交给教育社,《黄铜小号》出版的各个环节都经过了细致打磨,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希望更多的读者在阅读《黄铜小号》后受到鼓舞,勇敢前行。”而后教育出版社向晶海藏书馆赠书,之后葛水平及五位特邀嘉宾与文学爱好者畅谈作品与文学。
两场活动中,众多读者慕名前来,就本书情节、主题等与葛水平展开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交流结束后,热情的读者纷纷请葛水平签名留念。
(山西晚报记者)
相关链接
《黄铜小号》的主人公崔振芳是山西洪洞县人,1937年年仅13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14岁被调到总部特务团司号班,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对山西进行大扫荡,黄崖洞保卫战打响。崔振芳请缨把守黄崖洞的唯一通道——南口,他坚守数天,投出了120多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兵数百人,弹尽粮绝之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独家专访
葛水平:一切寄于美好,一切为了孩子
“崔振芳最早拿起的是一支黄铜小号。小号是用来吹奏音乐的,红玛瑙般的音符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凯旋……”8月1日,恰建军节,山西长治,山西教育出版社重磅首发著名作家葛水平新作《黄铜小号》,太行山上重新响起的“号音”成为献给这个节日最珍贵的礼物。这一次,这位鲁奖作家又回到了她最熟悉的土地——晋东南,把视角对准抗日战争期间在黄崖洞保卫战中牺牲的小号手崔振芳,讲述了一段少年英雄成长史。这也是她在儿童文学领域的首次尝试。
大众对葛水平的认知,多停留在一些固定称谓上: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或是鲁迅文学奖得主等。近些年关于她最破圈的新闻,大约是“勇于大声维权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编剧”。但圈内人,对她一直还有另一种评价:当今中国文坛“最有女人味的才女”、文学评论界的“一匹黑马”……
葛水平究竟是怎样一位作家?《黄铜小号》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是什么让这位著名作家甘愿放弃舒适区走进全新领域?这部酝酿了30多年的作品到底体现了她怎样的人生思考?带着这些疑问,在《黄铜小号》发布前,受山西教育出版社之邀,山西晚报记者走进葛水平家,试着去揭晓这些谜底。
80年代的黄崖洞行一颗种子悄然种下
对于一位身兼数职的作家来说,时间的宝贵性不言而喻。两杯清茶上桌,没过多的寒暄,我们的对话便从《黄铜小号》的诞生开始了。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长治戏剧研究院工作时,有一次当地文联举行编剧笔会,我第一次去黄崖洞。当时的黄崖洞还没有开发,当地人穿着红军装唱着《在太行山上》,那种活泼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当我穿越悠长的峡谷,看到一尊举着冲锋号的小战士的汉白玉雕像,那就是小号手崔振芳。”那是葛水平第一次见到“崔振芳”,先是被他稚嫩的脸庞所吸引,而后就是他的故事。
“当时我对红色革命题材的东西并不熟悉,听了简单的介绍,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因为战争之于青春是非常残忍的。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他还那么小,对死亡的认知、对战争的认知都是陌生的,但还是走上了战场,他短短的生命就结束了。”葛水平慢慢回忆着。
继而,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细节开始撞击她的心。“当时流传着日本人进入中国是很亲善的,书中我也写到他们在当地挨村发馍馍。善良的中国百姓在遭遇天灾后受到救济,根本不会多想,他们甚至意识不到日本人从踏进中国大门的那一刻就是侵略了!所以,我们对这场战争是没准备的,甚至我们的国家也是没准备的。我们的民众没有武器,不知怎么抵御侵略,所以黄崖洞兵工厂的创立对地方来说、对国家来说都太重要了。我就想把黄崖洞的故事写出来。”
深受触动之后,她即刻动笔先写了一篇散文,名字就叫《黄铜小号》。而在她的心灵深处,一颗种子已经被悄悄种下,一篇更大的文章在她脑中酝酿着。30多年后,当她终于有机会出手时,毅然决定还为新书取名《黄铜小号》,她的解释是:“我对这个名字非常有感觉,因为这个孩子手里的黄铜小号就是他的武器啊!”
静心创作想让更多孩子看到
2022年,葛水平深埋心里的那颗种子终于要开花了。“那个时候,当脚步和想象都不能延伸的时候,我就有了大量时间和空间,写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黄铜小号》。”初稿她用了两个多月,一气呵成。
她从少年崔振芳的日常生活细节写起,从实处落笔,写他眼中的战争、写他思想的逐步变化、写他从一个农村少年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过程,一个抗战小英雄的形象逐渐丰满。“崔振芳在黄崖洞保卫战中很出名,他在生命的最后还是要保卫他的家乡。当年我已经是一个母亲了,身为母亲,我很想心疼一下这个孩子,当然还包括许多跟他同龄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孩子。一群孩子在对未来还没有认知、对和平还没有想象的时候,就在战争中死了。这一点触动了我,我想让更多今天的孩子看到这个故事。”葛水平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中充溢母爱的温柔。
对比今昔,她感慨良多:“现在的16岁孩子,还是妈妈的掌中宝。但那个时代的孩子,大山给你的就是山,因为父母无力养活,为了一口吃食选择当兵,只能看到眼前的日子。”
为了这篇小说,葛水平后来又两赴黄崖洞采风,只是再也没找到当年的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里还保留了战争时期的一些面貌,她可以让我的想象展开,想到战争、想到小战士。我很珍惜我曾经保留的黄崖洞记忆,也非常珍惜记忆中这个汉白玉雕的孩子。”《黄铜小号》终于落笔,一个孩子的故事鲜活而出,葛水平当然清楚,她不仅仅是在写一个孩子、一段历史,更是在写一种纪念、一种反思,“纪念这方山水,记住的虽然是它的革命战绩,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记住这些孩子,因为他们象征着一代人的儿童阶段。当一代人在儿童阶段就丧失了生命,实在太沉重了,后来人不应该忘却。”
跨界儿童文学题材让美好寄情于故事
为了呈现好这个故事,葛水平坚定地选择了她陌生的儿童文学,她很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用我擅长的严肃文学来表述这个故事,笔下的人物可能就不够出彩。我尽量让孩子们阅读时候,感觉散文化一点,散文容易给人文字的感染,我不仅是叙述一个故事。”
儿童化、散文化,也是记者在阅读《黄铜小号》的过程中,最深的感触。比如书中有一个贯穿故事的灵魂词汇:“捉月华”,就非常能体现这些特点。文中写:“捉月华就是用双手捧着明月的光华将它们藏起来。传说,将月华藏到米缸里,米缸里的粮食也永远吃不完,藏到炕席下,炕席上就会有数不清的新被褥叠摞起来;藏到心里,脸上的笑容就会亮给世人,心中就会开出幸福花。”浪漫而充满生趣。“这个词应该不是长治方言吧?是您的创造吗?”记者问。葛水平笑笑说:“其实北方没有这个说法,是南方的说法。但我童年的时候,我会在老家山上捉萤火虫,可以用来读书。农耕文明是很重视节气的,年怕中秋月怕半,时间对每个人都很紧迫。我加这个情节,就是希望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想一想,月亮的光华、月亮神秘感,是很美好的。”
此外,《黄铜小号》中还有很多童谚、童谣,这也是葛水平下工夫整理和创造出来的。一切寄于美好,一切为了孩子,是她在沉重故事背后埋下的希望。
一本书,跨越两个时空,牵起两代孩子。葛水平没说,但我相信她最期望的是架起一座时空的桥梁,让今天的孩子能走回去见证勇气、摆脱迷茫;也让当年的孩子能见到希望、拥有“未来”。
延伸对话
葛水平:一个人爱好太多肯定是“江湖骗子”
山西晚报:记得有位儿童文学作家说过,大多数成人文学作家并不适合写作儿童文学,只有内在生动的人才可以。您怎么看?
葛水平:你说的内心生动、停留在童年阶段,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我认可,因为每个写作者都应该在场,如果不在场,读者就会读出隔膜。
山西晚报:“停留在童年”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对您的感受。那您认为自己真实的心理年龄有多大?
葛水平:我认为我还是很小的。因为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独生子女,我没有亲姐妹,没有给我形成一个成熟人的榜样,我母亲又是小学讲师,当我跟着我母亲走乡串村时,遇见的也都是孩子。所以我认为我的实际年龄是40多岁,虽然我很大了(笑)。其实我不太会去考虑年龄,实在没时间去考虑。过年偶尔想一下,但也不会多想。
山西晚报:有一种说法,评价您是中国文坛“最有女人味的才女”。
葛水平:哎,那我没有听过的(笑)!我想可能跟我早年的一些经历有关。当年跟随母亲走乡串村教学,一直在流浪,两年换一个地方,春夏秋冬都坐着毛驴车行走在不同的土路上,拉着家当,其实那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浪漫。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会拉二胡,而且他还打蛇、做二胡。所以我对乡村有一种童趣的认知。
山西晚报:外界都知道您爱好广泛,也是缘于童年这些经历吧?
葛水平:对,我的爱好很多,是因为我觉得生命很短暂。用很江湖的话说,一个人爱好太多和懂得太多,肯定是一个江湖骗子!哈哈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只是觉得生命短暂,在生和死之间,我们总要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赋予什么?肯定是热爱。所以我尽量把我喜欢的罗列到我身边来,还蛮有乐趣的。
山西晚报:听说您爱绣花做衣服等,这还好理解,但听说您还喜欢打猎?
葛水平:对,那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当时枪支管理还没那么严,每年冬天他休年假15天就钻进山里打猎,我就跟着他一起打猎。
山西晚报:您的故乡也太棒了!说起沁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赵树理,那片土地对你走上文学之路是怎样的影响?
葛水平:我在沁水待到11岁,后来去长子县学戏曲。我和赵树理先生还没办法比较,因为他成长在一条大河之上,他们家在沁河最繁华的地段——尉迟村。而我是生活在一个山洼里面,我小时候住在窑洞里,都没有见过砖。那边没有大河,只有一潭泉水,它曲里拐弯地流出去,方向是大河,这中间它在不停变化着,我的成长也是这样。
山西晚报:什么时候您觉得自己可以走写作这条路了?
葛水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写作,只有热爱。我喜欢听乡民讲故事,喜欢听盲艺人说书,最早还迷恋炕墙画,老百姓家的炕墙画一般就是花花草草,而大户人家的就有了戏曲人物和故事,所以那时候最爱去大户人家听故事。
山西晚报:您学画画也是从喜欢炕墙画开始的吗?
葛水平:那没有。后来是因为我在长治文联当主席,文艺人才聚集,那时想问别人要一幅画是很困难的,我就想那我也学学画画吧。最开始从模仿别人的画作开始,一点一点,寻找自己的喜欢,也有10年了。最近5年只要不出差、不太忙,每天都会触摸一下,很有乐趣。
山西晚报:突然明白了,如此丰富的人,作品才会如此丰富。
葛水平:对,生活给了我很多,成长教会了我很多。我特别感激我出生在贫苦的乡村,那种生活是活泼的,这让我的成长很灵动。你说我身上有童年的色彩,其实正是这种生活滋养我的。
山西晚报:您怎么评价自己的性格?
葛水平:我性格里是有一种野性的东西,除了在文学上我不服输之外,其他的我都服输(笑)。在文学上我是有野心的,因为我想写出一部好的作品,能让后人记住这部作品。
山西晚报:您觉得这部作品还没有出现吗?
葛水平:我觉得还没有自己很满意的东西。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这里给我的营养太足了,甚至让我精力不够去触碰这些养分,比如明清古建、寺庙、人文山水,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太多,需要现代人书写它。
文学是我有生之年只要还健康,就不会丢掉的。因为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就特别幸福,什么都不想。请让我安静地活着、孤独地行走,这很重要!
山西晚报:能说说您最近的创作吗?
葛水平:刚写完一部长篇《和平》,就要出版了,主要写抗日战争,以黄河为背景,从我的视角写普通人面对的战争。另外,正写一部晋商题材的作品《风水》(暂定),书名其实是风和水之意,写人在风和水中成长的不易。和别的晋商作品不一样,我以一个女性为主角,预计30多万字吧。
山西晚报:最后想问问您,走了这么远,还回老家吗?
葛水平:要回的呀,其实我的成长从没离开过乡村。人们说,肠胃是有故乡的,写作其实也是有记忆的,那么我的原乡就是乡村,我抛开乡村写别人的城市,就找不到疼痛感。即使要写,也是我家乡的人和事强加到他乡的,而他乡是没有故乡的!
记者手记
文字世界秘密之门随着聊天而打开
采访是在夏日的一个大晴天,刚到葛老师家院门口,发现小院的门半掩着,以为她是在等我们,便走进去扣门。一小会儿,她穿着一件黑底淡绿花的棉布长袍缓缓走出,脚上拖着一双绣花鞋……阳光正洒在她身上,慵懒的松弛感尽显,她淡淡说了声:“哎哟,昨晚又忘了关院儿门了”,随后浅笑着把客人请进门。
一进客厅,便觉震撼,小型博物馆的既视感。在书架和满目的绿植间,是她多年的各路收藏,木质、琉璃、陶瓷、竹编等材质的老物件杂而有序地组合着,叫不上名字的古老打击乐器,轻轻一碰就发出空灵的醉人之音。当然,最显眼的是墙上她的画作,还有茶几、飘窗上她采摘晾晒的玫瑰花、水蜜桃……所有的一切,都展示着女主人的品位。
采访就是在这座“博物馆”里展开的,我们陷在两个惬意的红色皮沙发里,一对一展开交流,教育社的编辑们则在一旁静静地聆听、录像。那天的氛围特别好,聊着聊着,我们从作品漫谈到了性格、人生,葛老师讲述她童年的那段格外动人。突然就有种打开她文字世界秘密之门的感觉。
越聊越惊讶,一个会写文、画画、烧陶、刺绣、做衣、种菜、弄乐、钓鱼、打猎……的女人到底有多少面?答案难寻,但那句“漂亮的女人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
山西晚报记者 范璐
1.《黄铜小号》首发吸引了大批读者。
2.《黄铜小号》文学沙龙。
3.签售会吸引了很多文学爱好者。
4.葛水平回答记者提问。
5.山西晚报记者(左)专访葛水平。
6.《黄铜小号》书封。